女作家葛水平 葛水平:赵树理家乡走出的女作家
来到“魅力城市”长治,走进葛水平居住的小区,才知道工作于斯、生活于斯的女作家葛水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是陌生。细想之下,怨不得别人,去年一年她的迅速蹿红实在太突然,以至于这座小城的人们来不及事先知道她。
4月26日一大早,记者通过电话与葛水平相约小区门口见,几分后先行到达,向门卫打听,葛水平住哪?中年男子一脸茫然。补充:就是住在咱这儿的女作家。———茫然变作愕然。这时扭头,不远处一短发女子浅笑嫣然,眉眼间透着清爽和韵味。
七分袖的宽松外套前襟处一团手工刺绣原始、乡土。她说衣服是请裁缝做好后自己再亲手绣了花,说话间言语中透出一丝小小的自得。 葛水平家的院子不大,内容却丰富:几株盆栽、半块石磨、两只鸟、一条狗……客厅里最显眼的装饰是两只硕大的南瓜和一口生锈的破钟。
穿过客厅进书房前,得先跨过一块木板,木板竖起如同旧时祠堂的门槛,高度恰好让一路悄悄尾随身后的小狗断了继续下去的念想。书房内,满满一壁书籍、硕大一张书桌之外,古条几、土陶罐、太师椅……房间里无处不在的田园情调和古旧陈香,无一不在印证着主人散文集中的一句话:我是一个蜗居在城里的乡下女人。
A 抽几口旱烟,看几朵云彩,心里平和着,吼几声凉腔走调的山歌来,那一种幸福,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记:坦白讲,你现在的生活很“精致”,感觉与你作品中的黄土塬、土窑洞、秃岭、深沟和土得掉渣的男人女人、牲口等全然扯不上干系,那些活生生的人、事、物多半来自童年的记忆吗? 葛:一个人的精致,自己是看不到的,我只是想做一个好女人,心手相印的好女人,不管生活如何,只想自己把自己开放得灿烂。
现在很少有人住窑洞了,住过窑洞的人才知道它的好。我成长的窑洞,窑掌喂了驴,拐一个洞藏了粮食,也藏着另一个家族:鼠。
人、驴、鼠相安无事。墙上因鼠的原因多出了一个小小的洞,拿玉茭芯塞进去用斧子捣实了,外面挂一个干黄的葫芦,葫芦是割了口的,藏着我喜欢的零嘴儿。我的祖母是裹脚,常年戴着一个绣花大肚兜,肚兜里有柿饼,和像羊屎蛋一样的黑软枣,我的小手进去,常常掏一把土出来。
土生土长的人吃土是能咂出一些活命的滋味来的。当我像云一样离开窑洞,走向社会,我反而丢失了一种窑洞里生存的人的自在的神态。
谁又能说混沌不是一种大境界呢,像窑洞里的人,只守着自己的家园,守着一种不变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抽几口旱烟,看几朵云彩,心里平和着,吼几声凉腔走调的山歌来,那一种幸福,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记:你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葛:我小的时候学习不好,准确说是数学不好。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我父母把我当男孩子使唤,有一段时间在村里当小学教师的母亲让我去学习武术,断断续续大约有两年。后来考虑到参加剧团将来能吃上供应粮,12岁就去学唱戏了,接受了两年培训后跟了剧团下乡演出,演一些丫环之类跑龙套的角色。
在乡间赶台口,从车上摔下来过,躺在汽车肚下半尺高的麦苗地里,我还在睡。我演过最重的角色是“秦香莲”的女儿“冬梅”,开场到最后,没有道白没有唱词,干叫“妈妈”。
那时年龄小,熬不了夜,记得有一两次出台中间躲在幕布后睡着了,最后一场戏“秦香莲”只好领着一个儿子上台,观众起哄,我因此被扣了一个月的工资,8块钱。
小时候常听人说:“半河腰出了个赵树理。”半河腰子上出的事情太多,但是,知道赵树理是一个编故事的,我知道了就很激动。因为,我们同喝一条沁河水,当然,赵树理永远是一个高度!开始是学写诗,大概在十四五岁,第一首诗的名字叫《松果》,发表在《山西青年报》上,我那时在乡下演出,举了黄旗站在台上,接到消息很激动,像唱了一回主演一样,满身子热血沸腾。
记:有评论说你作品中“娴熟的叙述、丰润的情感”“难得的民主精神”“暖暖的理想色调”共存,也有人称2004年的小说创作为“葛水平年”,你个人怎么看? 葛:俗话讲吵架:“无理全仗音高”,我的作品是评论家提高了,我对我自己的作品评价是:还可以,谈不上有多好。
中国这么大,有多少人在辛苦创作,怎么能定为“葛水平年”?这个好名儿加到我头上,大了。 我写是因为我想写,我这人爱好太多,这么多年狗熊掰棒子一样也丢了好多,比如钓鱼、玩麻将、打猎等,惟有看书写文章是第一爱好,多年不舍得丢掉。
我父亲不是我亲父亲,是继父,他教我好多男人发嘎的事情,比如:偷鸡、炸鱼塘。我父亲50岁上和外地人打架,我到派出所交罚款赎他,55岁上私自造土枪卖钱,我又到派出所交罚款赎他。
我父亲走出派出所的第一句话是:“做什么事就得像什么事,有这样的结果,说明我做好了。”我当时是哭笑不得。有缘结识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家族是我的幸事,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达观的东西,他的诚恳逼真和来自大自然野性的浪漫,让他的思想散漫得很广,他的事业和感官玩乐融成了一体,让我知道了做一件事情其实是玩一种心情,也要做得像那么回事情,把心情玩得出彩,才好!
B 这件事对我的伤害很重!我一直想把它写出来,等了好多年,我终于把它写出来了。
记:那些读来真实生动的故事中有没有你故乡长辈甚至你自己的影子?写作中是否会把自己当作其中某人? 葛:写小说的人都是富有想象力的,但是,肯定要有生活,哪怕是书本的生活。我小说中的人物《甩鞭》有我祖父、祖母的影子,准确地说,是我小爷和小奶奶。
小奶奶是地主婆,土改时她原来的丈夫被贫下中农斗死了,我的小奶奶被小爷以贫下中农的身份娶回来。娶她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穷,租不起花轿,我小爷的哥哥,也就是我爷爷想了个点子,找了两个后生用土改分来的一把太师椅,就像我书房里这把,抬了过来。
小奶奶当时嫁过来的时候是带了棺材过来的,上好的楠木棺。那口棺材放在窑掌深处,很多年。我小奶奶比我小爷大10岁,早走时留下话,把棺材给我小爷,她要一个松木的。
我那时候已经懂事了,很是感动过他们的爱情,后来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爱情,是对我小爷的感激。我小奶奶想“速烂”。这件事对我的伤害(原谅我用这么一个词,我认为触痛心灵的东西都是一种伤害)很重!
我一直想把它写出来,等了好多年,我终于把它写出来了。就是我的小说处女作《甩鞭》。 其他的基本没有了。我喜欢听乡下人讲故事,好奇心让我想把听来的故事写出来。我强加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会想我如果在那样的环境会怎么来选择生存,来选择生活。
记:你作品中的男女之爱多了乡间的原始、纯真,少了城市人的造作矫情:一个鸡蛋、一张饼、一张羊皮、一次耕种、一生守望……成为他(她)们苍凉生命中一抹亮色。
你如何理解现实生活中的爱情? 葛:爱情是人类存在的永恒话题,它就像自然界的青山秀水一样,因了存在才得以让人类源远流长,长盛不衰。我想起一句话儿:“钢刀儿拿来头割下,血身子还陪着个你!
”爱情是一种无法广泛种植的稀有植物,它直接源于一个人的心灵。当一个人爱一个人的时候,就像三月种下一棵树一样,他必须不断来培育这棵树要它枝繁叶茂,多年来这棵树会吸食双方的养分,但是,你会发现天生的并于无意中培育起来的感恩之心像金子一样可贵。
爱情是有约束的,它包容着很多内容。它不应该太自私,应该给对方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互相在一起的时候要有一种自在自主的状态,能互相激发出那种天赋的活泼、自由和奔放。
我认为男女之间的性福,也要像舞蹈一样轻松愉快。 记:你的作品中很重视偶然事件对人物命运带来的巨大改变,你认为现实本来如此还是创作的需要? 葛:命运对一个人的改变有时候不由自己的意志来转变。偶然事件的发生给好多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和痛苦,单纯说小说的话,偶然发生的事情是需要细节来连缀的。
C 他那只好眼睛流着泪,说:“割了鸡巴敬神呢,人都疼死了,神还说腥气呢。” 记: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家里人看你的小说吗?看后如何评价? 葛:我不好来评判我的性格。
这么说吧,我喜欢静,喜欢与人真诚相交,有时候又怕说错什么伤害了别人,怕美好的开始很快就有了糟糕的结局。不喜欢把不愉快的事情憋在肚里,不喜欢别人的心事要人来猜。
喜欢打抱不平,但人微言轻。 通常我小说的第一读者是我的丈夫,由他来决定我的作品是否拿得出手,我很相信他,因为他是搞新闻的,他比我读书多。母亲和儿子不喜欢读我的小说,不认为我做什么事情了,只关心我胖了瘦了。
我的公公和婆婆喜欢读我的小说,公公总是第一时间里到街上的书报亭买来读,有时候还写读后感,这让我很感动。 记:目前主要做什么?近期有无作品问世?今后是否仍继续延续已有的风格,还会继续用两个字的题? 葛:我现在屯留县挂职,还没有深入到农村。
到农村采风很重要,我到一个农村去了解一个事情时,看到县里的干部刚刚吃喝了抹嘴走人,边走还边埋怨招待不好,说什么没有一条龙服务。村里的干部不说话,像丢了心似的。
伙房做饭的那个人戴了墨镜,我当时没有看到他是一只眼,只发现他一半儿脸颊上流泪,他告诉我他有一只眼睛是坏眼。他那只好眼睛流着泪,说:“割了鸡巴敬神呢,人都疼死了,神还说腥气呢。”他在说我们的干部。
手头在写一个农村题材的中篇。《中国作家》第五期有一个中篇《黑口》,《小说月报原创》有一个中篇《陷入大漠的月亮》,《北京文学》和《花城》也将有作品出来。以后还会以农村题材的小说为主,我喜欢农村,能找到感觉。
用两个字的题,是因为用多字反不能显示作品的力度。 后记:采访结束,告辞的话还没说完,小狗已从作家主人的脚下蹿出,朝着胡同口扬长而去,主人顺手操起一柄笤帚,吆喝着展开围追堵截。 那一刻,我看到了她身上“乡下女人”的影子,在书房之外。
个人档案 葛水平,女,1966年出生于山西沁水县。现为长治市戏剧研究院编剧,长治市作协副主席。曾出版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
2003年开始小说创作,2004年相继推出中篇小说《甩鞭》、《地气》、《天殇》、《狗狗狗》、《喊山》等。其中《甩鞭》和《地气》分别入选2004年度当代中国文学最新排行榜和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葛水平本人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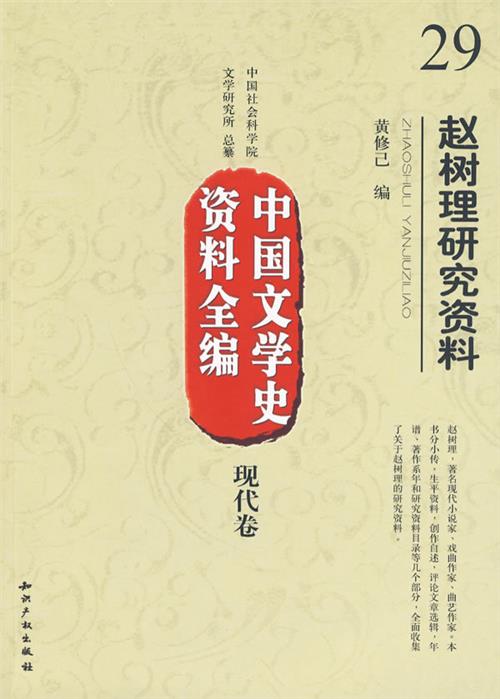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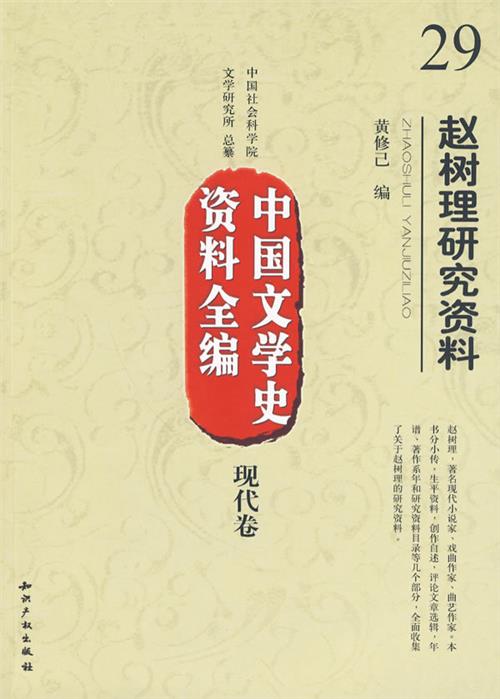






![>东北虎刘玉堂 [山东人物]"当代赵树理"刘玉堂:幽默的"文化人儿"](https://pic.bilezu.com/upload/c/83/c83fb15c4653f94999a297f740277d5b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