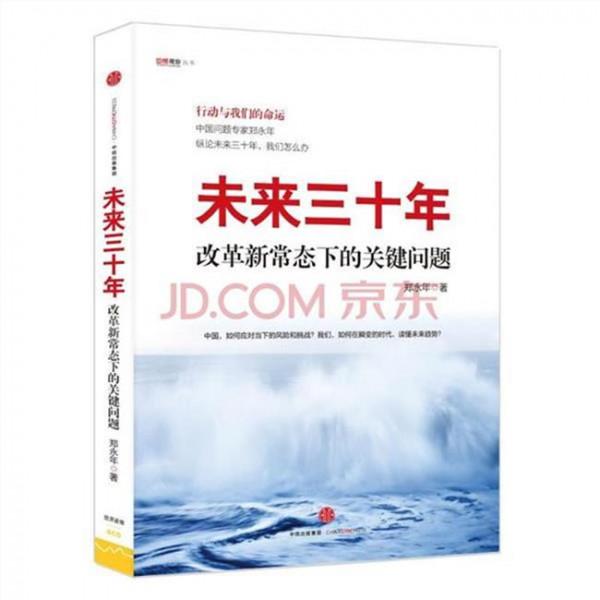郑永年书籍 《郑永年2016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摘要 书评 试读】
不过,强调“中国特色”,并不是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其他国家毫不相关。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成功故事里面既包含了中国本身的创新,也包含了中国这个学习大国向其他国家学习的宝贵经验。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向他国学习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开放式学习的过程。可以说,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很难在世界上找到第二个像中国这样能够学习他国经验的国家。中国既向美国那样的大国学习,也向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学习。
当然,向其他国家学习并非照抄照搬,而是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创新。这种过程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经验同其他国家既具有相关性,也具有特殊性。 作为今天东亚国家,中国的经验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更具有相关性。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故事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亚洲的,是广义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就如美国的发展故事既是它自己的,也是广义西方的。美国一方面强调“美国梦”,另一方面也极力推崇整体西方价值。
美国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建设其软实力,即把美国置于整体西方世界里面而显示出其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也是反映了事物的真实面。如果套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世界范围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明不仅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制度,而且也具有了不同的“世界秩序观”。
的确,在近代西方形式的国家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前,尽管各国的制度存在差异,但同一文明圈内部不同国家的制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使在近代西方国家形式传播开来之后,同一文明圈内部不同国家的制度的相似性要远远大于不同文明圈国家的制度之间的相似性。
的确,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展及制度建设是不同文明圈内部的发展和制度建设。尽管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互相影响,但这并不是说一种文明可以取代另外一种文明,一种文明内部的制度可以为另外一种文明内部的制度所取代。
在经验层面,不难观察到,文明间的互相影响和互相学习可以促成制度的改善,但文明间制度和发展经验的照抄照搬,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会出现问题,甚至导致灾难。
简单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制度建设都具有文明性。 在亚洲,“亚洲价值观”概念的提出正是反映了亚洲各国和地区发展及制度建设的亚洲文明性。
这个概念由李光耀等亚洲政治家在20 世纪80 年代提出,并在当时的政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过,在学术界,这个概念所受到的待遇情况复杂。尽管很多学者(主要是亚洲学者,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此持有积极态度,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总体上,近代以来一直接受着西方话语体系的亚洲知识界对此的反应和西方学术界对此的反应并无两样,并在围攻这个概念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关亚洲价值观话语的塑造和传播便中止了。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首先是20 世纪90 年代初的变化,即在苏联和苏东集团解体之后,美国便成为的世界霸权。对西方来说,这意味着西方文明赢得了胜利。美籍日裔作家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便是这一政治氛围的典型反映。
其次,与此同时,世界的全球化加速,迅速扩展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波全球化主要是西方资本推动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受惠于资本的全球化。再次,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本身面临危机,需要转型,包括李光耀在内的一些亚洲政治家也开始反思亚洲发展模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亚洲价值观的讨论转入低潮。 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说,亚洲价值观消失了。
有几个重要因素促成亚洲价值观的复兴。第一是2008 年的西方金融危机。在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普遍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如果亚洲要避免类似的金融危机再现,就要向西方学习。
不过,2008 年西方金融危机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看法。再者,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受到危机深刻影响的亚洲国家很快就走出了困局,但2008 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受到危机深刻影响的西方国家长时期处于危机之中。
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亚洲发展模式具有更大的能力对付危机。第二,在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亚洲国家的发展模式出现了分岔,一些国家和地区变得更西方化,而另一些则坚守自己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努力改善自己的制度。
分岔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前者的表现远不如后者。那些把自己变得更为西方化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和中国台湾)陷入停滞发展的陷阱,而那些不放弃自己的发展模式而加以改进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韩国),其发展更上一层楼。
第三,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方面开放向其他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也明确强调中国不照抄照搬西方模式。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崛起对亚洲价值观的影响具有双面性。
在实践层面,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其发展过程实际上也体现了亚洲价值观。在这个层面,中国经验是对亚洲价值观的贡献。但是,在话语层面,中国的崛起反而制约着亚洲价值观的复兴和传播。
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如前面所述,中国本身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非亚洲价值观。这种标新立异的追求从表面上把“中国特色”和亚洲价值观隔离开来。其次,西方是看到了中国发展的亚洲性的,即尽管中国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但总体上是属于亚洲发展经验的。
从政治上说,西方方便地选择了批评“中国模式”而避免选择涉及更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亚洲价值观。其三,从地缘政治环境来说,中国的崛起改变着亚洲其他国家的国际环境,很多国家和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冲突,因此并不想让中国来代表亚洲价值观。
对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是亚洲国家,如果中国代表亚洲价值观而它们又是从属于这个亚洲价值观的,这在政治上很难接受。 中国所面临的情形和美国的情况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一直是代表西方价值观的,不仅美国自己这样认为,很多西方国家也是这么认为和接受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在事实上是西方价值的一部分,更是因为美国的内政和外交行为容易被其他西方国家所接受。
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但冲突主要发生在利益层面,而非价值层面。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在价值层面,实际上和其他亚洲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共同性,但中国的内政外交行为方式促使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并不乐意接受中国代表亚洲价值观。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要复兴和进而代表亚洲价值观,主要的困难来自政治,并非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对亚洲价值观的认同差异。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因素也不能妨碍我们对中国和亚洲价值观之间关联的探讨。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大国,我们有条件对亚洲价值观重新评估,重估中国和亚洲国家发展的相关性和中国对亚洲价值观的贡献。 从政策层面看,我们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复兴弘扬亚洲价值观的同时结束长期以来在话语权方面的孤立状态。
脱离了亚洲文明,简单的“中国特色”很难持续下去。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历史地看,中国历来就是亚洲价值观的的源泉。在再次崛起的今天,我们不可以放弃这份丰富的历史遗产。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塑造发展话语方面,把自己孤立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之外。尽管我们有自己的特色,但我们更需要找到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共同经验。 复兴亚洲价值观面临两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必须纠正西方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错误认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正面阐述新时代的亚洲价值观。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可以成为这种阐述的重要部分。随着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其地缘影响范围也在扩大。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亚洲社会共享的、又为其他区域国家所理解的亚洲价值体系。而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更是为亚洲价值观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机遇。 中国领导层近年来越来越重视中国和亚洲的共同发展,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如果我们能够把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命运共同体整合起来,中国可以掌握塑造一种至少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所能接受的话语的主导权。亚洲的成功和亚洲价值观分不开,正像西方的成功和西方的价值观分不开一样。这不是说,亚洲价值观的再次崛起要取代西方价值观,而只是说,世界上又多了一种选择。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的分享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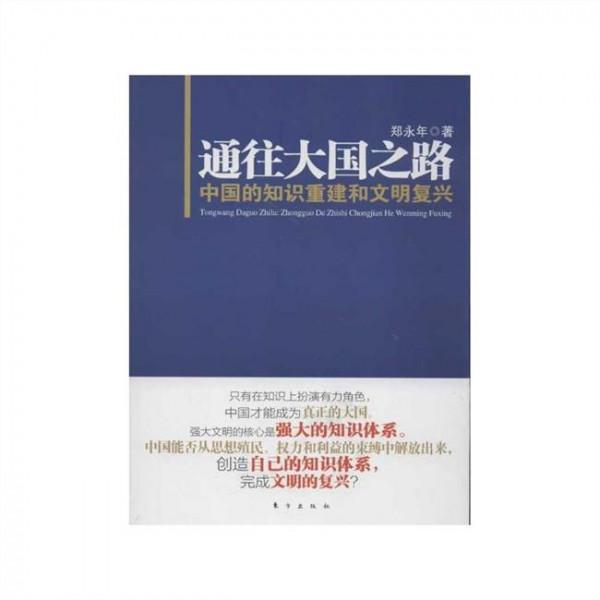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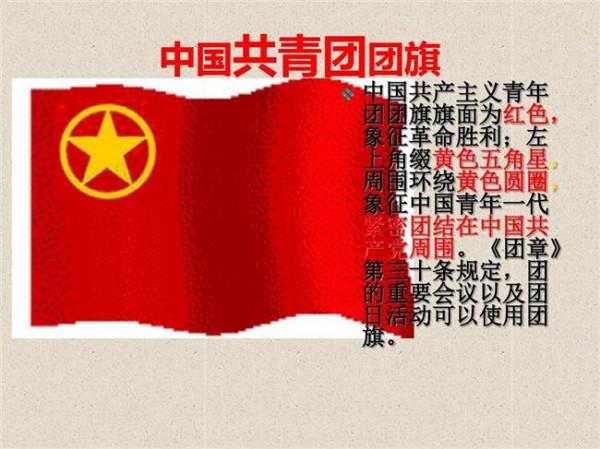


![>[郑和远航]郑和远航](https://pic.bilezu.com/upload/9/d5/9d5cfdadab03fd0726dc0e89c730378d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