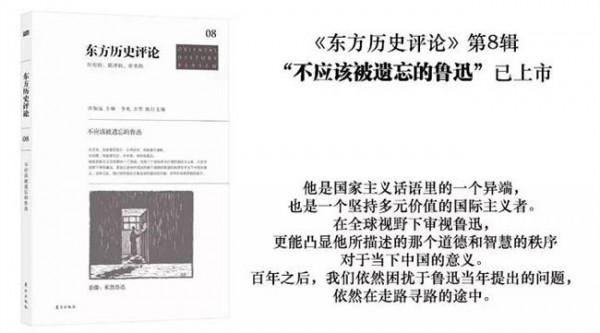许章润天数 许章润《坐待天明》——儒在苍生捍共和
(上) 最早知晓许章润先生是通过他关于立宪民主与人民共和的系列文章,第一次有幸相见则是去年6月20日在高和分享主办、张彦武老师主持、马立诚先生和许章润先生主讲的《在思潮博弈中认识中国》讲座上许先生前来为马先生及其新书“站台”,彼时其对当下时局中“权贵资本与民粹主义遥相呼应”的论断更是激发了我对于转型期中的中国在政道和治道的深切思考。
同时,正是在这次读书会上,我因提问发言而有幸得到了许先生亲笔签名的这本散文集《坐待天明》,让我有机会带着许先生笔触的温度近距离地体察他的思想与情怀。
从去年6月到今年1月,从国贸2期到颐和园路5号,从帝都北京到魔都上海,在历经坎坷变幻的大半年后,我又重新拾起这本文集,细细品味许先生的儒生情怀与共和理想。
在引言中,许先生用温情脉脉且又心有戚戚的笔触,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从故乡到异乡又到梦乡和愿乡的“乌有之乡”。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乡,生活从故乡出发,又不得不流转异乡而抛洒生命;然而梦回人远,乡关何处,最终落脚的却是梦乡和愿乡;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俯仰往来之间岂不都是乌有之乡,白云苍狗之馀所剩徒有坐待天明。
倏然觉得,这从故乡的异乡的辗转挪移,这从异乡到梦乡的惆怅流离,不正是我的双城记么?不正是我从古城西安负笈求学于首都北京,坎坷沉浮寄居南国沪上,又将远离故土身赴异邦的真实写照么?在这故乡与异乡之间,在这本土与他国之间,又有多少的“自我”与“他者”的错乱纠缠,又将演绎出多少的怅惋迷茫——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全书共分四章,子时、丑时、寅时和卯时分别对应故乡、异乡、梦乡和愿乡,在这黎明前的黑色深夜中徐徐展开先生从曾经的少年游子到如今已两鬓飞霜这若干年来的思忖、感怀与回想——一滴相思血,两行悲喜泪。
《子时·故乡》共17篇,讲述了许先生负笈背囊里滋养其一生光阴的永恒瞬间。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真人秀”,被老鼠啮去双睛的“马先生”,旧日的”大学生村官“高正迟,“青草堂反革命集团案”中的王秀才以及因果报应的关帝庙,四位乡民的不同死法,做受生活的人生体悟,“意想不到”的两件往事,县城里的十七件消息和街景…… 许先生笔下的故乡里那散落于巷陌街肆的零落,流布于野村孤郊的荒僻,沾染着尘落风霜的往事以及挣扎在卑微艰难中的乡民,无不让人身近情怯而不能自已。
然而,也正如许先生所言,尽管这些永恒的问候温暖着此在世界继续跋涉的生者,但总是来去匆匆且终究一去不返;故乡早成异乡,而异乡又不可能变为故乡,身处两端的他们无所适从,而游走四方的我们又倍感荒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 《丑时·异乡》共31篇,讲述了许先生背井离乡人在途中的见闻、经历与感慨。
跻身法理学研究的前前后后,中年罹患后又终得痊愈的“天数”,功力、心力、愿力和体力所构成的学问“四力”,住院期间目睹的浮世苍生、六则病例、老将军的“亲骨肉”和两位心怀天下的病叟以及许先生早年求学、深造期间与李光灿先生、李步云先生和江平先生等前辈大家之间的往事,因出国被查、出版受阻、出题被撤的感慨还有对清华死板校规的无奈,对“制度性羞辱”和“日常性羞辱”的愤懑和对威权主义政治和官僚化体系所衍生的应试教育模式下清华学生唯命是从、唯分是举而变得聪明但少才华、应变不见性情、志向淹没理想、勇敢却无血性的无限慨叹与惆怅。
在许先生看来,不管是“三分春色,一分散漫,两分慵懒”的宁静校园,还是蛮横无理的党政权力和龌龊肮脏的校园政治对于人性与人心的欺凌,不管是思接千古的课堂与九曲回肠的心田,还是生死轮回且人各有命的天数,我们每一个个体在境性生存的同时也映照着亿万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经历的其他个体的生命光华,回鸣着它们沉潜心田的低吟长啸——在这个意义上,琐碎的文字作为长留心田的生命记忆与无意间散落尘世的零落花瓣,点点滴滴,星星斑斑,连缀起生死一线。
《寅时·梦乡》共29篇,讲述了许先生在有限生命和无限长梦中所感受和承受的欣悦与凄徨。
对“万里姻缘”无常有常的喟然与慨叹,对“风姿绰约”们的鄙夷与无奈,对公款吃喝的不满和嘲讽,对“三聚氰胺”事件的痛恨,对“非法同居”罪和“投机倒把”罪的戏谑,对“民国派头”的钦慕,对“理论学习组”的“平庸之恶”下所露出的“马脚”的警示以及对“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利私性化”的批评,对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中小学生数目的忧虑,对法学语言缺乏“历史的想象力”的扼腕,对晚近十年学界衰颓的笃思甚至包括对南京“换偶”案所反映的社会进步或堕落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零零碎碎的铺叙和喋喋不休的议论,正是为了讲述、理解和反思这个千载难逢但却悲喜交加的时代——“用讲述来回应这个时代,于回应中认识和理述这个时代”。
在他看来,这正是读书人的生物脾性和时代责任,也只有我们每一个经历了这一时代、听闻于这个时代、受惠于这个时代、特别是受害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它的读书人都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用笔、用纸、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记述曾经发生过的“我们的”悲欢离合,追思曾经被迫承受的“我们的”的血雨腥风——为它留下一抹记忆,哪怕一鳞片爪,不啻是在告慰祭奠先逝的父兄,而且,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从而,护卫子孙万代。
《卯时·愿乡》共21篇,讲述了许先生对于未来的祈祷以及一份梦境为幻的侥幸。对于黄宗羲先生的缅怀,为梁漱溟先生两份晚年口述所写的书评,在学科分际背景下对“学问如诗”的呼唤,对法律共同体用法学发声的正名,为清华大学2009届毕业生致辞的讲稿(《七月的寓言》)以及对重庆“唱红”的警示,对市场经济中的“强盗逻辑”的反思,对能够彰显遭到遮蔽的生活意义的习惯法的重视,对近亲结婚在法理与清理上的分析,对西南政法校园搬迁及其抗争的看法和法律语言、法理学教育、开放的思想市场、尊重普世价值的国家理性和自由理念的思考。
这些“祈祷”与“侥幸”都构成了许先生眼中讲述与反思的“交谈”,而这种交谈也是符合前苏格拉底学派所倡导的“对话的”和“与大众分享”的“逻各斯”的交往伦理与交往理性,也只有通过交谈我们才能有望保持人性,人间的欢笑和号哭才能具有存在的意义。
用文字捍卫记忆,用记忆抵抗权力,用抵抗守护人性,为身体招魂,让思想发声,放逐恐惧,拆解羞辱,重建生命,这恐怕也是这本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的散文集的全部意义。 (下) 许先生将自鸦片战争以还这一百七十五年中国近代历史中吾族吾国吾民的时代特征总结为“羞辱”二字——这种“羞辱”延续至今的例证则是汉语在当今中华大地的地位与荣耀荡然无存,而这“最不容易被污染”的语言也成为中华文明遭受的创伤和羞辱的活生体现。
在许先生看来,汉语文言作为一种最典雅、最温驯、最具表意能力的伟大文字,本来是一个比拉丁文字更伟大的文化传统,承载的是东亚世界千万年积淀的文教风华,含蕴了汉语文明有关神事与人事的雅量高致,“她那一切无言之言与不言之言,她那无际无涯的丰瞻绰约纬地经天。
” 而就法学世界中的法言法语而言,不管是因为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政工具与生俱来的“平易近人”,还是正如苏力与丁丁所言77、78级法学院入学生也就是现在掌握各大法学院院长、书记、博导、教授之流均为“低能弱智”之辈,本着“直面现象”的态度,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法言法语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式的“大鸣大放”,还是工农联盟主力军式的“一穷二白”,就连台湾司法院大法官解释文书所透露着的温雅隽永都远远比之不及,更遑论与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判决文书中的议理或表情的闪闪星光。
而在此之中,许先生无疑是一种“另类”的存在和不俗的“写意”。 读过许先生文章或是听过许老师讲演的朋友都会知道,他那深厚扎实的语文功底,逸兴遄飞的浮思流情,加之典雅温驯的汉语文言和感怀相与的儒生气度,让我们无不感觉到中华文化的深秀隽永和汉语法学的博大精深。
相比于其他高屋建瓴、鸿篇巨著的法学大家,或是意气风发、口若悬河的高校名师,许先生的期期艾艾、水转山连,反而透出他极为难得的真诚、质朴与坚持。
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以申说幽思而表达忧思,以诉诸感性而贴近灵魂——任阑珊,人如玉,忍负一春闲。
” 但是,许先生绝不仅是寄情山水的隐士或是放浪形骸的酒徒,在他典雅温驯、流畅多情的文字背后,在他自言“少年无知”与“自幼家贫”的言外,还满怀着一介书生儒在苍生的义气和不平则鸣的胆识。
许先生曾这样说道,“人要讲理,不讲理便是禽兽;世间要有讲理的地方,否则顿成地狱。”诚然,他与蛮横无理的党政权力的讲理,不遗余力抵抗其对学术自由和学者尊严的挑衅;他与龌龊肮脏的校园政治讲理,不计后果对抗其对校园生态和教学规律的干预;他与无所不在的权贵资本讲理,不厌其烦地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他与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讲理,不辞劳苦地宣扬立宪民主与人民共和的真谛。
在他看来,天下总有理在,人间不可或缺一个理字,而其所耕耘多年的本行法理学,更是实现天理、法律、人情有机统一的重要利器。
许先生在《落草》一文中曾这样讲道:“法理存在于一切法律现象之中。正如法律理性使得法律之成为法律,法理凝练法意,说明了为何法律理性之得为法律理性,而构成了人类理性的重要一环,也是人类情感的重要体现。
就此而言,法律是人生的一部分,并服务于人生,而表现和具形为人世。法理即人情,也就是世道,人情世道合为人生,本是人世的根本。
有什么样的人情世道,就有什么样的法意与法制,从而有什么样的人生。” 的确,许先生这份对真理的追索与坚守,对鬼魅的鄙夷与顽抗,不仅体现在他深耕多年的法理学领域中,体现在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晚近十年来学界之衰颓之景间,体现在他近四十年不曾离开的大学校园里,也体现在他爱之期之责之叹之的莘莘学子上。
在其《你我都是这时代的产儿》一文中,许先生哀叹在威权主义政治和官僚化体系所衍生的应试教育模式下清华学生唯命是从、唯分是举而变得聪明但少才华、应变不见性情、志向淹没理想、勇敢却无血性。
在此,他特别提出在所谓的“智商”和“情商”之外,尚有“义商”、“仪商”和“灵商”,尚有对于庄严的敬意,关于神圣的憧憬,凸显着人类用思想来思想,以生命印证生命的伟大禀赋,并以此理性、良知与教养构成了一种君子人格与超越心性,名曰——“读书人”。
然而,如果仅有以上二者,以其文人之才情与士人之情操,许先生也足够杰出甚至堪称伟大。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许先生身上极为难得的是在这滔滔文采与磐磐坚守之间跳跃着的诙谐、戏谑与幽默。正如千帆老师所言,“现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般比较沉重,不会像他那样诙谐幽默,而那些风趣有文才的,却又大都没有多少社会责任感。
两种美德不容易兼有,却同时体现在章润身上。 ” 读许先生的书,听许先生的课,望许先生的人,都会觉得有种似曾相识却渐行渐远的书生意气,又有一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士人担当,更有一种“度一切苦厄”的释迦、基督的济世情怀。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评价后主之词时说其是“以血书者也”,并将其评价为“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许先生的人生体悟与道德情操,只不过他更为弥足珍贵的是以如此诙谐戏谑的方式言说展现。“读书救国”(《走马转心楼》)、“英雄群体”(《扁担挑子两头沉》)、“万物竞长”(《县城里的消息和街景》)、“和谐”(《这次第,浮世苍生》)、“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两篇横幅》)、“世界一流大学”(《教学事故》),以及一声“朋友”和“哥们儿”、一句“奶奶个熊”和“滚他妈的蛋”,这些嬉笑怒骂的“粗言秽语”,这些情之所至的“意气用事”,才是许先生的才情所系、豪情所驻、真情所依与深情所冀。
究其原因,用许先生自己的话说,他们这一辈人性格的宿命便是逆来顺受与深度叛逆——“压抑时代的阴影之笼罩终生,与自始即决绝冲决罗网、拥抱自由的激昂,一直并存于灵魂的幽微深宅。
”(《落草》)这是这看似矛盾冲突的秉性与时不我与的哀愁,让以许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历经沉浮坎坷仍充盈悲悯仁慈心肠,饱饮血雨风霜还不掷“少年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与许先生最为秉性相投、心戚相依的是他所谓的“民国派头”——在那些汉语法学界的前辈学人身上看到的公共理想与家国情怀,看到的温情敬意与洵洵蔼蔼,看到的诚恳散淡与坚忍承担。
其中,最令许先生钦慕敬仰的“民国派头”当属胡适先生。作为1962年生的胡适先生的“转世灵童”之一,许先生最为感佩的是胡适先生“浑身洋溢着一种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批判力量”与其所秉具的“高等常识”所体现出的旷达、通达、理性的洞识与读书人的良知、理性与教养。
然而,作为对许先生的揣度与妄评,在文章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不由得再次想起20世纪近代最重要的词学大家,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和诗词学家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的一句名言:“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
”这不仅是叶嘉莹先生奉行一生的文化格言,也是激励吾辈为学为人的毕生准则。 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许先生数十年来求学读书、教学育人、为师为士所秉承的最为根本的人生信条。
他那汉语法学的温雅隽永,他那教书育人的勤恳从容,他那指点江山的责任担当,他那嬉笑怒骂的书生豪情,正是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中国转型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读书人之生活——文染才江育桃李,儒在苍生捍共和。
最后,我想用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篇书评的结尾: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
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但是这样一种客观的评判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给后人。
” (完) 张熙 2016年1月20-22日 于上海家中 初稿 2016年2月4-6日 于上海家中 修改、补充 注:前昨所发(上)中末段“二十字”应为“二十万字”,(下)中第十段“跳跃着的的诙谐”应为“跳跃着的诙谐。感谢吴兄启智的提醒,特此订正,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