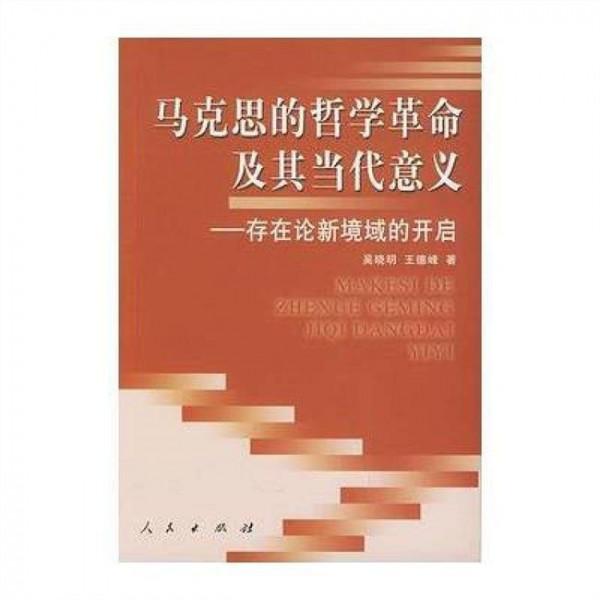杜维明刘茂才 杜维明等:当代中国怎样才有更好的商业伦理?
原题为《当代儒商如何重建主体性?》 2015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了“商业伦理”工作坊2015会议。会议发起人为高研院的杜维明院长,邀请的嘉宾包括高全喜、朱翔非等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副教授、讲师和博士后。
他们就商业伦理的发展史、及其与全球化正义和法制的相关性、以及与儒家伦理的接榫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杜维明(开幕辞):今天我们考虑这个商业伦理,特别关于人文精神,是从比较更宽广的角度出发的——也就是从“学做人”这个基本框架,和儒家三个同时并行的发展趋向。其中一个就是,儒家是关于做人的道理,这是它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另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几千年的学术传统;再来呢,它绝对是经世致用的。
在西方的启蒙时代以后,人文的观念(如humanism)提出来,大体上是把自然和精神世界作了分裂的处理。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一个叫做“新时代的人文主义”,用的就是humanism,但它基本上是启蒙以来西方发展出来的一种凡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ty。
就是讲这个凡俗的时代,出现了把知识当作力量,对大自然的一种掠夺,这是一种掠夺性的个人中心主义。
这个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于宗教、超越等价值诉求基本上是排拒的。而我们希望从儒家的传统来考虑人文精神,是一个比较宽广的、比较有涵盖性的。那么在新的商业时代,儒家在商业伦理的问题怎么来考虑,各位都从各个不同的专业领域进行了探索。我们就这个机会,希望大家互相对话,以期在将来能进一步发展共同研究的计划,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会议。谢谢!
朱翔非:首先,我向杜先生致敬,向高教授以及在座各位请教。我在学习儒家的时候,不经意的开始接触和使用“德商”和“灵商”的词汇。“德商”在西方近十年来是比较新的话题,大约同时也开始谈论另一种“灵商”。“德商”源自九十年代的一本书《德商为什么比情商智商都重要》,提出“德商”有五条原则:不造成伤害、让事情变得更好、尊重他人、公平、友爱。
我讲儒学的时候经常用这个词,但是感到不太给力。儒学有形而上的领域,而这个词没有,都是形而下的。
我就想到了另一个“灵商”。“灵商”也是那个年代兴起的一个新概念。在科学家相继提出“智商”和“情商”的概念以后,一个英国夫妇写了一本书叫做《灵商--人的终极智力》,提出“灵商”就是人对事物本质的灵感顿悟能力的直觉思维能力。
而我们儒家会把“灵商”与“顿悟”联系起来,比如说“德”再往上就是“灵”,这就有在人文精神之外还有了宗教意义。我想这可以儒家伦理的人文宗教性作一比较。从这里看,现代的商业社会转型依然是可以与儒家的人文宗教精神结合,并受到其引领的。
王堃:当下的商业社会转型和儒家伦理的现代性转化,让我想起了高教授经常提到的休谟和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苏格兰启蒙精神。而在超越启蒙的今天,我们如何面对现实、回应和重诠现代性,是儒学艰巨的历史使命。在反思启蒙的同时,儒学已经呈现出纷纭的面相;而我试图在批判以往对儒家伦理的各种解读中,提出切合当下语境的叙事方式,使之更适应商业社会的伦理需求。
过去对儒家伦理的阐释主要包括“血亲伦理”与“德性伦理”两种,前者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然而在回应现代性上没有建树;后者则与宋明理学有诸多比较之处,这也是儒商总从晚明心学开始谈论有关。
然而晚明的“现成良知”有巨大的问题,且不限于后来对其导致的人欲滥觞的批判。心学与理学的冲突,其实依然在天理与良知之间,而这都不越过“德性”的范畴。
而这个高悬在上的德性又何来呢?的确,在对德性的批判上,休谟和斯密回到经验领域,把超越的普遍性还原到了现实的普遍性,不过这个二元的对立依然存在。这也是麦金泰尔的社群主义与休谟以来的经验自由主义长期的争端所在。而儒家则有另一条既突破理学与心学式的虚悬“德性”、同时又不至于陷入自由主义原子化个体滥觞的“中庸”进路,我称之为“诗性伦理”。
“血亲伦理”其实关注到了人的本源情感,只不过将其狭隘化为宗法血缘了。其实本源的情感不仅限于亲子之情,也包括见孺子入井的怵惕恻隐,以及一切前反思的情感,统称为“仁爱”。而这种仁爱的情感,在儒家经典中是用诗和诗学来表述的,故也可称为“诗情”。
在诗情之上“先立乎其大者”,就形成了形而上的主体性,再由此充实为形而下的伦理主体,这就是“诗性伦理”。如果说,社群主义对启蒙思想的批判在于,取代德性的个体性依然无有着落;那么儒家并不选择回到德性或理性,而是回到前主体的诗情,从中确立新的主体性(或德性),并建构出新的形而下的伦理话语。
这个主体性来自与人共处的本源情感,随着情感的流变,主体性也是可损益的,避免了德性伦理那样僵化的角色理性;而在相互关爱的诗情之上,建立起服务他人的伦理角色,又超越了自由主义的孤悬个体。因而,诗性伦理是一种群体-个体-群体的圆融构架,是对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超越。
高全喜:王堃谈了她所认同的商业伦理,重点在一种“诗性伦理”的提出,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大家的探讨都偏哲学化一点儿。当然,我想到商业伦理与人文精神,马上就会跳出中国传统思想,我们的商业社会至少在一百年之前算起,其实是不让于西方社会的。
说起来,儒家对商业的思考也是非常丰厚的,儒家如何看待物质财富、商业生产、及其商品运行中的内在规律,商人的心性要求,还有相关联的政治权力结构,等等,我觉着在这些方面有很多东西值得爬梳。
以前读过余英时关于中国商业伦理的书,也读过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的论述,这些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业属性以及商业伦理会有很大启发。我前不久写过一篇文章,参加《文史哲》关于人性论以及儒家和自由主义的研讨会。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在不同的领域关于人性的预设是不同的,例如,在家庭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商业领域,人性展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探讨时的预设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一般领域中人性善是个很好的预设,但是在政治领域中人性恶就是一个很好的预设。
同样,在商业领域,儒家怎么看待人性问题,这与在家庭血缘亲情领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商业伦理的伦理性就是协调利益与情感的关系,如何看待商业关系中的物与物的交换,在人情世界或小共同体中,和在陌生的大共同体中,其伦理原则是不同的。
财富机制的运行规则和一般的政治规则、乃至人情社会中的礼俗,会有一些张力性的关系,但财富以及商业又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的。商业伦理的形成、发生机制、尤其是这个发生机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促使儒家有几种不同的表述形态,从社会财富的需要出发来研究儒家的商业伦理比从儒家学者的人性论来探讨,更具有历史的意义。
张薇薇:王堃讲到“诗性伦理”,但我觉着诗在古希腊悲剧中,是不受伦理控制的,如果你把这个诗跟伦理粘合在一起呢有一种悖论。我们讲到伦理的时候,其实是孔子要删诗经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要驱逐诗人的。不知你的“诗情”是什么,个人欲望?我认为诗里面有一种英雄主义情怀,而英雄是超越伦理的,是反对世俗主义或者说平民主义等等。
我们喜欢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赞美美赞美英雄。所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面那么反对庸俗社会,庸俗社会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商业社会嘛。
我客观地讲,商业社会是败坏了的,是尼采说的“末人的道德”。商业道德有什么呢,就是诚信,而这就是说诗被拉下马的结局。刚才高老师说张力,我就想说张力,诗和伦理之间就像拔河那样产生张力。
那么你讲“诗性伦理”,我要批判你这个概念。因为我认为“诗性伦理”这个概念是非常温情脉脉的,但用温情脉脉的情感替代了诗。但母子之间的温情可以在孝道里面找到,却不能加以诗性。因此,我反对你这个概念。
王堃:虽说古希腊诗学与中国诗教有很多不同,不过我也承认二者有可比之处。你讲的英雄情怀与世俗情感的冲突,在儒家的“诗情”里是没有的;无论是激越超拔的宣泄,还是“温情脉脉”的亲情,都是本源的诗情,只要这种情感不是为己的私欲,而是“爱人”的本源情感。
换句话说,仁爱既可以是温柔的母子之情,也可以是舍生取义的豪情壮志,这二者的冲突在本源诗情中不存在,因为诗情是“无分别相”的。只不过,当你鄙视世俗“人欲”,高扬“英雄情怀”时,就已经进入了“分别相”。这就类似理学家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而这恰恰是可以在本源情感中消融的冲突,这也是我批判“德性伦理”的地方。
高全喜:我觉着休谟虽然没有直接谈到诗,但在几篇重要的文章里他曾经谈到审美。在休谟他们那一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中,诗与伦理不是那么截然对立的,他们其实是找到了美德、情感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某些相关性的,他们并不是像卢梭、以及后来的尼采那样把两者对立起来,把所谓的道德人文领域与商业政治领域完全对立化,而是找到了一些结合点,例如,他们都强调同情、道德情操以及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正义等,这些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第一场结束)
高全喜:儒家如何看待商业伦理,我认为应有三个层面。首先,从儒家思想的视野下,我们应该对商业社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我赞同杜先生说的,儒家对商业活动本身是非常重视的,我觉得这是第一层,首先确立儒家与商业社会的非对立关系。
第二层是什么呢?其实商业又不等于商业伦理,商业伦理这个伦理到底是怎么发生能出来的?商业伦理并不等同于一般的道德心性,在儒家的视域下,如何看待商业,如何看待在商业过程中形成的商业伦理,以及它们与一般的儒家伦理是何种关系,这是第三层面的问题。
中国社会确实面临着古今之变,以前的“商”有自己的一套规范体系,但是在历经了古今之变后的新的商业社会,由此形成的新的商业伦理和传统儒家的商业伦理有了不同。西方古希腊、罗马也有古典时期关于财富的一系列理论;近现代以降,以亚当.
斯密为代表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谈到的现代财富发生机制中的新的商业伦理,显然与西方古典社会的伦理是不同的。与此相关,儒家视域中的古典儒家对于商业的看法及形成的商业伦理也面临一个现代性的挑战,那么儒家能不能开辟出这些新的东西,这对我们当今的研究更具有现代意义。
我曾经有一篇文章,是对麦金泰尔的一个说法的反驳。他认为休谟代表的思想是对苏格兰思想的一种反动。他认为在苏格兰思想中,很类似存在着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脉脉含情的那一套伦理学说,而休谟所引入的英格兰的精神整个颠覆了苏格兰思想中的美德,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伦理体系把传统的美德社会给撅了,然后形成了人欲横流的社会。
作为社群主义的代表,这个是麦金泰尔的基本思想。我在我的《论休谟的哲学》那本书中专门回应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麦金泰尔谈到了真问题,但是他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就像我在上一场发言中谈到的,我们古典社会必须面临一个现代性的转型问题,无论是基督教传统还是古希腊以来的传统社会,它们所形成的那套美德学说,即便是公民德性学说,都是基于奴隶制之下的德性学说。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之后,人首先是要从事生产、交换、消费等商业活动,人要自立,要有一个商业社会产生,美德社会是要建立在商业社会之上的。也就是说,人首先要从事生产,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有亲情关系,才有家庭伦理,才有我和你、我和他的关系,甚至人和上帝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一个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商业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你以这个来指责休谟的话,那么你只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社群主义的基础,就像刚才王堃所谈到的,是基于一个现代经济生活之上的伦理共同体思想谱系,由于经济生活中的原子化的个人,过于沉溺于自我个体性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纽带越来越缺乏了,所以,社群主义企图重新回到一个含情脉脉的伦理生活或者说群体性生活。
但是不能忘了,社群主义的前提是在这样一个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商业社会的现实情况下,建立一个社群生活。在此,如果指责苏格兰思想揭示出一个有关现代经济活动本身就蕴含着伦理性、道德性——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是假问题,那么你的新的道德该如何建立?我认为在苏格兰思想中,尤其是休谟、亚当.
斯密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开辟出一个人在进行财富创造、经济商贸等所谓的逐利活动中,如何也能够同时在实现着正义的价值,这里就关涉一个现代性的商业伦理德问题。
当然,这就涉及到麦金泰尔与休谟的思想冲突,其实,这个问题当时在苏格兰思想中也有表现,例如,如何看待曼德维尔提出的“人人为私也可以成就公益”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看到,针对这个伦理问题,休谟和亚当.斯密他们是发展出一套伦理学,这套伦理学恰恰是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生活完全接榫的,甚至是根源于经济社会之中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不是相互割裂的,恰恰是两者互补的。一方面斯密有关于财富创造这一套经济学的市民社会论述,另一方面在这个商业社会的运行中他又建立起一种道德情操论。
休谟也是如此,经济与道德不但不对立,反而恰恰是它们的联合,为市民生活树立起一种新的道德,即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
我就觉得苏格兰思想家们的问题也是儒家视域中的中国思想界所要面临的问题,以前是士农工商,对商业活动不排斥,甚至儒家有持平之论。但是,仅仅如此,在现代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促进一种基于财富创造的社会动力因,寻求培育一种现代经济社会的动力机制,而不仅只是满足于国民富足,不排斥商业活动,这是儒家需要应对现代性的新问题,具体一点说,把古典的义利关于转化为现代性的义利关系,为经济社会的“利”找出“义”的正当性,转化为一种财产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就是儒家义利观的古今之变。
就像刚才杜先生讲的,以前士农工商不分轩轾,但是到了现代生活,商业是一个社会主体的动力机制,在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商品交换以及价值分配等一系列经济过程当中,如何使得现代的社会富有生机,这就需要儒家给予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说明。我认为这才是儒家的开新。
前面谈到的两个层次,都面临着法制问题,法制在第一个层面比较好理解。因为这个法制就是现在的这个国家法制。在国家法制的统辖下,大家遵守之,从事一般的生产与交换,都知道要守法,要有诚信,所以,关于商业的伦理规则,很多是民法意义上的,这些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上显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代的商业社会,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除了商业伦理之外,还有一个法治社会问题。这个法治是rule of law,不是ruled by law(法制)。
法治社会最核心的方面,就是要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因此,也是一个现代的宪政体制问题。没有法治与宪政的制度基础,现代的商业社会也就根本没法成立。只有在宪政框架下,才有所谓个人的心性问题。
个人的心性问题是一己之学,作为一个商人,在法治社会中也可能做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对于整个经济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法治社会或缺的话,哪问题就大了,商人的道德再高尚,也不能达成一个富有活力的商品经济社会。
所以,法治社会的建设,对于儒家来说就是一个有关商业伦理的新命题,传统儒家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既能接榫传统又能开出法治的新型商业伦理的话,那就只能是一个传统之学,对于商业伦理具有某些思想资源的补充作用,成为不了现代社会的主流伦理。
反观一下苏格兰思想,它们作为一种接续传统道德哲学的思想,它们的成功在于富有活力地把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的商业进程和法治进程联系在一起,最终变成了一套活的理论,为现代社会的财富生产提供了一种道德性与伦理性的证成,从而塑造了一种现代社会的文明理论。
相比之下,现代儒家的成就就非常薄弱,当然,其历史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儒家想要变得富有生命力,那就必须真正面对商业社会中的财产权问题,面对国家公权力的权力制约问题,并给予基于儒家思想立场的回答。
蒋孝军:我的发言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原始儒家的义利观,第二个部分谈皇权时代的义利观与商人地位的改变,第三个部分谈近代以来商人角色的改变。当然也谈近代以来中国如何处理高老师谈到的宪政问题、商人地位和独立性的问题。
在我看来,孔子的义利观跟皇权时代的义利观是不一样的。孔子虽然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他并没有否定“利”的意义,而是以义处利。他对赞叹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也有“当道者益事”“谋道不谋食”的观点。
在春秋时代,商人地位很复杂,既有陶朱公,子贡等周游列国,富甲天下的商人,也有《管子》里面所提到的“士农工商”的划分,就是说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个严格的安排。而当时诸侯国之间商人来来往往很频繁,商人的地位是非常自由的,也就是“士有游士,商有游商”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原始儒家对于商人的态度比较开放。
第二部分是到了皇权时代,出现义利观和商人地位的下降。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非常明确地谈到了“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说与民争利。在司马迁的观点里面,与民争利是政治最次的一个状态了。
但是正是在司马迁的这个时代,有东郭咸阳,有孔仅,有桑弘羊,特别是在《盐铁论》里谈到了他们跟那些贤良们的争论。《盐铁论》里面的贤良就是儒生,儒生在跟这些官僚们讨论的时候,儒生是很强调老百姓(603883)的财富的,他们认为桑弘羊的做法其实就是与民争利,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看出儒家的态度,儒家对义利观的态度还是不与民争利的。
但汉武帝的这种行为其实是改变了这种状态,因为当时有一个大一统的需要,这导致了《盐铁论》之后国营的加强;而国营的加强其实就是,大一统成了商业活动的中心。
唐宋的儒生已经慢慢地接受了大一统的商业观念,所以有了后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商人当做了仅仅是利的代表。商人,特别是在宋明理学里面,成了一个先天的道德缺失的群体。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同情的理解,因为皇权时代的商人本身就有一种依附性,对皇权的依附性。
他的依附性会导致他剥夺百姓,与民争利。所以,宋明理学认为商人先天的道德缺失。如果再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到晚明,余英时先生也在谈晚明时期商人角色的变换。有人认为,余英时谈到的商人变化始于元代,因为元代中国的士人已经不可能从政治权力那里获得生活的资源了,所以只能经商。
从此,尤其是在明清之际,商人慢慢地获得了自我认同,而不再是道德先天缺失的群体。商业伦理如诚信、如公益事业开始发展起来,甚至很多人认为商人可能比当时的士做的还要好。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认同余英时的观点。中国的商业伦理开始在这个时代自足自立起来,这就是我对前现代的中国商人的地位的一个分析。
第三部分是谈近代以来商人角色的变化和宪政的关系。自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后,中国社会一直有一个救亡的倾向,在这个救亡的倾向里面,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他的伦理关系一直被爱国的情绪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民党时代,蒋介石如何对上海商人做出的那一切要求,比如你要爱国,你要捐出你的资产这样那样的要求,商人的伦理独立性,地位独立性自近代以来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可以说还落后于明代。
那倒1949年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商人的地位是一落千丈的。
应该说一直到今天,商人的依附性地位一直很严重。我们一开始谈到的红顶商人,说白了就是一个买办。如果我们刚才高老师谈到的苏格兰的情况,我也非常认同亚当.
斯密的说法,即英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社会。不光是亚当.斯密有这样的观点,贡斯当在他的文章里也谈到了,“商业甚至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解放个人,它还通过商业信誉将权力本身置于依附地位”。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在中国一千多年来,商业是依附于权力的;而在贡斯当那里,他明确地提出权力是依附于商业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古今之变。
网上应该有高老师的一篇文章,讲古今之变高于中西之异,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对照西方社会,怎么建设商业伦理?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独立性的确定。
商人的独立性,必须要独立于权力。这个当然很困难,因为今天能挣钱的基本上都不独立,能明显感觉到是跟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和高老师一样谈到商业与宪政的关系,高老师可能会谈权力的制衡,而我会从商人角度来谈宪政。
我觉得个人与国家之间缺了一环,就是社会这一环,用西方的话语就是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社会独立了,才能够真正的制衡权力。只有商人独立了,才会导致宪政的确立。
同时我就会想到儒家自身的独立性。这就回到了儒商结合的社会路线,儒商结合恰好就是要发展出儒家自身的独立性。有了这种独立性,整个社会基础才会变成商业社会这样一种结构。社会路线是儒家的一种下行路线,即走下行,跟商人结合。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像西方一样进入了真正的现代状态,然后我们再来思考,儒家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怎么应对、甚至批评现代社会,这一点我觉得是我的一个思考吧。
王堃:我最近读到高全喜老师的一篇文章:《理解博丹主权论的三重视角》。据我所知,过去您一直在讲宪政,而现在您开始探讨主权的问题了,而我对主权和人权的关系问题也是很关注的。我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原来师从安乐哲老师,现在师从杜维明老师,因此我其实更认同社群主义,只不过觉得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并不矛盾,希望二者可以结合起来。
自由主义者的精神显然是注重人权的保障,如您刚才所讲的宪政法制,都是现代商业社会所必须的保障;而注重人权就意味着约束公权力,以免公权力以某种借口向个人权利进行殖民。
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里,主权却往往担任了一个类似的借口,因而人权与主权的讨论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在您的那篇关于主权论的文章里,我发现您对自由主义价值与主权的冲突似乎作了某种化解,那么这个化解的基础在那里,目的又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谈到休谟开创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并非如麦金泰尔所说的那样颠覆了美德传统,而是继往开来的发展出了与商业社会切合的新道德,而儒家这点没有做好。
我对此的确也承认,儒家的传统心性学,比如我举的王艮现成良知的例子,曾与此失之交臂;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如何面对现代性也依然是儒家的困境。
这也正是我提出“诗性伦理”的原因。与“德性伦理”不同,它不是要求人在现成的天理良知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而是把回溯到前主体的诗情体验中重塑自己的良知,也就是从当下共同生活的情境中重新确立主体性道德。
当下的生活情境是商业社会,那么从中确立的就是商业伦理道德,再以此为基础发展责任、权利,并制定法律来保障个体权利。这与您所说的道德、财富、法律三层次并不矛盾,儒家只有越过了德性的坎,回到情感的本源,就可以同样开出新的公民道德。
蒋孝军:您所说的这一点,其实我的内心里是非常的欣赏赞同。刚才我讲到晚明时没有明晰的表达出来,但是我也提到了晚明的商业繁荣不是资本主义。王艮所说的良知现成,商人就应该干经商的事情,好像很支持商业;但是王阳明以及阳明后学的良知都是含有皇权制度下特有的纲常伦理的。
也就是说,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的那套政治体制下,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已经被涵盖在“现成良知”中了。王艮所说的商人就该干商人的事,其中就暗含着商人要领会到自己的地位,其实你是要向权力屈服的,所以只能在商言商,不能去思考别的。
这种现成良知之所以导致后来的个人纵欲,其实就在于当它给商人安置了相对主体的同时,却没有给他们相应的绝对主体;而过时的道德主体由于只在少数人那里才能确立,即使商人主体代表着巨大财富,也只能以妾妇之道依附于权力,而不具有自行的道德主体性。
因此,这种现成良知反而酿成了一种恶果。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是一个绝对的主体,这个绝对的主体是有普遍性的。而王艮所说的主体良知就不是绝对的主体,你不能说自己在商言商,做一个小商人,除了赚钱就什么不管了,那么这不是绝对的道德主体,不是今天商人应有的主体。
杜维明(总结辞):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什么社会,从全球来看,没办法定义。原因是今天碰到的危机是人的存活的危机,在这个存活的危机出现以后,再加上金融风暴代表的不是一般的社会,而是金融;它是几秒钟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几秒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很多经济文明,从轴心时期以来的精神文明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它们做反思的时候得到的资源是它自己的文化资源,比如哈贝马斯基本上是一个康德的哲学的背景下,而新教是美国、伊斯兰世界所碰到的问题。
我们现在要走的这条路,不可能是具有中国特色而与世界文明不交接的独立路线。我们今天要走的路,假如是条中国路,它必须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前提之下;不仅是西方,印度,非洲都得认同,而是人类要重新学习人是什么,必须在一个大的世界文化背景下。
现在出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比如这次气候会议是比较成功的,比哥本哈根的那次好多了。在他之前有一个法国总统推行的良知高峰会议,就是所有人谈良知问题,他们叫conscience,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良知理性的问题。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完全和现代商业没社会关系,这是人类之存活,经过那么长时间,包括很多原住民,他们的精神资源都出现了。所以在政治建构各方面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有开阔的心胸,就各个不同的资源都可以用。
另一方面呢,就是批判的能力,这是独立人格的必要条件。看到我们周围儒学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有些机会很多也是陷阱。韦伯说的资本主义兴起,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新教所代表的基督教伦理的崩溃,所以后来他用一个铁笼比喻,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铁笼。
现在我们还不是一个铁笼,我们是一个救生艇,漏的很厉害的一个救生艇。所以在这个大的前提下面,所有其他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如儒学作为一种全面性的思维,该怎么样子来讨论才比较平和和宽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