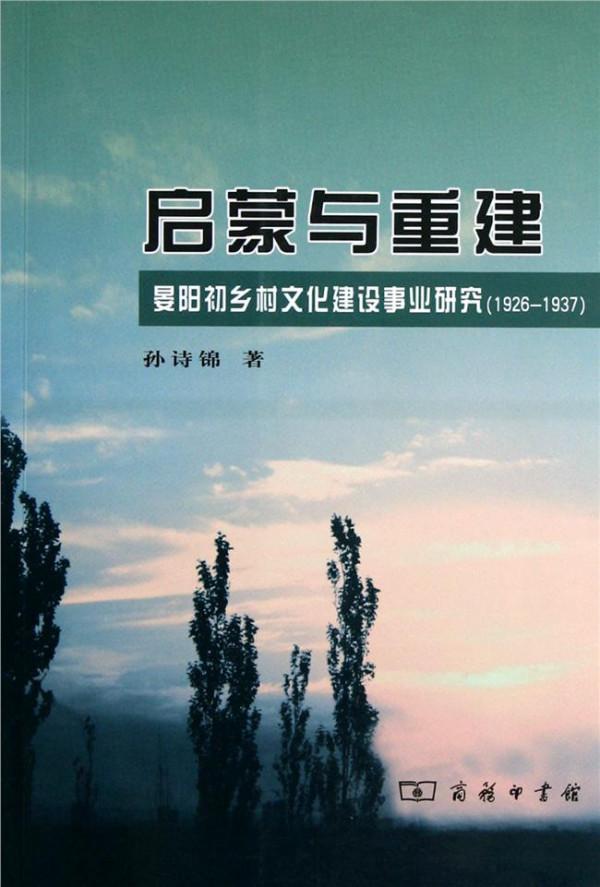罗家伦名言 【名家后人谈名校】罗家伦在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节选
(编者按:著名教育家罗家伦毕业于北大,1928年担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1932年,又担任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校长,长达10年。这是他最人生最成熟的一个阶段,为中央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七七”事变,使他许多长远规划未能实现。现将历史学家罗久芳老师文章的有关部分介绍给大家。
父亲1932年8月就任中央大学校长,1941年7月辞职照准,总共任职九个学年,十个年头。当初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澎湃,面临解散危机。同年8月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他出任校长时,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先生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相责”,使他深感“不忍在国难期间,漠视艰危而不顾”。
于是抱着“个人牺牲非所当惜”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务,从此为了在中央大学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奉献了他宝贵的壮年。
那段时期,正是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父亲是研究历史的人,自然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使命感也就格外强烈。他在中大所作出的努力及获得的成就,不仅自己留下了丰富的纪录,许多同事和校友们也都写过详细的回忆,为校史的编撰人提供充足的资料,作出了公允的论述。
但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愈看得清楚。”从现今的眼光来看他主持中大的岁月,最突出的两件事,是他对大学使命的理念,以及对大学校长职责的定位。
1932年开学后他第一次对中大师生的演讲,题目便是“中央大学之使命”。他认为“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可以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
”他例举拿破仑战争以后,普法战争以前德意志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除了政治和军事的改革外,柏林大学的学者对于德国民族精神再造的贡献和影响最为关键。为此他希望中央大学能向柏林大学看齐,并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详为阐释,以期与全体师生互相勉励。
父亲原先计划把他治校的方针分成“安定”、“充实”、“发展”三个阶段来实行,每段约略三年。一开始他便利用每星期一举行的“总理纪念周”集会,就学校的进展情形、国内现状和国际局势,详细报告和分析,使学生对国家、世界的处境有所认识。
1935年4月,他首次在中大提出了“中国与近代化”这个主题,指出“一个国家,要能够独立存在于现在的世界上,就非经过近代化不可。”而近代化(后来改用“现代化”)三方面的意义是:用科学的方法,以改造物质的环境;用科学的方法,以支配社会的组织;用科学的方法,以支配人的思想与生活。
1936年9月至11月,他又为全校作了一系列的演讲,题目是“近代文化概论”,分七次讲完,综合起来是一长篇有系统的论说。
目的是希望对全校各院系的学生发生启迪性的作用。当时父亲应邀对社会各界的演讲一年比一年增多,“现代意识”和“科学方法”这个主题,无论在校内或是校外、在战前、战时或是战后,都经常出现在他的讲词内。
正当中央大学进入“发展”的阶段时,“七七事变”迫使它长途迁校到后方。父亲除了应付战火下繁忙、紧急的事务外,纪念周和其他校内集会上的演讲,成了他固定与学生接触的渠道,连柏溪分校的一年级学生,也经常能听到他的演说。
1938年初,父亲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新人生观”的三点内涵:(一)动的人生观,(二)创造的人生观,(三)大我的人生观。后来又作了十五次系列的演讲,修订成集,取名《新人生观》,1942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他“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的礼物。
这本书出版后五年之中,一共再版了二十七次,成为全国青年热爱的畅销书。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仍然在各地再版、发行。其中父亲所提倡的“理想”、“智慧”和“人格”三个力量,以及“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运动家的风度”、“文化的修养”等观念,至今仍是中国人迫切需要培养的。
1935年父亲为中大作的校歌词中,有“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几句话。
1941年他在离职惜别会上,向中大师生表示未能达到这个理想而惭愧。但是“百年树人”的工作,本来是长期的奋斗。2002年南京大学庆祝百年校庆时,有人提议将当年父亲选用的“诚朴雄伟”和校歌里的“励学敦行”八个字作为校训。可见他所号召的精神,并未随时光而消失。
在贫困匮乏的抗战时期,父亲一方面在校内力图激发学生的对振兴民族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不忘设法引导后方知识界的舆论。1938年,他采用了当年北大师长创办《每周评论》的模式,与一批中大同事编印《新民族》周刊,目的是要讨论“现实的政治、社会、国际、教育等问题”。
发刊词指出,“《新民族》不但应当讨论战时有用的问题,并且应当讨论战后建设的问题”。他本人除担任主编外,一年多中撰写了二百六十多篇短评。这个杂志一共出版了64期,直到1939年5月4日重庆遭到日本大轰炸,才因印刷发生困难而停刊。
父亲从中大卸任后,选出他为《新民族》撰写的19篇时论与短评,于1943年印成一本取名《黑云暴雨到明霞》的小书,来代表他“对国是一贯的主张”。
1945年,父亲综合他在中大所作部分演讲纪录,以及在《新民族》中发表过的一些文章,重新编写成一本“广泛式的民族哲学”,取名为《新民族观》。他在9月9日“受降日”那天写的自序中说:“当这转败为胜,转弱为强的关键,也就是我们民族返老还童、起死回生的时机,时机是稍纵即逝的,我们千万不可错过!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民族表现的各方面,应当重新认识,重新反省,重新估价。我们要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他的热诚与期望,仍然是北大时代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延续。
1941年父亲离开中大的时候,可以说已经心力交瘁。但是他在惜别会中,还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学生不要太看重现实而失去了理想;学校不要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忽视了其整个人生的修养;不要把青年的知识造就好了,而身体却弄坏了;希望大家要为科学的真理而奋斗,要走到现代化的路上去。
父亲为了人才的培养,贡献了他精力旺盛的年华。后来即使远离了教育行政的岗位,他仍然念念不忘对青年的关注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