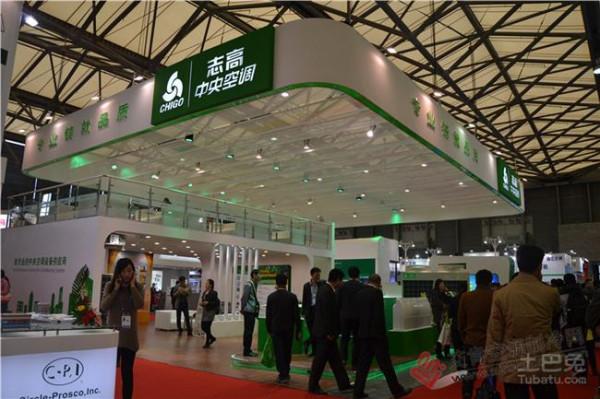张承志李陀 张承志:公开与隐匿之间的思想张力
今年《张承志文集》出版。行走在主流文坛之外的张承志,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思潮研究所“当代小说国际工作坊”的讨论主题。在这个多数人因信仰缺失而患了“软骨病”的时代,在民族主义泛滥的当下,探寻张承志的思想世界或许激发我们新的思考。
1,《心灵史》:让我们知道在历史中的位置,知道怎样行动
杨晓帆(中国人民大学):
《心灵史》是张承志在1989年写成的,2010年出了一个改订本。在89年的《心灵史》版本出来后,有评论认为张承志所叙述的宗教史,和民族国家叙事框架内的历史,格格不入。在这个版本里,张承志的确更多地专注于叙述哲合忍耶教这一个独特群体的历史,他们怎样被压迫,怎样抗争。但是到了2010年的修改版中,我注意到几个非常突出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有了一个明确的历史参照。在89年版中,张承志几乎没有提到他自己的红卫兵身份和60年代经验,但是在改订本里,他在前言部分就强调说“我是伟大的60年代的儿子”,写这部书就是缘起于那个“时代的败北”。
“时代的败北”是什么?张承志在这里使用的历史参照是八九十年代,60年代革命失败后的所有后果都体现在八九十年代的历史展开中。
我们可以从张承志的散文随笔中读到他关于“败北”的认识:首先是大面积地清算革命,对革命的污名化;然后是“经济上的发展主义”,就是一切往“钱”看;第三个是官僚体制的修复,这个跟“文革”时期强调的“造反”、打破一切官僚体制是完全相反的;第四个就是文学界虚假的人道主义、粉饰西方,以及学术重建过程中过度偏向考据,知识界对政治生活的脱离。
张承志在《心灵史》改订版前言里说,“这是我面对的历史的问题”,当他有了这样一个历史参照后,他对于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才可以认识得更加清晰。
所以他在叙述哲合忍耶教时说,“这是与中国革命共生的悲剧”。这一点在初定版中是看不到的,当他叙述一个宗教的历史的时候,他其实在思考我们关于革命的认识,关于中国自身历史的认识。这一点在改定版中出现,我觉得特别重要。
第二个变化是张承志在改订版里特别强调哲合忍耶教的阶级色彩。“阶级性”、“阶级色彩”这种词在初定版里从未出现(编者按:不确。第一版即提出了“穷人宗教”的概念。),但是在改订版里出现了。在初定版里张承志虽然也强调哲合忍耶来自于贫苦的底层,但是当他没有一个从60年代出来的阶级逻辑时,就不会表达得这样明确。
在改订版里,张承志特别强调,哲合忍耶教是底层农民,他们面对的是三座大山,神权压迫、阶级对立和人身控制,他们都是受迫害的民众。
在阅读时,一开始我会觉得特别有隔膜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回族教民,而很多词汇比如“农民”、“人民”,好像跟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或者左翼文学特别相近,你会怀疑他怎么能把这些不同群体放到同一个阶级的逻辑中去。
但是后来我读到张承志把哲合忍耶教说成是一个“穷人的宗教”。在他的叙述背后有一个新的历史参照,他说“伊斯兰一直在与高利贷与资本主义抗争”,他把伊斯兰放到了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对抗的历史逻辑中去,而60年代也同样处于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对抗的逻辑里。
通过这样一个对接,他就把对伊斯兰、对哲合忍耶教的理解都放到了所谓“人民共同体”的认识中了。这是通过阶级逻辑和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叙事来完成的。
《心灵史》好像在讲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就像程老师说的,这是一部关于良心的小说,怎样去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摆脱了低级趣味的人,即张承志所讲的“基本的正义”。但如果这个正义只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就会面临类似刚出版时邓晓芒式的质疑:你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形式跟智识界所讲的爱心、美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所以,《心灵史》的写作又特别强调具体的历史情境,以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为参照,让小说的理想性获得一个比较具体的形式。
《心灵史》里提到,“我叙述哲合忍耶教,我只从清末一直叙述到1920年,1920年以后的哲合忍耶教的历史我不叙述。”
他为什么不叙述?因为1920年以后的教派史必然会跟中国的革命史重合,重合时就面临怎样判断和分析革命史内部对于宗教的处理问题,也就是怎样评价革命。张承志明确地说过,“狗尾续貂不仅并无意义,而且有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工程之一砖半瓦的危险。”他意识到如果叙述1920年后的历史,就有可能以我们现在对革命污名化的态度去迎合世界资本主义,是拆自己的台。
这里体现了我所说的“公开”与“隐匿”之间的思想张力,张承志在小心绕开两个陷阱:一是他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同时又要讲反美、抵抗全球化,所以他要强调国际主义的部分;二是国内的左派资源有历史问题,所以他选择穆斯林,以《心灵史》义卖到巴勒斯坦的行为,来激活60年代经验。正如他所说,“我们在60年代有两件事情特别能够代表红卫兵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抗美援越,另外一个就是巴勒斯坦问题。”
从80年代写作到《心灵史》,抒情的位置一直被保留下来,张承志通过不断的历史叙述去给他的“理想主义”提供新的内容。他不是抽象地停留在人文精神或者人道主义的层面,而是不断有新的历史叙述参与进来,让抒情性、理想性变得更加丰富,更能动态地与现实对话。
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就像他即使叙述哲合忍耶教的历史,这个宗教形式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动态的,是可以被不断填充新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灵史》给出的不仅是一个历史叙述,它提供的还是一种历史结构,让我们知道在历史中的位置,知道怎样行动。
2,在每一个阶段寻找的东西都不一样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
我简单地讲一下。我发现“80后”在面对我们“50后”时有他们的困难。
关于“我”的遭遇,80年代“我”建立起来后,到90年代就没了。“我”在80年代是文学的中心,也不能叫自我,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概念,需要好好界定一下,到90年代文学“我”变得非常弱了,变得暧昧不清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研究张承志,比如他和红卫兵的关系,他和80、90年代的关系。晓帆提出来的问题还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一代人总体性的东西,好像张承志那一代一直在无言地抵抗、无言地坚持、无言地思想,他在坚持的东西有没有意义,我觉得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张承志的写作有一种功能性,折射出80年代中国很多问题,无论知识分子问题、历史问题,还是历史走向和选择的问题。张承志代表着的,可能是“50后”失去的总体性的问题。我自己还没有想的很清楚,我想听听李老师的想法。
李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一个作家问题越多,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一般来说他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但不见得是我们最喜欢的作家,比如,路遥好像是个单薄的作家,深入讨论后发现他身上背着一堆的问题。
刘禾(清华大学):
晓帆提出了一个关键,即如何进入张承志的写作,他的文字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
但你的这个“我”字啊,恐怕不能望文生义。比如北岛有一首诗叫《履历》,仔细研究一下那个“我”字,它可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单数,而是指一群人,虽然汉字写下的是“我”,而不是“我们”,但概念上其实是复数。从北岛这里,我们也许能获得一点启发,然后再回过头认识张承志作品里的“我”。
另外,张承志是一个史学家,不过,不是那种只会挖材料、搞文献的史学家,他比那些史学家要高明;同时他又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作家,比我们读过的绝大多数小说家都高明。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思想是没有边界的。
大家提到他的国际主义,很对。他的确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去思考宗教问题、国家问题以及人民的利益问题。张承志曾经背着包,沿地中海走了一大圈,他的走法不是去住五星宾馆,是和当地的穆斯林联络,住在比较便宜的地方,去体察那里老百姓的生活。张承志思考的问题非常广阔,从中世纪的西班牙,19世纪的中国大西北,到当代的资本主义,这些全都在他的视野里。因此,他的创作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小说写作。
李陀: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的写作阶段的时候,他征用我们中华民族古典资源的时候,所体现的那个思想里有没有民族主义。因为“以笔为旗”那个阶段跟他后来明确地说把这种资源用来反对消费主义、反对全球化,进一步后来变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们现在需要把张承志从《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黑骏马》到《金牧场》到《以笔为旗》,再到放弃小说写作,写作《鲜花与废墟》到《珍重与惜别》,这各个阶段都要认真研究。
这一系列的写作过程,也展现了他思想变化的复杂情形,还有他对民族主义、民族文化的讨论,要打开,要仔细分述。
张承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作家,这么复杂的作家在咱们中国文学史里不多。他一直在寻找,而且他在每个阶段寻找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他改变自己。比如说他早期的写作在民族主义上有没有和国家有合流的地方?但是张承志复杂性在哪?就是他刚有这样一个倾向,他马上就醒悟、就反省,调整自己的姿态,调整自己和古典文化资源的关系,调整自己和红色传统的关系,调整自己和左翼思想传统的关系,然后用一个更新的姿态进入写作。
像他这么辛苦地不断在“寻找”的作家,在中国不多。他是一个知道什么叫痛苦的作家。你们都触及了他内心煎熬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需要再深入挖掘,他内心的痛苦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国作家里,很多人都是真理在握,对什么都有答案,中国应该往哪里走?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他们全都有答案。
刘禾:
而且他们满足于用文字来浮光掠影地描述,没有什么思考。
李陀:
对,所以像张承志这样一直在寻找的作家不多。我也不是说,没有在寻找的作家一定写得不好,只不过类型不一样,给文学提供的意义不一样。我们要对不同类型作家所提供的意义做分门别类的研究,不能说某种类型写作就一定好,某种类型写作就一定不好。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批评家,批评应该有温度,批评不能那么冷静的。
我是张承志的老朋友,我最没想到的是,他寻找来寻找去,最后这么坚定地皈依了伊斯兰文化,他的皈依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个理解过程。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我被他逼的不得不重新考虑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认识伊斯兰文化。这个问题本来在我的视野里是不存在的,我只熟悉基督教文化,我也熟悉中国的文化,但伊斯兰文化对于我来说是在视野之外的,是小布什发动了几场战争,使全中国的人,或者说全世界有良心的人都在重新思考伊斯兰。
张承志比我们走得远,他很早就开始在《心灵史》的写作中考虑伊斯兰文化的问题。只不过他不像我们有些人一讲伊斯兰文化就开始云缠雾绕了,他就从哲合忍耶这么一个伊斯兰的小派别进入它的历史、它的苦难、它的意义、它的信仰,然后把自己放进去,我站在哪儿?我跟哲合忍耶什么关系?从哲合忍耶再认识伊斯兰文化。
张承志这点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要考虑在中西之外还有一个伟大的文化存在。
3,民族主义把张承志简单化
刘禾:
90年代《心灵史》出版后,很多人批评他,说他是民族主义。不幸的是,民族主义的标签被人乱插,也把张承志简单化了。
李陀:
咱们将来讨论张承志的时候,民族主义也可以当一个环节来讨论,民族主义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作用是好的,有时候作用是坏的。这是由历史形势来决定的。现在的一些公知们啊,动不动就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好像很简单,其实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刘禾:
二战前后,民族主义是像现在伊斯兰一样,是站在抵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前线的,当时民族国家独立运动是唯一能够用来脱殖的思想资源,那个时候没有其他思想资源,除了国际主义,但国际主义最后不得不向民族主义妥协,转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这种关系在历史中是不断变化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走向自己的反面,它没有固定的历史意义,永远处在各种变动的关系之中。我们今天生活在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里面,大家靠什么抵抗帝国主义?如果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当今的思想资源,难道国家主义是必要的选择吗?这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
李陀:
二战以后,亚非拉的脱殖运动,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话,就没有民族解放运动。
刘禾: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民族解放运动的话,很多地区那就无法摆脱殖民地,或者有效地组织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二战后,很多新兴的民族国家开始进入历史舞台,就是这个道理。
李陀:
简洁地说,如果民族主义一旦和国家主义结合,这个民族主义一定是坏东西。
刘禾:
因此泛泛地说张承志是民族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李陀:
但是张承志的民族主义是可以讨论的,张承志和民族主义是摘不开的。这里还涉及对民族的定义问题,中华民族不是西方民族国家的那个民族。民族的概念是可以创造的,你可以说中华民族在nation这个定义里不是一个民族,50多个民族混在一起,但是历史又规定它是一个民族,这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