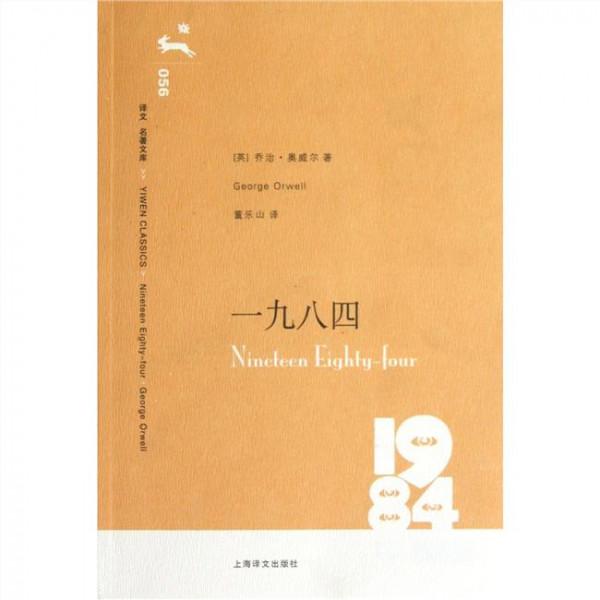李程远北大 转载 李程远:我与北大
这是写给北大的告别文,正如论文的最后总该有一章致谢,一段生活的结束,也该 有一份对这份生活的回望。我于2010年9月来到北京大学,在这里,我生活了五年,这五 年生活的点滴未必都是在北大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然而,随着在这段生活里与北大的交集 越多,我在这份生活中的投举之间,北大的印记和气息也日渐浓厚。就好像当我身处海外 给我的学术同侪讨论研究时,北大依然在我身后隐约浮现。
从绩点和履历的角度看,我来到北大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差生:相比其它高校 来比拼的同学都是他们年级中的数一数二,我的绩点在自己的小班都只排名中游;那时我 唯一的英语成绩是刚及格的大学四级,而只到保研流程结束后近半年,我才以勉强及格的 成绩通过大学英语六级;四方来争的大学生们都拥有扎实的科研经历,尤其是北大自己的 一些本科生,有人当时已经有了SCI文章数13篇的惊人纪录,而我当时的唯一科研经历就 是本科学校支持的仅3000元的项目,且最后不了了之结束。
就是那样子的我,被北大选中 了。
最初来到燕园,我依然带着中学时代坎坷经历留下的戾气,和我一同来到北大的两 位同班同学当时对我有些畏惧,因为我与他们的本科相处中,态度是非常冷漠和攻击的。 我依然记得后来听人说,其中的一位男同学当时特别担心和我同一个宿舍,因为他知道, 程远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人;而很久以后,另一位女同学也曾对我说,她发现我来北大之 后给他们的印象与本科相比变了好多。
我并没有因北大的特殊垂青而立刻创造奇迹,第一次博士英语考试,我以六百多 人中排五百六十多名的成绩交出了我给北大的第一张答卷,毫无疑问地,这注定了我的起 步必须付出更多艰辛。当时,我待人并不温和,尤其是对于那些感情丰富的同学,我倾向 于攻击嘲讽,我的一个同学曾因此被我刺痛到流泪。
我喜欢熬夜翘课,当时吴学兵老师教 授的《辐射机制》安排在周五的上午第一节,而当时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又是 联合授课的,因此我的同学们都不得不忍着北京冬天早晨的严寒,骑车赶往保福寺桥的中 科院上课,而我则是他们中最爱翘课的那一位。
第一次上吴学兵老师的《活动星系核》的课,我没有好好准备,轮到我讲那一章 时,我直接把光变忽略了,吴老师语气加重了,指出我根本没认真准备:我吓懵了,那个 时候,面临自己和同学的差距,甚至和北大的那些聪明的本科生的差距,尽管我外表骄傲 ,内心实际上是危如累卵的。
和我本科来自同一个大学的左文文师姐帮了我,她跟吴老师 说她下一次帮我把这一章补上,就这样,我遭到了来到北大的第一次警告——吴老师说, 这次因为有师姐帮我就算了,但回头我必须认真把这一节补上,我连忙答应。
天文学一年级的博士生没有导师,当时除了时任副主任的刘富坤老师,没有任何 人限制我们,我便白天放肆睡,晚上瞎熬夜,节假日自己给自己延长假期。当时我的一些 同学,已经和他们早已工作在一起的导师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而我还在各个课题组之间游 走。
2011年清明节三天假,我擅自延长假期回家待了一个礼拜,结果遇到导师学生双向选 择会议,那是一年级的天文学研究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很自然地,我缺席了,刘老师在 邮件中给出了公开警告,他同时把批评转发给了班主任和当时我心目中想合作的范祖辉老 师。
介于我回母校后认错态度较好,老师们没有继续追究,但很自然地,我被范老师拒绝 了,我愤懑不平,内心又悲伤失落。我的另一个师姐对我说,来他们组吧,Richard希望 有个博士生,人也很好,于是我便去找到了我现在的导师,来自荷兰的Richard de Grijs老师。
我对自己没有信心,这里的人太优秀了,我发现来到北大是个错误,我的外表强 大并不能掩盖我和周围人之间巨大的鸿沟。我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要请教导师,于是, 便有了我在另一篇文章《怎样完成自己的博士生涯》一文中提到过的导师的警告,我听说 过一些北大的学生因种种原因被退学的故事,现在,我已经被前一个导师拒绝过了一次, 没来多久又被现在的导师批评了,我相当害怕。
我第二天来到了Richard的办公室,他对 我说,在西方人们说话很直率,他的话听起来刺耳,是因为确实希望我能成为独立的科学 家,他告诉我,犯错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推翻一切重新再来的勇气。
我将信将疑地点 头,现在我知道,Richard当时说的是真话,他并不讨厌我,我当时的害怕基于我内心对 自己的怀疑和卑微。
我熬夜更厉害了,尽管受过刘老师第一次警告后,我不再频繁离校,但逢寒暑假,我走得 甚至比本科生还早:因为内心的恐惧,我在北大压力太大,我希望多回家和当时的女朋友 (现在的妻子)在一起。尽管在她面前,我也很少把自己内心的害怕说出来,但离开北大 ,我觉得安全。
Richard看在眼里,也并未多说什么,后来,Richard说,他一直把我看作 同事,我拥有处置自己生活的权利,但我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如果我真的因此没 法毕业,那他也不会觉得负有多大责任,我是一个成年人,我是独立和自由的。
随着熬夜越来越厉害,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2011年年底,我罹患恐慌症,对我来说,这 不是什么新东西:在我高三和大三压力最大那两年,这病也曾折磨我整年整月。恐慌袭来 时,我会突然觉得周围的世界天旋地转,呼吸急促,仿佛一股气在身体里四处流动,我没 法做任何事情,事实上,那就是濒死感。
我检查了心脏、头部CT、血压、甲状腺激素,医 生曾多次想给我开出高血压确诊标签,却总因为下一次恢复正常又不得不填成疑似(高血 压需要连续三次在一天不同的时候均高方可确诊),我又被校医院检查出疑似甲亢转诊北 医三院,复查却又给出阴性结果。
我饱受折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给我在医学上宣判 一场重病反而是个解脱——那样我就不用担心自己会倒下了,因为我已经倒下了……
2012年3月1日,我寻找了心理医生,治疗我的医生是北大的一位心理临床的博士研究生, 是的,没错,当时她也还没毕业。就这样,如同上个世纪弗洛伊德致信爱因斯坦想为他作 心理分析,一位心理系的博士研究生,就这样给一位天体物理的博士研究生展开了长达三 年多的治疗。
如你们能想象的,未来的三年时间,我们的相处跌宕起伏,其中爆发的情绪 时而绵延婉转、时而荡气回肠:其中充满了欢笑、哭泣、还有我习惯性的用骄傲理性与她 的温柔包容相对抗。
我的所有故事都留在了那间封闭的屋子里:小时候父母之间的恐怖战 争、妈妈两次离家出走带来的巨大悲伤、父母分离之后我进入叛逆期,内心巨大的委屈和 愤怒让我赶走了父亲、随后我被迫一个人居住在小混混满街游荡的市井小巷里……当时,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朋友、家人、北大的老师和同学、还有心理医生,因此,我 充满暴戾,内心充满挑战和刺伤周围人的能量——我在北大的最初几年如同带刺的荆棘, 自我保护成为了掩藏在理性之下我需要关注的一切。
心理医生的稳定支持改变了我,无论我怎么挑战攻击,她始终坐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听我 哭听我笑,听我诉说当年的委屈和那些来之不易的温暖和骄傲。我开始重新感受世界,那 一年我开始改变:我开始锻炼身体、改变睡眠,我开始踏踏实实学习、我告诉自己,即使 失败了也没关系,我可以重新再来。
我开始发现,即使我做得不好,那些批评过我的老师 们也不会因此而放弃我,我的导师依然对我友好,我的女友依然对我不离不弃,我的心理 医生依然会守在那里等我回来。
之后的一次年度报告前,我和刘富坤老师爆发冲突——缘 于我的进展报告被他要求重写,我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下“该死的富坤!”,那一刻,我仿 佛看到心理医生在身边说:是什么让你这么愤怒?我被击中了,我再次看到了自己的怯懦 和脆弱,我把年幼的苦难带到了今天,并用想它来攻击身边的人。
师姐拼命劝我不要抗争 ,我静了下来,下午,我来到刘老师办公室低头认错,我忘了对他保持作为学生的尊重, 我请求他原谅,刘老师原谅了我,还向我解释了为何对我们要求如此之严——他说了足足 一个小时,他本不必要为我花费这么多时间的。
我的科研开始起色,我的第一篇文章犯了许多错误,因此还导致导师从投快报被迫降格到 主刊,但Richard并没有再一次如同上次批评我,他说能发现错误总是好的,这比不负责 任地把文章发表出去要好。第二年,Richard没有申请到经费,我的工资被迫停了,他给 我写了推荐信,我凭借优秀的科研成绩拿到了国家奖学金,经济反而更加宽裕了,我给我 的女朋友买了钻戒,我们订婚了。
那一年,我开始发现生活也许并非如我当年生活的市井 小巷那样充满危险,这里的人不仅优秀,而且友善,我或许本不必自己隐藏起来换取一份 心理上的安全。
那一年,我开始试探性地进步,我隐约觉得,即使我失败了,有一些人也 不会离开,我设计了自己的项目,并且获得了两位导师的支持(另一位是Richard的好朋 友——国家天文台的邓李才老师),我们提出的预言在观测上获得了强有力的证实,这一 次,我挽回了上一次的失误,成功将我们的成果发表在了快报上。
随后,我被邀请担任了 一次该课题方向的审稿人,那一年的寒假,我在朗润园抚摸着讨食物的猫流泪,我逐渐走 出了那个只属于怯懦卑微的我的小巷子,开始成长为一名自信向上的北大人。
我的生活开始朝着向上的方向进步,我重新想起了当时中学时和好朋友约定的天文梦,想 起了在本科时因保研英语受挫时朋友们的帮助,我发现过去的生活并非如我想象的那般充 满敌意。向上的生活进一步让我决心向上,2013年,侯仁之先生去世,我和一位文学院偶 然结实的老北大人——侯晓晨师兄去大讲堂拜祭老先生,那天我说,我以后一定要成为大 师,师兄当即记下了这句话,他会等着我兑现那天。
那一年,我送走了两位我中学时代一 起来北京的好朋友,我陪他喝了很多酒,但我没醉,当时我还没到能放心醉倒那样安全; 那一年圣诞节,我与她在西门的蒸鱼店告别,我们各自许下来年的愿望,我说我希望能发 表一篇《自然》或者《科学》杂志——两年之后,我在微信上说:“我做到了”,那一刻 ,朋友们沸腾了,他们说我是他们的骄傲。
你的力量并不是源自减少或阻止悲伤的努力,而是源自选择承载悲伤的过程。以前,我不 懂这个道理,我拒绝悲伤,拒绝煽情,我拒绝送别,也从未认真对待过他人的悲伤。那一 年,我去了荷兰,接待我的师弟陪我喝得烂醉,他带着泪水说他的爷爷已去,家道中落— —我羡慕他,我刚认识他不到一个月,他却不害怕我,这么深刻的爱,他敢对我说。
那天 晚上,我吐在了房东地毯上,Richard为我陪了不少钱,但他没责怪我,他说我很诚实承 认是自己干的,这就够了。
师弟对我说,Richard以我为荣,他说我进步太快,现在他已 经没有什么能再教给我了,在飞机上,我反复思考师弟告诉我的话,我希望这句话是假的 ,因为那样我就可以再依赖导师两年,我又期盼着这一切赶快到来,因为我希望成为独立 的科学家——我太希望了。
在荷兰的宿醉让我落下了病根,2014年10月,我突然病倒,此 后三个月我饱受胃病折磨,师弟来到了北大,我却没有很多时间指导他,他的文章至今未 发表,我一直身怀愧疚。
我频繁请假,那一年光病假我就休了20多天,Richard和邓老师 给了我完全的特权,朋友们陪我看病带饭。在心理医生那里,我一直哭,我想起了一个人 在小巷子里发烧时无助的日子,我想妈妈,想家人照顾我。那一年,我和女友领了结婚证 书,岳父岳母把我接到了家里,照顾了我一个多礼拜,我逐渐痊愈,痊愈后妻子送我到了 回北京的高铁站,我转身就哭了。
Richard在蒙古组织了国际会议,作为他的学生,我面带微笑向台下的同行还有前辈做了 精彩的报告。我认识了从未见过的美国博士后Aaron博士,一位大胡子长头发的大高个, 我们之后又合作了好几个工作。德国的Hans教授是恒星形成领域的大师,他在会议总结上 说,我要恭喜程远,因为你作了让我印象深刻的报告,这让人赞叹,在后来寻找博士后的 经历里,Hans先生后还主动帮我写了许多封推荐信。
国家天文台的Rainer教授邀请我参与 到了他们与韩国Lee教授合作的研讨会中,我作为会议上仅有的两名观测者做了报告,作 为一个博士生,我还“任性”地携带了我的妻子一起去韩国,Lee教授非常慷慨地为我的 妻子写了邀请函,还安排了当地的住宿。
那时候,我开始蓄胡子了,因为我发现我的拔毛 症逐渐痊愈了(童年时我曾莫名其妙把自己的头发拔得光秃秃的,后来心理医生问我,当 我拔头发时,你的爸爸妈妈关系会缓和些吗?我便低头开始哭)。
那年夏天,天文系推荐了我参加云南的中国科协博士生年会,在那里,我见到了全国各领 域最优秀的博士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组的博士生、大亚湾中微子震荡实验的工作者 ……那些如雷贯耳的实验,就是那些和我一样年龄的博士生们参与完成的。
在云南,道格 罗斯.奥谢罗夫教授(1996年诺贝尔奖得主)告诉我,科学并非个人英雄主义,他需要一 代代默默无名科学家的共同努力;第二年,我在钟盛标颁奖仪式上,我把教授的这句话告 诉了我的同侪还有师弟师妹们,我说:今天如果我们不携起手来,我们的下一代科学家就 会嘲笑我们,说科学在我们手里没有得到发展,我们就没法让人们相信,未来会因为有我 们而变得更好……让我们站出来,把导师们的任务扛下去。
颁奖的钟先生夫人对我说,把 一等奖颁发给我,他们服气,她说你要努力把中国的科学传承下去——他们真的是爱中国 的。
今年六月,我来到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杨戟邀请我做了会议报告,我在报告中总结 了我的博士全部工作,报告末,我说,我们已经站在了新一代设备更新换代的节点上,未 来,会有更多的望远镜让全世界的天文学家使用,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有下一代的 望远镜,我们还要下一代天文学家,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在座的各位研究生和年轻的研 究员们。
杨台长说,他想要把紫金山天文台的恒星研究发展起来(也就是我研究的方向) ,而随着老院士的退休,现在台里几乎没有人在这一块工作了,如果我要出国深造,是否 愿意同时在台里任职,三五年也没关系,只要我愿意担负起建设团队的重任,他愿意为把 这个位置给我留下来。
Richard和邓老师说,他们会尽全力帮助我。
与心理医生分离的那个礼拜,我痛哭了整整一周,但我却不失落:我终于明白了“你的力 量并不是源自减少或阻止悲伤的努力,而是源自选择承载悲伤的过程”这句话的道理。那 天,与心理医生告别后,我的朋友陪在了我身边,看着我哭,她说她羡慕我,我虽在流泪 ,却能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她相信我一定会振作起来。
婚礼上,我对我的妻子说:过 去的我因与你不同的经历,我们走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只因你的理解,包容,我们才能 走到今天,感情才变得稳定。
小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最高的山是岳麓山,现在,我知道最 难翻越的是生活。但是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可以借彼此的感受去聆听这个世界,去感受这 份生活。心理医生对我说:未来的生活,还会有起起伏伏,重要的不是生活有多少起伏, 而是我依然爱自己,相信自己有面对生活的力量。
在北大,那些人那些事,陪我度过了那 起起伏伏的五年,最终他们帮我一起填满了那一份生活。在毕业聚餐上,我对刘老师说: 刘老师,程远过去五年,有什么做得不好的,请您谅解。刘老师说:你没有什么做得不好 的,从来没有过。
2015年,注定是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马上,它也会成为那一年:那一年,我和妻子 走入了婚礼的殿堂;那一年,我离开了导师,成为了一名独立的科学家;那一年,我和心 理医生分手告别,同作为博士研究生,我们互祝对方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一年,我的 父亲为童年为我带来的伤害道歉,我流着眼泪回复了爸爸的信息:我不怪你了;那一年, 站在毕业典礼上,《燕园情》响起,全场起立,我摘下了眼镜,因为我已泪流满面。
程远啊,我经常在未名湖畔问自己:你可曾见过生活为谁而改变?
北大啊,你可曾见过世界为谁而改变?
未名湖静静地荡漾着,她知道我会自己找到答案。
我生活了27年,我从未见到世界为谁而改变,但我见到太多人因生活而被迫改变自己,妥 协了梦想,输给了现实。我曾输过,哭过,但我选择了不妥协,北大收容了当年昂着头横 冲直撞,头破血流中依然找不到方向的我——那天,我终于低下头,院长微笑着为我把穗 拨到了左边,那一刻,我看见生活正在前方为我打开一条通向未来的路——未来,我愿意 作出任何进步,发生任何改变,我会尽我的全力改变生活和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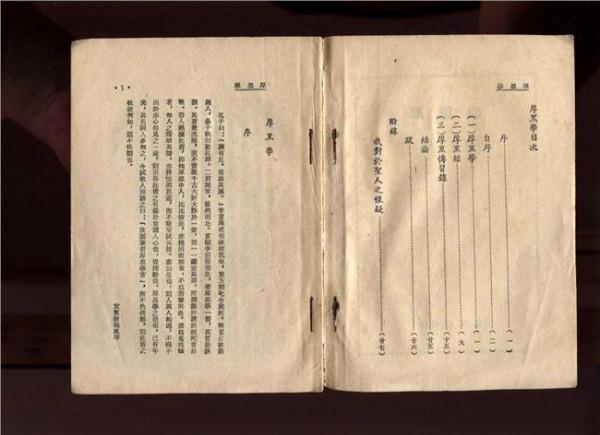

![>李庄现在可以说了 [转载]李庄:现在可以说了(之二上)](https://pic.bilezu.com/upload/7/10/710831bbf0ff70a519e7324c82183df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