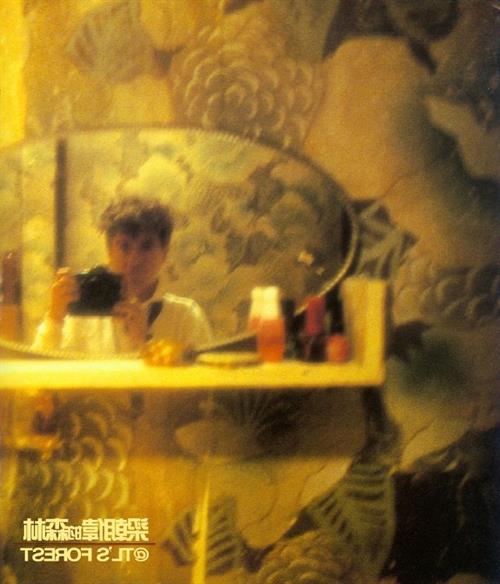《春光乍泄》摄影手记(杜可风)
摄影师杜可风,本名Christopher Doyle。作为香港导演王家卫的合作拍摄伙伴而为观众所熟知,自称为“得了皮肤病的中国人”。
主要摄影作品:暗恋桃花源、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春光乍泄、花样年华、英雄、绿茶、无间道
导演作品:三条人
杜可风善于使用肩扛拍摄,拍摄手法强调形式感,镜头跳跃摇摆,叙事残缺模糊,视觉效果强烈。例如《阿飞正传》里的升格拍摄,《重庆森林》里的大量的跟摇镜头,《堕落天使》整个片子几乎完全用短焦广角镜头拍成,近景扭曲失真,稍远的景象变得过份遥远。杜可风的摄影探索不惜走极端,镜头语言总是惊人地新颖。但如果简单认为杜可风的风格手法只是这种新潮、浮躁的形式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在接下来的《花样年华》、《英雄》中,他充分向观众展示了作为摄影大师应具有的素质。
在《花样年华》里,杜可风的镜头语言一改往日的变化多端,为了造成一种平稳的节奏,他使用了大量的几乎是唯一的一种镜头运动方式:平移,这与《末代皇帝》的镜头风格相似。但较之斯特拉罗,杜可风的手法要简单得多:起幅、落幅均匀,中间的移动十分平稳,让观众能看明白场景和时间上的变化。
《英雄》是杜可风首次和中国大师级导演合作,影片延续了张艺谋以往作品中大全景,大色块搭配运用的视觉造型风格,然而在杜可风摄影风格的影响下,更加注重色彩的搭配,影片淡化了张艺谋的那种粗犷、质朴的色彩风格,多了几分鲜艳、瑰丽。在镜头语言运用上,放弃了张艺谋一贯的压抑、平缓,变得凌厉且十分灵活,可以说《英雄》是两位大师相互影响下的产物。
对于光影的把握,一向是杜可风的拿手好戏。早在《东邪西毒》里,他就运用了动态投影在自然光下产生通常灯光才能有的效果(鸟笼旋转的画面和湖水的波光流影)。而在《花样年华》里,他对于光影的把握更成熟了,在影片的许多镜头里,画面大部分处在黑暗中,演员在光源照亮了的一小块地方进出。这种利用黑暗造成强烈明暗对比的手法,使得画面显现出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像是在暗喻片中主角苏丽珍那进退两难的处境。
《春光乍泄》摄影手记(杜可风) Don’t try for me Argentina部分翻译: 《春光乍泄》摄影手记(杜可风) August 14-15
另外三十六小时的飞行再飞回去我大半生想飞离的…平庸而非自我,借用人家价值而非自己想法…每飞越一个时区,很久以前那所有痛恨而离开澳洲的理由逐渐迫近,在免税店的玻璃杯底中恣情放大…别猜我,Argentina,我也不知道怎样去猜你!
飞到那儿我们赚了一天,离开那儿我们失魂落魄。摄影手记
第一日开镜并非真正开拍——只是确认一下我们来到这儿。但愿我记得谁先说出大家对这部片的感觉。“好导演不会拍出差的作品…他只是下错决定。” 我们在油淋淋的小港La Boca和Hotel Rivera(法国的Riviera)门口及屋顶“执”了些“空镜”。伟仔同哥哥(张国荣)就在酒店这儿开始相爱。
我不大清楚我在干啥——只是到处听听,试试滤镜胶片速度…不找灵感,只是意念…然后侥幸的巴士绕道穿过废桥见到灯明火亮景象。一片孤寂、远离、形神尽失…我终于找到影片的视觉主题,去揣摩这片空间“性格”的方向。 说过走完一条街都想不出五个新映象或意念,你便不算是艺术家。Streichen 说你可以在房间内拍到一个世界…而后Robert Frank 和Keichi Tahara告诉我们怎样做。
我开始奇怪我是否失去我的心我的眼…自从来到这儿,我未拍过任何“个人”的照片…而且“看不见” 这地方…它不跟我“说话”。屎! 给自己制造的难题六个星期后。还有卅日才夏至,离南方又远达千多公里,下午五时,太阳快要落山,而现在要解决这个难题。
“怎样给南回归线打灯?”就象问怎样“放映黑暗?失落的颜色是什么?”…“怎去为记忆构图?”…这类无法回答的问题是每个摄影师每日都会自问自答。
我们想找一行亮光移过南回归线那想象中的线。但在这渐暗的日光下做这个效果要好几里长的灯闸,而我们手上只有两只一千火的灯枪及手掌般大的化装镜。
我们不想要电脑绘图。我们要点比候麦的《绿光》更明显的东西。
但阳光没有“天然”动机做一行阴影或线…周围也没有标志日晷…我们只有极目平野,日落在草丛和两株树后。
“让镜头食正光吧!”家卫自顾自说…“无得拣。”
于是有树又有反光!在广阔路上,日光自树间透出来,正对镜头现出花班一行光,我借助化装镜,转片速和光圈,伟仔和哥哥在日光中如魅魉,画面花白了两秒,然后转暗,他们两眼凝望,在“浪漫”的慢动作中…一切都很“正”在荧幕中…家卫笑着说:“O.K.!” 我们的内景故意“没有时间”,灯光不依“逻辑”照明。日或夜都不重要。伟仔与哥哥的世界时空不明。 我们放“空镜”的毛片来看。家卫很兴奋:“光用它就够做这城的Milonga(拉丁舞)了。”管他什么意思。我只看到空的桥、空的船、空的天、空的一切。明信片式的乏味港城!我还是不会跳探戈…只希望能够有点Gordon Willis 的诗意,找到这地方真正的“音乐”。 看毛片看到灯光颜色稍为有错令我不快…我为什么要“写实”而不“诗化”?总是小错误造成大伤害。虽然无人这样看这些画面…但我会。劝自己“由错误中学习”并不等于去改戏或灯光。 我们这部片有很多桥,多到一百份日历都用不完。
我们那两个情人争吵,日出之时各行各路。桥不止是意象,还是生活的阴影。
晨早桥上交通繁忙,我根本听不到导演演员的话,只有靠估,几时几刻情绪爆发我就要审慎地把镜头摇走…但应该是流畅的过场变成急摇…不是风格如此,只是我脚下的“苹果箱”左摇右摆令我难以平衡。 我们最初颇犹疑要否重复我们的“绝招”…不用也实在气馁。
愈拍下去愈多镜头要变速…由“正常”转到一秒8格或12格…或者反过来做。最初视为“禁忌”的广角镜,愈用愈多好使“平板”的画面“变得有趣”。
我时常把我们那种“Blurred action”视为受惊时肾上腺素或者兴奋时的大动作。今次的更像“啪丸”。我们在“决断”、“顿悟”、“启示”之时变速。演员走动得特别慢而周围一切就正常。目的为吊住时间,拖长事件,放大证据…有点像打了海洛英(听说如此)。
理论如此,在那时仍是理论。我们没钱试毛片或光片来看效果。我们“用双耳来玩”直至回港。 家卫说只有剪片时才知道拍过的片段意义何在。当时并不肯定清楚某些细节颜色动作意味什么。它们预知影片去向而部片会带着我们走。它们是来自未来的映像而当时我们才刚刚抵达。
哥哥和伟仔
打算去蒲酒吧喝个烂醉——好让伟仔(梁朝伟)入戏而我们对这地方多点感觉。星期二市中心冷过主教卵蛋,开门的只有灯火通明的咖啡室…每一两条街就有一家红帐遮门的“真人表演”吧。我们选了家门口无人拉客的,却失足堕下地狱。我放下五十元付两个人八元的入场费。
“这儿没钱找,进去给你。”
肥婆安妮来落单——又要钱…一屁股连人带啤酒坐在我腿胯。角落里有个女人舔着唇像“中间折页女郎”把底裤拉到肚皮上。
“黑婆玛莉”真的在喂奶…两寸大的乳头差不多塞盲我双眼…“你吮我的奶,我吮你的。”伟仔给人不停地问有多大条而数不清是谁又有几多只手…“Change”他咕哝的说,听不清是找(钱)还是走(人)。我们试着辨。
经理拦住。“给小姐钱。”
“我们没有摸过她们。”
“她们喝了五十元。”三个打手从暗角走出来摆明车马。
忘了“找钱”吧:不给钱就开打…我只想大笑一场或者放一个屁。
伟仔好似Tarantino的角色,一边丢下五十大元一边说:“****, ****, ****…”
我忍不住笑我们“青头仔”受骗…而我一笑就放屁。 September
哥哥和伟仔在I LOVE PINK酒店狂欢,在浴室拍宝丽莱,互掷生日蛋糕、啤酒、可乐。结果搞到摄影机和我浑身都是。
我玩的不亦乐乎,把摄影机时开时关——追求率性随意的效果,像宝丽莱生活照,时空乱跳,犹如记忆…
我们由第一场造爱戏开始——预计沿途遍历阿根廷以北——在北回归线附近一个小城一家偷情酒店内。哥哥叫宝荣(是我对焦助手名字),伟仔叫阿明(是我推轨助手名字)。他们把名字刻成心形在墙上一块木板上。
伟仔和哥哥试着如何抚摸感觉。我茫无头绪到处乱看。家卫抱怨说:“我们跳的是Milonga,不是Rock ‘n Roll。”
清了场。只有家卫、我和“男孩们”。不知道怎样又为何,伟仔在“上面”。
也不知道为何又怎样,我们尽力做到既挑逗又审慎。
这场戏美丽又性感。伟仔和哥哥在床上表现出色。但拍完后伟仔垮了。
“家卫说只要接吻,可现在过了份。”
哥哥恨恨的说:“你知道我这几年多惨,假装要把我条嘢放入女人都有的另一个洞。” October 22我们今日又要再去屠房…有一半人不想去,伟仔更抱怨上次搬冻肉弄伤肋骨。
“都是你错!”家卫说:“上次你动作不够清楚。”
我所知一切导演的通性都是虐待狂…王家卫,今晚也不例外。
昨夜通告取消。大家都愕然。
“伟仔到处揾食的场面已经不缺。”家卫沮丧…“Hotel Rivera 是他和部片的中心但现在又变得太幽闭叫人发狂…一定要扩大空间,让部片及观众抖抖气!”
阿根廷的圣诞节快到…很明显他又想来个大改动。 家卫
家卫对留在香港而不去荷里活或其他地方拍片的妙论是:“我情愿同一流的黑社会打工也不同九流的会计师工作…黑社会多点自尊,讲道义,整你之前也先亲你。” 家卫时常说:“别改动任何东西。”又或者“这个角度不够有趣。”今天他最喜欢的还是我去小便时助手把摄影机放在伟仔床上时。我们把床弄乱一点,用脏衬衫或底裤半遮着镜头,新的风格於焉诞生!我遂把摄影机放在茶柜、沙发、床底、窗台,任何随意未想过的地方。
真的,这种“风格”反映出伟仔与哥哥多次分手时“给遗弃”的心情。却又非来自“学问”,也非计划得来。视觉上有趣又特别,解决了如何拍摄这个三十多天来我们出出入入无数次的细小空间的问题。
“风格”应该是“选择”问题而非“观念”…应该“自然生成”而非“生安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