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梅演员 慈母——电影演员王玉梅自述
我是山东济南人,解放以后我上了一年学,这一年是我生活中的转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记得我上最后一年学的时候,我们加了一门儿课叫政治。一个政治老师给我们讲解放军是干什麽的,他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要让天下的人不分贫富,都能平等,都能生活的好。我当时听了这个话特别惊喜,我觉得要是大家都生活的那麽好,那该有多好啊!那个时候我一下子产生了一种萌动:我不上学了,我想去闯世界。
我的家庭是个比较封闭的家庭,对我管束的很严,所以我属于那种比较特别的女性,不是那种女强人式的,而是比较温柔的那种。我当时要出去闯闯的想法被几个女同学知道了,她们也要和我一起去,于是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政治老师。我们问他:“有没有女八路军呢?”他说:“有啊!”“我们怎样才能参加革命工作呢?”“你们去报名啊。”“怎样报名呢?”“你们可以到社会上去闯一闯。”
就这样,我走进了社会,上了职工学校。在学校里,我把没有文化的老工人组织起来,分了几个队,我在二队做文化干事。那一年我才十六岁。想一想,我能教人家什麽呢?就教文化课、教唱歌、教扭秧歌吧!大伙都叫我小王老师,每当这时候我就特别高兴。
到了年底,济南警备区政治部文工团把我招了去,说是搞文艺。当时什麽也没想,搞文艺就搞文艺吧,只要让我出来工作就行。来到文工团一看,大家都穿着军装,别提有多威风了!发给我的军装穿起来特别肥大,上衣棉袄都到了膝盖,再打上裹腿就看不见腿了。
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帮着老同志裹裹腿,看谁裹得快,当时就觉得生活特别有意思。在文工团的日 子,我们又扭秧歌又跳舞,还演歌剧,什麽角色都演。记得在一部戏里领导让我演一个老大娘,我犯了愁,老大娘该怎麽演呢?老大娘该都是小脚吧?于是,我在演戏的时候就把脚翘起来,用脚后跟走路。
后来有人就把我们演的戏拍下来了,导演看了就说:你不能这样翘着脚走路,大家听了都笑我。
在部队,我经历了第一次行军,那时,我们所在的警备区政治部改成了七师政治部。这次行军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而且还特别好奇,就像飞出鸟笼子的小鸟。记得行军那晚下着大雪,老同志教我打背包。这一路上虽然不很远,但是我却感到了艰难。
开始走的时候,没觉得什麽,走着走着就没劲儿了,背上的背包觉得特别沉,穿的棉裤又觉得特别笨。还不时地滑倒,没办法老同志就用麦桔杆拉着我们走。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拉下很多,几个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就叫嚷:什么时候到啊?我们的政治指导员就说,快到 了,快到了。
这三十多里路,我们一直走到天蒙蒙亮,终于看见了村庄,大家高兴地叫起来。到了目的地以后,我们才发现穿的棉袄都已经湿透了。老同志都忙着去抱柴火,在房间里把火升起来,顿时我们感到了温暖。
现在想起来,我自己觉得很幼稚,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阶级友爱,可以说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慢慢地懂得了许多道理。在这个大家庭里,别人关心我,我也去关心别人。
在文工团里,我什么都干:编舞、说快板,即使再冷的天,我们也要坚持为战士们演出,演出中,我抢着做一些份外的事。说来也奇怪,那个时候我们吃的都是高梁米,但是,我们的热情却很高,我体会到,人的精神要是好了,什么困难都会忘记。
大约一年以后,我上调到山东军区,然后又马上下到基层去锻炼,同时还兼任人民武装部干事,那一年我十八岁。人民武装部管民兵,除了教他们演戏,还要在劳动之余教他们唱歌。有一次,领导让我到一个村里排戏,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村名叫“瓢”,大家想想,瓢能有多大?这是在山坳里的一个小村庄。
我不认得路,只能是按照领导告诉的大概方向向前走。早晨起来我也没吃饭,拿了两个苹果,一个干的凉红薯就走 了。路上遇到一个老大爷,我问他:大爷,瓢在哪儿啊?他说:翻过山就到了。
我这一路也不知问过多少遍,一直走到天快黑才到。村里的人特欢迎我,觉得我是个文艺工作者。其实我自己最了解自己,什麽本事也没有。吃完晚饭我就抓紧时间看剧本,那个时候的工作积极性可高呢!
在那段时间里,我演过歌剧,扮演的大都是朝鲜的阿妈妮什麽的。因为我小时候唱过评剧,就常常利用空闲时间教别人唱评剧。庄稼人没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跟我学唱评剧,学会了就到集上去演,特别受农民朋友的欢迎。别人就说:小王,你真行。
受到别人的表扬,我也很自豪,觉得自己真实长进不少。记得有一次领导说:最近咱部队要招新兵,你给编个节目吧。于是,我一夜没睡觉,赶编了一部小歌剧《送子参军》,领导表扬我说:今后你可以搞创作了。
后来我还和另外一个女同志合作跳朝鲜舞,我去过朝鲜,对朝鲜舞也不陌生,可是当时却找不到朝鲜衣服。最后没办法,我们就穿农村新媳妇穿的花棉袄,再系上大红绸子,跳 着也很好看,老乡们看了也觉得新鲜,特高兴。
劳动之余,我们也教老乡学五线谱,有时候还要到公社去教,每当去公社的时候,村里就派一个民兵保护我。我就想:我都是干事了,怎麽还能叫民兵保护我呢?于是,我坚决要一个人去,有时候是晚上,领导还是不放心,就给我配了一支小驳壳枪。
我第一次晚上走高粱地,还是紧张,老觉得背后有人跟着我,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手抠着扳机不敢松。终于到了目的地,可松了一口气,心里也特别高兴,好象自己做成了一件特别大的事,也觉得自己确实长大了。从这儿以后,我经常一个人跑这儿跑那儿,慢慢地,从一个内向的女孩变成了活泼开朗的文艺工作者。
抗美援朝时期,我们代表华东部队到朝鲜前线去慰问演出。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把北朝鲜走了个遍。去之前,领导对我们说:你们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大家都纷纷表决心。我虽然出身不好,但是表现却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领导也批准让我去。
来到朝鲜以后,确实感到了艰苦,气温经常是零下四十多度,早上起来把杯子放到院子里,再回去拿牙刷,回来的时候杯子已经冻上了。我们演出的地方经常是透风的,门也关不上,窗户也没玻璃,战士坐在那儿不动,那冷劲儿就别提了。我们演出的到没觉得什么冷,这也许是我们的心都是热的缘故吧,我们年轻人对于吃苦已经习惯了。在朝鲜,我们呆了半年,这半年对我来讲锻炼特别大,那时我才刚二十出头。
回国以后,文工团减员,我就到了山东省话剧团,一直到现在。其实我的本行就是演话剧,排电影只是第二职业。在话剧舞台上,我演了很多话剧,扮演了许多角色。我记得我演的第一部话剧叫《破旧的别墅》,在里边我演一个特务,我爱人演地下工作者。
因为第一次到专业剧团演戏,特别紧张,老怕演不好,所以心里七上八下的。没想到演完后反响特别好,从那以后,我也接连接了几部大戏,从《兵临城下》的女间谍,到《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银环、《秋海棠》的罗香怡,同时我还演过刘胡兰等一些正派角色。
我的第一部影视作品是《丰收之后》,这部戏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在戏中我演了一个支部书记。这一年我二十八岁。当时我特别害怕,我怕丢人,但也只能服从组织上的分配。压力虽然大,但领导也给了我很好的条件,让我到角色原型的地方去体验生活。
我与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同吃同住,以前在部队的时候也和老乡一起住过,但像现在这样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还是第一次。这部戏最终获得了成功,我觉得应该归功于我的这段生活。
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那位支部书记的原型。这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小脚老太太,一米五几的个子,这怎么能是支部书记呢?其实,她的经历简直能写一部小说,她丈夫是个赌徒、酒鬼,在家里,她是个受尽压迫的妇女。也许正是她的受压迫,才使她更加地自立。每次上山,她都走在我前面,什么活她都能做。在家里她也是一把好手,做饭、绣花儿什么都行。
记得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在与老乡们打场的时候,发现丢了一个麻袋,里面装着刚打下的粮食。干完活以后我们的支部书记就说:大伙等一等,我说两句,咱们也是先进村了,我也不多说别的了,是谁拿的我不指名,要是有自觉性呢,今天晚上就隔着院墙扔到我院子里去;如果不这样,就别怪我让你难看。别说,这两句话还真管用,第二天早上院子里就有一麻袋粮食。
说起支部书记的老伴儿,还是个大队长。过去在旧社会他是打过她,可现在她成了支部书记领导她的丈夫。大队长开始不服气,总觉得一个男人被妇女领导不好看。一些时候。他总是找茬儿,甚至还动过手打人,她也不服气,就上县里去告他。
在解放前,她还经常做地下工作,她是那一片第一批地下工作者。那个时候都不识字,开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互相摸几下耳朵就说明应该到哪个山头开会,搓搓膝盖就知道应该到哪儿去碰头。
这一个半月,我在这儿生活的非常快乐,村里的老乡们对我特别好,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我后来演这个戏非常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戏之所以受大家喜爱,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出场就赢得了掌声,我的出场和那种样板戏式的英雄人物不同,完全是一个朴实的农民的形象。观众对这样的形象很容易接受,也感到亲切。戏里的一些台词也是经过反复推敲的,甚至还要征求农民的意见,专门有人来回传递消息,这句台词怎么说,那个情节怎么改。
那个时候我的脑子跟录音机似的,一天变几变。到了会演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场戏没有排,当时大家伙都紧张的不得了。
好在我们的演出获得了成功,连我们自己都没想到效果会那样好,一下子有那么多人来向我们祝贺,这里面有其他剧团的同行,有老同志,也有新同志。他们说: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戏了,特别生活化,特别感人。会演结束以后,我们的戏被选送到中央去汇 报演出。
在北京,周总理看了我们的演出,演完之后他上台接见我们,他拉着我的手问我多大了?我说:27岁。周总理就说:你还是个小赵五婶啊!在演出期间,我们还召开了文艺晚会,周总理把陈老总也请来了。我记得那一天是在北京饭店,我们早早来到现场,坐在角落里。
大厅的灯一亮,周总理就问:那个小赵五婶来了吗?我们团长听见了,赶紧把我拉到前面。总理走过来和我们说话,许多人都围过来,总理对陈老总说: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戏。陈老总就说:我没有时间呀。总理说:我给你安排时间,明天晚上就可以嘛,你明天晚上看。
舞会开始了,总理过来请我跳舞,边跳还边和我聊我演的戏。指出我们的不足,我觉得他真像一个慈父,在他面前我一点都不紧张。
这个戏后来拍成了电影,一些三十多岁的人见到我就会问: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看过您演的电影,里边的女主角叫什么“婶”。当时我还记得总理夸我们这个戏编得好是因为处理好了三个关系,这就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人物也有个性,还有矛盾冲突,写得生动真实,很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拍成电影以后,我陆续接到几千封信,大人小孩都有。
这部戏成功以后,我就开始以演老大娘为主。在十年动乱期间我有七年没演戏。恢复演戏后比较成功的一部戏是《喜盈门》。这部戏也引起了轰动,许多观众以为我那时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其实,我那时年龄也不时很大。我演《丰收之后》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化妆只是在脸上涂三层胶水,然后自己用手捏皱纹,当时也没觉得受不了。
但是,感觉上却很真实,真像个老太太,所以,好多人见到我就会问:你怎么还是演《丰收之后》时那个样儿,一点变化也没有?我就说:我那是先老下了,现在就不显得老了。
在这期间我还演了《内当家》、《山菊花》、《高山下的花环》、《帅孟奇》,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演了慈禧太后。《高山下的花环》是先演的电视剧,分别获得了飞天奖和金鹰奖;后来谢晋导演找到我让我再拍成电影,同时在另一部戏里演慈禧太后。其实,作为演员是很不容易的,机遇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对慈禧这个人物特别有 创作冲动,我不想只是演老太太,总要再闯闯路子。
由于是同时拍两部戏,我要从广西前线赶到长春,从零上四十度到零下四十度,一到长春我就发烧,我是躺在病床上打着吊针看得剧本。其实关于慈禧的一些书籍我过去也看嗰,对这个历史人物我也有一定的了解,这对我演好这个角色很有帮助。
在拍戏期间,我们还请到了博物馆的人员给我们讲课,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历史学家,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受益菲浅。
第二年,这两部戏同时获奖了。《高山下的花环》获电影百花奖,我在另外一部片子里演的慈禧太后获得了金鸡奖。这以后,我先后在六部影视片子里扮演慈禧,时间一长,也就没有什么新意了。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更喜欢梁大娘这个角色,她的戏虽然很少,但是留给观众的印象却很深,她是中华民族妇女的优秀代表;梁大娘身上最突出的一点是:她虽然一贫如洗,却有一身傲骨。
梁大娘苦,儿子死了却不愿留下欠账单,她省吃俭用卖了猪,用白开水泡煎饼吃,为的就是替儿子还账。
而慈禧这个人物就不同了,我是从演一个“人”的角度出发的,首先是一个活人,一个有感情的人,而不是她的阴险毒辣,不是从概念出发来演这个人物。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扮演的这两个角色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当我接过奖杯的一刹那,我感到心里沉甸甸的,我应该用最好的角色去报答观众的厚爱。
这儿以后,我无论 走到哪儿,大家都叫我梁大娘,到部队去,战士门就叫我妈妈。在老山前线,那些感人的事迹经常让我哭肿了眼睛,说实在话,我对子弟兵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我从小是在部队长大的,又演了许多子弟兵的母亲,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我自己的孩子。
我的另一部引起反响的戏是《儿女情长》。刚开始的时候我没答应接,因为我在拍着别的戏,另外我也觉得戏中的这个母亲也不适合我。导演坚持用我,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跑到我拍戏的小山沟里来找我,这里不通汽车,没有电,而且他们请不动我就不回去了。我理解他们的诚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有一个条件是允许我自己改剧本。他们很尊重我的意见,答应了我的要求。
这部戏里的母亲,地域文化色彩太重,带有上海殖民地文化的痕迹,比如:这个妈妈有时说这个孩子不好,大哥回来就说老二不好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我不赞成的。当然我不怀疑社会上有这样的人,但毕竟是少数。我们塑造艺术形象应该把人物升华,不能照生活的原样不变,像上海人的一些小事就不要过多地表现了,比如:计较小事,哪个孩子给的钱多,哪个孩子给的钱少等。
后来导演接受了我的建议,剧本里好多东西都是我自己加进去的,比如:大儿子回来看我那段戏。
实践证明,上海人看了以后特别欢迎,说我演的很像上海的妈妈,我觉得能得到她们的认可是最值得庆幸的。实际上,她们也不愿把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暴露给全国的观众,看到屏幕上的妈妈的所作所为,生活中的妈妈们也在对照自己的行为。在我看来,不管是南方的母亲还是北方的妈妈,我希望全国的妈妈们都是善良的。
作为一个女性,能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女性美德,包括现代女性的美德都能表现出来,是我心里的愿望。但我觉得这麽走过来也确实不容易,这完全靠生活的积累。我不是一个聪明的演员,我主要靠笨鸟先飞,用的功夫比别人多而已。有人经常对我说:王老师,像您这样的,轻车熟路,不用演就行。我说:可不能这麽说,任何角色我都得从零开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拍戏中,我还有一个习惯,接到剧本后我就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也不看书,全身心投入到剧本中去,看资料。同时我也不像其他人那样背台词,而是先理解人物,在自己心里产生这个人物的形象,把她看成我自己,这样心里就塌实了。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生活给我的启迪很多,大自然给我的启迪更多。比如:我到森林里,看到许多树木,有乔木、有灌木,你有时会发现乔木和灌木长得一样高,这时你就会想,它们为什麽会长得一样,实际上是它们在争夺阳光的过程中不断长大的。从这些树木身上我体会到:人也像植物生长一样需要阳光,要给自己施压,除了不同的角色的压力之外,自我施压是很重要的。我如果放松了这一点,就生活得不塌实。













![王玉梅演员 王玉梅[川剧演员]](https://pic.bilezu.com/upload/d/2a/d2a58c115b74c637d2ef56159e79ae48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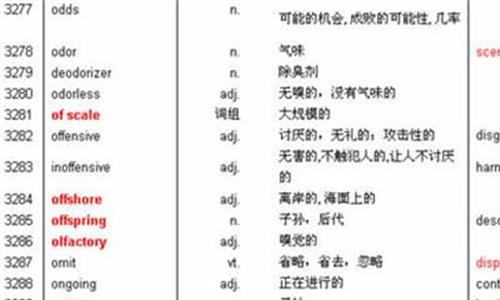
![>演员王玉梅现状 王玉梅[河北省政协副主席]](https://pic.bilezu.com/upload/c/fd/cfdc1e179c534ce632677fbf3b10e369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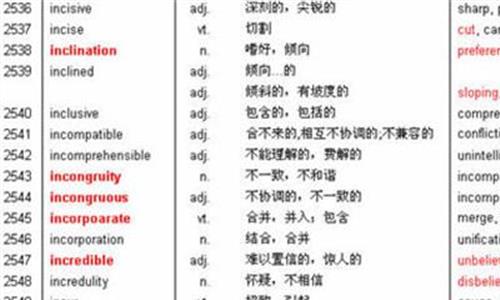



![>演员王玉梅 王玉梅[川剧演员] 简历](https://pic.bilezu.com/upload/1/d5/1d547b2b768b0a7f6e16cff132a5e424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