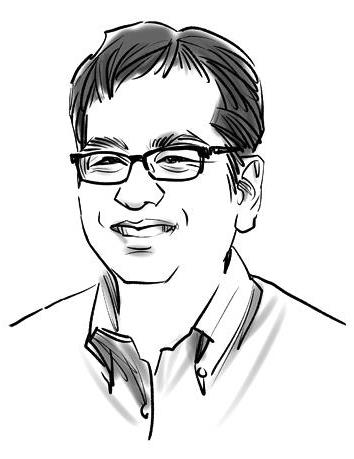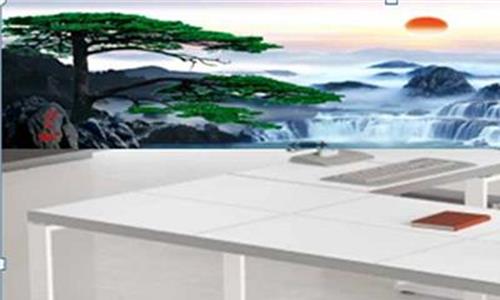林来梵事件 林来梵:法律实证主义方法的故事——以拉班德的国法学为焦点
如果要透过历史的框架窥视法律实证主义方法的具体面貌,有一段历史就不得不读,那就是19世纪在德国斑斓成熟的“国法学”的学说史。越过遥相隔绝的国界,穿过云谲波诡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在那里读到法律实证主义的谋略和命运,而且还可以读到今日中国法治问题的部分叠影。
后者的这种意外的可能性,主要缘起于如下事实:现代中国有关法的、尤其是宪法的许多观念和制度,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源流追溯到那段历史的源头上去,其中一个是前苏联国家法的源流,另一个则是日本公法的源流。但如果进一步追溯下去,则会发现在很大意义上这二者均发源于德国近代的国法学。[1] 既然如此,思考或解决现代我国宪法中的一些观念问题,其实可以通过解读这段历史而追寻得一些机要。
当然,由于研究的极度匮乏,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梳理这段陌生的历史相当困难,何况在有限的篇幅之中。有鉴于此,本文将自觉地把探究的对象限定于特定的维度之内。具体地说就是:第一,所要把握的固然是一种学说史,但不刻意深究其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而着重关心它具有规范形成意味的那种自我展开的脉络,笔者把这种“谱系论”意义上的脉络,喻称为一种“故事”;第二,由于这段历史中的学说与确立各种学说的思考方法具有相互形成的关系,我们便以方法的演变作为考察的主线,而通过这样的考察也会发现,法律实证主义方法在德国公法学领域中的确立、演变以及其在学说史上的功能和意义;第三,基于拉班德(Paul Laband, 1838-1918)[2] 在这段历史中的象征性地位,进一步将其人其说作为考察的焦点。
二、历史铺垫:拉班德国法学的条件
在近代德国的法学史上,所谓“国法学”(Staatsrechtslehre),相当于公法学,或今日的宪法学。拉班德生前就被誉为“当时最大的国法学家”,[3] 其代表性著作就名曰《德意志帝国国法》。[4] 但这种国法学又被置于所谓“一般国家学”的体系中,继拉班德之后德国近代国法学大师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1851-1911)在其巨著《一般国家学》,[5] 就采用了这样的学说体例。
作为国法学家,拉班德所生活的时代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所周知,在德国,近代意义的宪法典是在19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但那些都是各邦的宪法,作为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宪法是在1871年才得以诞生的《德意志帝国宪法》(Die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s),即俗称的《俾斯麦宪法》。拉班德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生涯,恰好展开在这样一个前人的宪法思想火化迸溅已久,接着,宏大的体系正处于喷薄欲出的时期。
在思想史上,这至少可追溯到18世纪末。自此以降,德意志法学开始进入了流脉颇为错综复杂的时代。由于普鲁士启蒙绝对 君权主义的发展,16世纪以来的德意志自然法学与西欧其他国家的自然法学为民主政治做出贡献的进路不同,曾一度积极介入立法活动的实践,并居然成为 君主制的拥护者。
与此不同,由于洛克、孟德斯鸠,特别是卢梭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当时也存在反对专制主义的立宪主义思想。有趣的是,一批公法学家则从这种立宪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实的宪法结构进行实证的分析。
曾被誉为“德意志公法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始祖”或“德意志国法之父”的莫泽尔(Johann Jakob Moser,1701-1784)以及与之齐名的普特尔(Johann Stephan Pütter,1725-1807)等人,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他们学说中所体现的那种由自然法学那里提供的立宪主义立场与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的奇妙结合,后来就成为贯穿于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宪法学的源流。[6] 而拉班德正是这个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宪法学的一位大师级人物。
但在19世纪前期,施塔尔(Friedrich Jurius Stahl,1802-1861)和布隆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1808-1881)等人进一步为后来的拉班德他们,预先夯实了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基础。
施塔尔是研究法哲学起家的,在法哲学的代表著中论述了他的国家理论 和 君主理论。[7] 他严格区分了国家的目的(内容)和国家的方法(形式),为此认为国家也可分为道德国家(Sittliches Reich)和法治国家(Rechtsstaat),其中,道德国家是“神性人格化”的国家,人类的共同体必须是道德国家,为此而设立法治国家,质言之,法治国家无非是实现道德国家的一种方法意义上的设备。而近代国家必须是这种法治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就国家行为的发动、国民的权利行使进行严格的规定,方能实现作为国家目的的道德理念。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 博士曾指出,施塔尔对法治国家“采行形式意义的认定,且必须透过实证法律来界定国家权力运作之轨迹和范围”,[8] 这是很准确的评判,日本学者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认为其学说“形成了近代德意志的实证主义宪法理论的基础”。[9]
布隆奇利是一位 “在德意志宪法学史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的学者。[10] 他的思想诞生在一个市民经济逐步发展,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取得重大成果的时代。在这种气运下,自然法学的社会认识就顺理成章地被看作是主观的、观念的假想,为此,抛开自然法思想的立场来建构国家理论,并在这种理论的框架中考虑市民的自由,就被提到当时的宪法学的面前。
布隆奇利回应了这个时代的课题,并巧妙地借用了科学,或确切地说是生物学的思考方法,提出了所谓的“国家有机体理论”。
在他看来,国家的出现是独立于人的意志和创意的自然过程,其自身拥有生命、运动和成长的机理,遵循进化的规律生成、发展和消亡。这种学说显然典型地体现了当时西欧社会学科理论开始服膺科学主义,并借助经验科学的方法来思考社会现象的潮流,反映了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合谋动机。
在笔者看来,这简直是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认识这一点,自然对理解19世纪的德国实证主义宪法学的精神也殊为重要。
但布隆奇利的学说并非那么单纯。就国家理论而言,他自己也意识到不能仅仅仿效自然科学的认识。在他看来,国家具有以下七个特性:[11]
(1) 被统一的多数人;
(2) 领土、国民与大地的永久性关系;
(3) 全体的单一性;
(4) 统治与被统治具有区别;
(5) 具有有机的性质;
(6) 具有人格特征,即是一种道德的、精神的高级有机体;
(7) 拥有男人的特性。
布隆奇利认为,宪法正是这种“国家的肉体”,因为它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制度,在它的形式中人民的生活才能实现;国家是被秩序化的“部分”的整体,这个部分包括个人、官吏 和 君主,为此,为了实现整体的目的,君主不能肆意妄为,官吏也必须服务于整体,像法官那样具有无党派性。显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布隆奇利理论中的法治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正像后世的耶利内克所言:如果说莫尔是自由主义国家思想的先导者,那么布隆奇利就是这种思想的普及者。[12]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德国也可以说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形成的。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普鲁士国王,以德国皇帝的名义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即位,象征着自解放战争以来德意志人民长年的国家统一这一悲情性愿望的最终实现。1871年,作为帝国的组织规范,《德意志帝国宪法》宣告成立。无须多言,这个宪法体制采用的是传统的君权主义与以产业资本家为中心的市民自由主义之间的妥协形态。然而,也正是基于这种妥协,过去数百年的政治动荡得以趋于相对的稳定,德国的产业革命急剧发展。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便产生了立宪主义的主题变奏曲:与其彻底实现实质的自由与正义,更重要的倒不如是维护形式意义上宪法秩序的安定性。
思想和现实的长久铺垫已经完成,拉班德时代的宪法学终于应运而生。
三、拉班德的国法学
在上述的那个所谓“立宪主义的主题变奏曲”中,拉班德时代的宪法学自然也相应面临两个相互矛盾的课题:一方面是不得不温和地接受传统的、前近代的君主主义体制;另一方面则是对已经形成的近代法治主义、形式合理主义的法理念也有所承担。在这种宪法体制下产生、并在理论上能够将上述那个矛盾的课题加以整合的,就是拉班德时代的宪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宪法学。
此处之所以说是“拉班德时代的宪法学”,而不说“拉班德的宪法学”,是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这个宪法学不独为拉班德一人所能代表。在学说史上,人们往往将之称之为“格贝尔—拉班德的法律实证主义宪法学”。
格贝尔(Carl Friedrich Wilhelm von Gerber,1823-1891)的研究领域涉及私法学、公法学和法史学,在学术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并曾担任过大学校长、国会议员、教育部长以及北方德意志同盟的制宪议会议员等职。他也是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倡导者,[13] 但与布隆奇利不同,认为国家要成为意志力的主体,必须拥有法律人格。本来,国家的法律人格是属于国家机械体学说的主张,与国家有机体学说格格不入,但在格贝尔那里,二者则被溶于一炉,这种具有二元性质的国家理论,乃引出了国家法人说的端绪,并成为此后耶利内克有关社会意义上的国家与法律意义上的国家那种所谓的“方法二元论”的源头。更重要的是,他将当时私法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引入国法学,[14] 以说明国家意志的发动形式,这为拉班德的宪法学直接预备了方法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