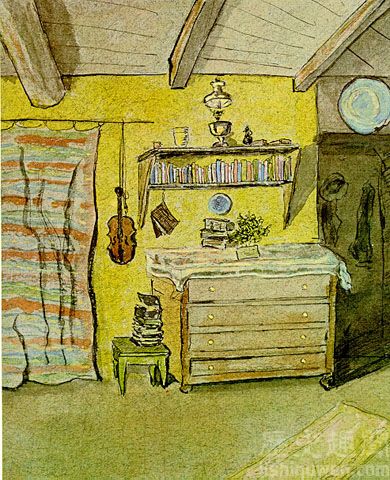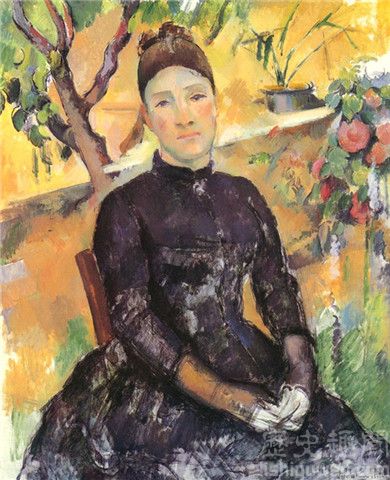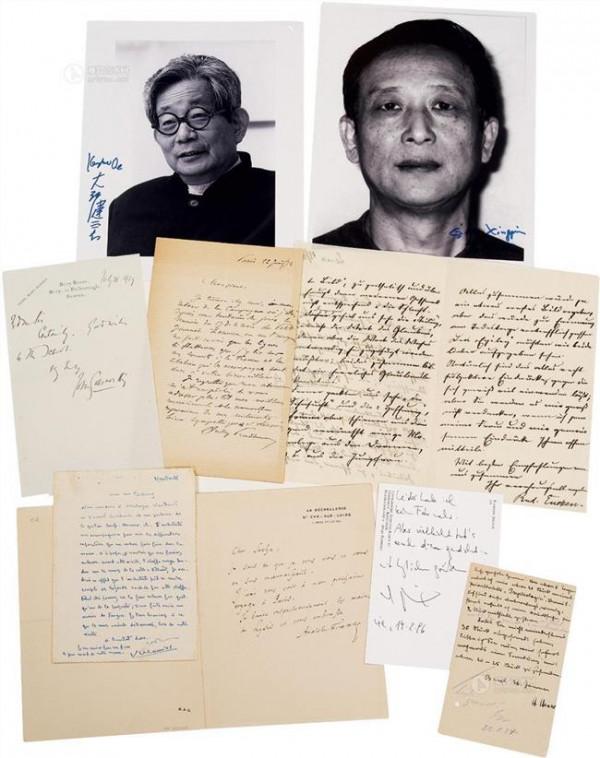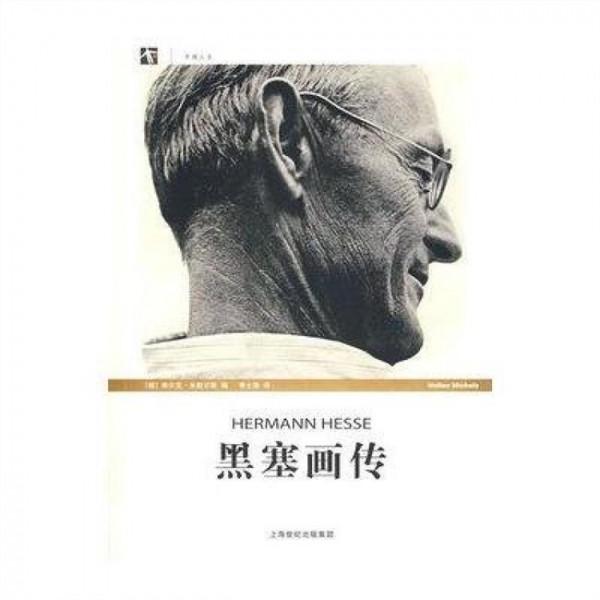塞林格一周 【试译塞林格】之一周一次不会要了你的命
一周一次不会要了你的命 收拾行装时,他嘴里叼着一根烟,眯缝着眼以防烟钻进去;因此看不到他的表情,也无从得知他是不耐烦还是忧虑,是恼火还是无奈。一个年轻女人像个客人似的坐在主人——这个大块头年轻人——的椅子上,在早晨的阳光下,她俊俏的脸庞一片斑驳,但依然很美。
不过最美的当属她的手臂,它们是小麦色的,且圆润健康。 “亲爱的,”她说,“我说,这些难道不能交给比利去做吗?” “什么?”年轻人问道,他的嗓音粘滞,正是一个老烟枪。
“我说难道这些不能交给比利去做。” “他已经上了年纪,”他答道,“打开收音机吧,这时候可能会有音乐,试试看1010台。” 女人向后伸出手,她的手上戴着一枚黄金的结婚戒指,紧挨着的小拇指上还有一枚镶着硕大祖母绿的戒指。
她先打开几扇小隔门,又啪嗒啪嗒按下了什么,最后还转动了什么。完成后,她重新坐好等待着,突然她打了个哈欠,丝毫不加掩饰。年轻人抬头朝她瞥了一眼。 “我说,现在出发是多么糟糕啊!
”她叹道。 “我会告诉他们,”年轻人边检查一叠叠好的手帕边说,“我妻子说,现在出发太糟糕了。” “亲爱的,我会想你想疯的。” “我也会想你的,我有比这更多的白手帕吧。” “我说,我会,”她接道,“这一切都太令人讨厌了,我是说,一切!
” “嗯,就是这样,”年轻人说,一边关上了旅行袋。他点了一支烟,看着床,然后直直地倒到床上。 正当他伸展四肢时,收音机也完成了热身,顿时,苏萨*的进行曲就占领了整个房间,那典型的似乎永远没个完的横笛。
“也许还会有一些别的音乐。” “至少不是现在这个疯狂的时刻。” 年轻人朝天花板吐了个不很圆的烟圈。 “你没必要这会儿就起床。”他向她说道。 “我就想这样。
” 已经有三年了,她还是一直用“强调”语气对他说话。 “不是起床!” 他妻子又重新调了一下收音机,他们两个都等待着,他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比较靠谱的爵士乐从收音机里流淌出来。 “我说,你现在还有时间像这样躺着吗?” “像这样躺着——当然,还早。
” 突然间他妻子显得着迷于某个煞有介事的设想。“我希望他们让你去骑兵队。骑兵真是可爱。我爱死他们衣领上的小剑了。而且你也喜欢骑马这一类的。” “骑兵,”他说,眼仍然闭着,“这种事是机会不大的。
现在大家去的都是步兵。” “太糟了,亲爱的,我希望你打个电话给那个脸上长着怪东西的上校。就是上周在‘菲力和肯尼’的那个。去情报局之类的啊。我是说你又会法语又会德语。
他肯定至少给你弄个尉官。我是说,你知道如果你光当个二等兵那可就太令人难过了。我是说你那么讨厌跟人说话讨厌一切。” “算了吧,”他说,“别再说了,尉官这回事,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好吧,我希望他们至少能送你去伦敦。
我是说那里好歹还有些文明人。你有芭比的APO*号码了吧?” “嗯。”他撒了个谎。 他妻子又在做另一个美梦了。“有些什么东西就好了,粗花呢啊,别的也好。”又是突然 地,她打了个哈欠,接着说了句错误的话:“你跟你姨妈告别过了吗?” 她丈夫睁开眼,猛地坐了起来,脚踮到地上。
“维吉尼亚,听着,昨晚我没来得及和她告别,”他说,“我希望你每星期带她去看一次电影。” “电影?” “不会要了你的命的。
”他说,“一周一次不会要了你的命的。” “不会,当然不会的,亲爱的,但是——” “没有但是,”他说,“一周一次不会要了你的命。” “我当然会带她去的,你真是疯了。我只是说——” “这要求并不过分,她已经不再拥有青春以及别的什么了。
” “但是,亲爱的,我是说她现在情况更糟糕了,我是说,她已经很古怪了,这一点也不好笑。我是说你并没有整天和她一起待在屋子里过。” “你也没有,”他说,“何况,她从不走出她的屋子,除非我带她到哪里去。
”他朝她靠得更近了,几乎就坐在床沿上,“维吉尼亚,一周一次不会要了你的命的,我不是开玩笑。” “当然,亲爱的,我是说如果你希望的话。” 年轻人突然站起来。“你能去跟厨师说我要吃早饭了吗?”他问道,正准备走开到别的地方去。
“先来个早安吻吧”她说,“你这个老男孩兵。” 他弯下腰,亲了一下她美妙的嘴,然后走开了。 爬完一段宽阔并且铺着厚毯子的楼梯,向左拐,他在第二扇门前敲了两下,门上钉着一块正式的白卡片,是从纽约的老沃尔道夫阿斯托利宾馆那儿来的,上面写着“请勿打扰”。
边缘还有一圈墨水淡褪的小字:“去爱国公债证券所,要回来,六点时替我在大厅里见汤姆。他的左肩比右肩高,他用一个可爱的小烟斗抽烟。
爱你的,我” 这些留言是写给这个年轻人的母亲的,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就读过,在那之后又读过几百次,此刻,1944年3月,他又读了一遍。 “进来,进来!”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年轻人走了进去。
窗户边上,一个五十出头的女人坐在折叠牌桌旁,她很漂亮。她穿着很迷人的米黄色晨袍,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白色运动鞋。 “嘿,迪基•卡森,”她说,“怎么起这么早,懒惰男孩?” 年轻人轻快地笑道,他吻了吻她的脸颊,一手扶着她的椅背一手翻看着摊在她面前的册子,这册子又厚又大,包着皮封面。
“这集子怎么样?”他问道。 “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这本册子——你都还没看过呢,你这个坏男孩——完全是新 的。
比利和库克会把他们的都留给我,你也可以把你的都留给我。” “那些停用的两分邮票*?”年轻人说,“是个好主意。” 他朝房间打量了一圈。“收音机怎么样?”这情景同他刚刚在楼下所经历的一样。 “非常好,我今早做了操。
” “现在,里娜姨妈,我要求你别再做这些疯狂的练习了。我的意思是你会拉伤的,我是说做了也没什么用的。” “我喜欢它们,”他阿姨翻过一页书,缓缓地说道,“我喜欢他们为这个操配的音乐,那些老调子旧旋律。
而只听音乐不做操显然是不够公正的。” “这是公正的。从今以后请停止吧!请少一点点正直。”她侄子说。他绕着房间走了一会儿,然后在靠窗的座位重重地做了下来。他的目光穿过外边的公园,想要在树丛中找出路子来告诉她,他要走了。
他曾希望她不是在1944年里需要盯着另一个人的沙漏看的女人。现在他知道他得把沙漏给她,作为礼物送给这个穿着白色脏球鞋的女人,这个收集已经注销的两分邮票的女人,这个是他母亲的姐姐、曾给他母亲在“请勿打扰”的边缘上留言的女人……难道她一定要知道吗?难道她一定要盯着他那个荒唐的闪光小沙漏看吗? “你这样摆弄前额的时候和你妈妈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你还有一点记得她吗,理查德?” “记得,”他马上接过话头说道,“她都不曾好好走过路。
她总是跑着的,跑一会儿歇一会儿。她替我的房间拉窗帘的时候总是吹着口哨,几乎都是同一个调子。我还是个小男孩时,那旋律一直萦绕在我耳边,大了却忘了。后来在大学里,我有一个来自孟菲斯的室友,有一天下午,他放了几张留声机唱片,有些是贝西史密斯的,有一些是提格顿的。
其中一首差点把我击昏,那正是妈妈当年吹的调子,正是!题目是《在星期天我也没法规矩点因为我一周七天都淘气》。
那个学期末,一个名叫阿特里维的遵守纪律的家伙插手这件事,从此我就再没听到过那首歌了。” 他顿了一顿,“我记得的就这么多。都是些傻事。 “你记得她长什么样吗?” “记不得了。” “她就像个包袱。
”他阿姨抬起那纤细优雅的手托着下巴,“一个房间里,如果你妈妈走开 了,你爸爸就无法像个人一样好好坐着。有人对他说话,他也只是傻傻地点点头,拿他那古怪的眼睛盯着你妈妈刚经过的那扇门。他是个有点奇怪或者说有点粗鲁的小男人。
除了赚钱和盯着你妈妈就再没有别的爱好了。哦,还有带你妈妈乘坐他买来的那艘怪里怪气的船。他原来戴一顶英国水手小帽,他说那是他父亲的。每到要去乘船的日子,你妈妈就会把那帽子藏起来。
“他们唯一找到的就是它,是吧?”年轻人问道,“那顶帽子。” 但他姨妈的目光重又落回到集邮册上。 “哦,这张可真漂亮。”她将一张邮票举到阳光下说,“他的脸是如此坚毅,还安着一个好似被撞歪的鼻子。华盛顿。
” 年轻人从靠窗的座位站了起来,“维吉尼亚已经让厨师做早餐了,我该下楼了。”他说着,却并没有离开而是走到了他姨妈的桌前。 “里娜姨妈。”他说,“请好好听我说一分钟。” 他姨妈把她那充满智慧的脸转向他。
“姨妈,嗯,马上就要打仗了。嗯,我是说你已经在新闻片上看到,在广播上还有各种地方听到了,是吗?” “当然。”她哼哼着说。 “好吧,我也要去,我必须要去。今天早上我就要走了。” “我知道你必须得去,”他姨妈说,并不慌张,也不苦涩地说“最后一个倒霉蛋”。
她太棒 了,他想,她是这世界上最神志清楚的女人。 年轻人站起来,随意地——只能是这样——把沙漏放在了桌上。“维吉尼亚会来看你的,老姐。”他告诉她,“她会经常带你去看电影。
萨顿下周有W.C菲尔茨的老电影。你喜欢菲尔茨。” 他姨妈也站起来了,不过很快地从他身边走过。“我写了封你的介绍信,”她宣布道,“给我的一个朋友。” 她此时站在书桌那边,打开左手边最上面的抽屉,充满希望地取出一个白信封。
然后她走回摊着集邮册的桌子,轻松地把信封递给他侄子,“我还没封,你想的话可以自己看一看。” 年轻人看了看手中的信封,上面是他姨妈刚健有力的笔迹,写着小托马斯E•克里夫中尉收。
“他是个很棒的年轻人。”他姨妈说,“在六十九连。他会关照你的,我一点也不担心。”她强调道,“两年前我就知道会这样了,我立刻就想到了汤米。他一定会对你关怀备至。” 她转过身,这次是慢悠悠的,不像前一次那么快地走向了她的书桌。
她又打开了另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大大的嵌在相框里的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年轻男人,穿着1917年的高领少尉制服。她颤颤巍巍走向她的侄子,举着照片给他看。 “这就是他的相片,”她向他指道,“这就是汤姆克里夫的相片。
” “我得走了,姨妈。”年轻人说,“再见了。你不会需要什么东西的,我是说你不会需要任何东西。我会写信给你。” “再见,我亲爱的,亲爱的男孩,”他姨妈边说边吻了吻他,“现在你认识汤姆克里夫了,他会关照你,直到你把一切都安顿好。
” “嗯,再见。” 他姨妈失神地又道:“再见,我心爱的男孩。” “再见。”他离开了她的房间,差点从楼梯上跌下去。 在楼梯拐弯处,他拿出信封,撕成两半,再两半,再又两半。
他似乎不知道该拿这些碎纸屑怎么办,就把他们都塞进了裤袋。 “亲爱的,早饭都冷了,你的鸡蛋还有些别的什么都冷了。” “你能每周带她去看一次电影的,”他说,“这不会要了你的命。
” “谁说过会啦?我有说过会吗?” “没有。”他走进了饭厅。 ------------------------------------------------------------------------------------------------------------------------ *约翰•菲利普•苏萨,美国军人,作曲家,指挥家。
被誉为进行曲之王。 ——来自维基百科 *陆军军邮局 *自1926年起美国寄信使用两分邮票,于1932年不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