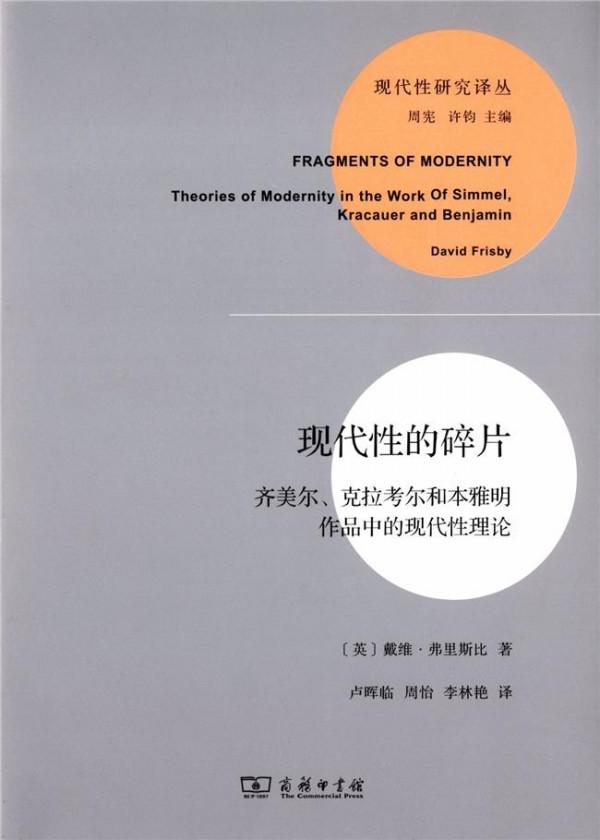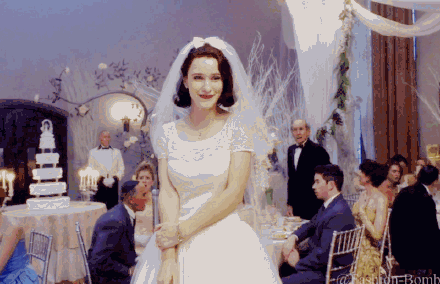齐美尔现代性体验 论齐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
20世纪的前三十年是德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社会学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M·韦伯、G·齐美尔、F·腾尼斯、K·曼海姆等,为此R·达伦多夫将这一时期称为“英雄辈出的时代”。
这些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前辈们,从理论设计和应用研究方面着手社会学的开创性工作,对社会学学科化、专业化的建设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齐美尔,作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之一(另外两位是马克思和韦伯)“,他自己就是一个使人感到既远又近的人,是一个潜在的流浪汉……他给他的循规蹈矩的同代人留下了一个不易归类的使人不安而又令人着迷的形象”[1]。
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们对他的定位也是不尽相同的:“形式社会学家”“、微观社会学家”、“互动论者”、“社会学的游手好闲者”、“唯美主义者”,甚至是“早熟的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等[2]。
虽然这些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各有不同,但无疑都代表了不同学人对其思想的一种把握。一个学者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殊荣”,或许说明他本身就值得我们去仔细探讨。 虽然齐美尔兴趣广泛、涉猎众多,但是只要稍微读过他作品的人都会对其“飘忽不定的随笔式”写作风格和“论述的非系统性”留下深刻的印象。
经过筛选和整理,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社会学领域的建树。齐美尔尤其关注在货币经济和工具理性日益奴役下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即是他对现代性的研究。
一、齐美尔对现代性的理解 20世纪初期以来,对于现代性的各种探讨不胜枚举,但是,齐美尔有着同时代人所不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捕捉现代性的能力”[2](59)。
戴维·弗瑞斯比认为齐美尔“是他那个时代唯一真正的哲学家,真正体现了时代的碎片化的精神”,是探索现代性的“第一位社会学家”[3]。
并且,他把握现代性本质的能力,不仅反映在对现代性的实质分析之中,更体现在独特的分析角度上。也就是说,齐美尔不太注重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变迁、科层制、理性化和世俗化等探讨现代性的传统话题,他所关注的只是一些现代性的“碎片”:都市生活、货币、陌生人、技女、情感、秘密社会……“他从来没有刻意的去谈现代性,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中一些常见方面的探讨,甚至是十分微小的事情的分析,来昭示现代性的特征和问题。
”[2](62)正如弗瑞斯比在评价齐美尔的《社会学》时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在此得到了一种动态的表达: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存在的总体性和个体要素的任意性,得以阐显。相反,集中的原则,永恒的要素,则荡然无存。
”[3](330) 弗瑞斯比认为,齐美尔是论述现代性的第一位社会学家,但这里的现代性是指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①中所谓的“捕捉现代生活瞬间之美的能力”。
齐美尔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把握现代性的研究对象,如“桥与门”、“椅子”、“把儿”“、服装”“、时尚”“、音乐”“、性”和“货币”等。这显然与其他社会学家在研究现代性时一贯关注的话题,如马克思的社会关系与人的异化、涂尔干的社会团结与社会分工、韦伯的理性化与科层化等大相径庭。
在当时,齐美尔一直是“学院里的局外人”,是一个“潜在的流浪汉”,但他“才华横溢,使得那些居于高位的、那些老朽的、那些一心向上爬的各色人物感到震惊和不安……他像昆虫牢牢抓住树叶一样,以最精确、最令人信服的洞察力牢牢的抓住了他要研究的对代写论文象。
”[1](216)齐美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即“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这个世界在躁动的灵魂中凝固的内容均已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均已滤尽,而灵魂的形式则纯然是运动的形式。
”在齐美尔看来,现代性主要表达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心理体验和生活感触。
现代性最突出的特征在于“碎片性”“、偶然性”和“不连贯性”。齐美尔认为“,我们总是在各个不同的平面之间来回循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根据不同的规则构成了世界总体,但从每一个平面来看,我们的生命在任何特定的时刻获得的只是一个碎片。
”[5]齐美尔之所以如此关注这种“碎片性”,因为在他看来“,从独特的东西中可以发现典型,从偶然生成的东西中可以发现规则,从表面和短暂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6]。
既然如此,对现代性的把握就不能仅从外在的经济、政治结构来看,还应注重在文化结构和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真切体验和主观感受。
所以,齐美尔在其一系列着作中描绘了现代人的“时尚”、“冒险”、“旅游”、“音乐”、“自我隐退”、“赌博”和“秘密社会”等日常活动和内心世界。他在看似平常庸俗的生活世界中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性的内涵,并通过作为“社会快照”的“生活碎片”昭示了人类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境遇。
他犹如一位“丹青妙手”,不需浓墨重彩,只是信笔涂抹,却为社会学现代性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 二、现代性的危机———“文化悲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由垄断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与此相伴随的社会矛盾也随之凸现。
齐美尔不仅对一般的社会矛盾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而且从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矛盾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成伯清认为“,在齐美尔对现代性的分析中,与以前的理论大师相比,其实有着一种根本的范式转移,即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变换为文化社会学的视角。
此一转变在《货币哲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即齐美尔不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来讨论货币,而是着眼于现代的社会文化形态,来阐释现代文化格局中个体的生存样式和生活感受。
”[2](91)耐德尔曼认为,齐美尔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模式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如下表所示[2](93):在这里,我主要阐述齐美尔的“文化悲剧”理论。在齐美尔看来,文化悲剧根基于现代社会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说“:我把文化理解为一种对灵魂的改进……生命精神化的形式,以及内部劳动和外部劳动的成就。”[7]客观文化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创造的一切成果,它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种则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制度、文化、宗教、艺术等。
而主观文化则是社会个体创造、控制、吸收、理解各种客观文化的能力。 齐美尔认为,从理想状态来看,主观文化影响和形塑着客观文化,同时又受客观文化的影响。
即“客观文化的主观化”和“主观文化的客观化”,从而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的这种和谐被打破了,二者面临着“深刻的、久远的对立”。
一方面,客观文化一经产生,就逐渐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它超越了创造者的控制,凭借独特的规律性急速成长。而另一方面,社会个体创造、吸收和控制客观文化的能力却在低速前进,甚至不断萎缩。
所以,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越来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微薄的个人力量无法跟上文化产物的步伐,我们注定越来越不懂我们创造出来的世界,而且我们逐渐被这个世界所控制”[8]。
换言之,人类创造了文化,目的在于让它服务于人类,但文化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客观形式和固有的发展规律,使其既违背了它产生的原因,又脱离了它的目的。“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其需求和愿望都受到支配控制的客观世界中……技术产生多余的‘产品’去冲塞‘人为的’需求,科学也产生‘多余’的、无特别价值的知识,这些知识仅仅是科学活动独立发展的副产品”[1](211)。
同时,齐美尔认为,在现代社会,对于感性刺激和时尚的追求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终极目标。
“白热化的竞争,使得现代人在赢得一切的热情和失去所有的恐惧之间疲于奔命,以至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那么,还有什么情感力量能够留下来呢?时代的压力已经驱走了早先生活方式留下来的、至今仍是人们常识的较为高尚的情感力量的成分……每个人,无论是平庸还是高尚,都无拘无束、无所顾忌的在欢娱的江河中沉浮,只能在娱乐和性生活中找到些许的感觉和发泄”[9]。
在现代社会,个体不再像以前那样举止优雅、从容镇静,都已经变成了异化的人。 在齐美尔看来,造成现代社会“文化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
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专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使得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制造复杂、精细的微观世界。但是个体在专业化的同时却失去了对整个客观文化的完全了解和控制能力,任何人在成为某一领域专家的同时却在其他领域变成了“彷徨失措的门外汉”。
“在今天,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越来越少,而专家型的人物却愈来愈多,同时精细的劳动分工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工作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劳作,没有激情,没有创造,有的只是机械的重复。
工作中的人际交往,也只不过是与自己差不多的人之间的会面而已,没有多少新奇的事物可供分享”[10]。 对此,犹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一样,齐美尔虽然坚信人类社会最终将从“文化悲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他又怀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情。
“‘未来的牢笼’(M·韦伯语)将把人类禁锢在社会功能里,完美的客观世界的现实将以人的心灵的衰退为代价”[1](212)。
其实,在对待资本主义文化的态度上,除了齐美尔之外,还有两派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具有强烈批判性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开启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
他们认为,启蒙精神在使人类摆脱愚昧的同时走向了它的反面———“启蒙的自我摧毁”,产生了相应的两大恶果:知识沦为工具、人异化为物。后来,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当代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它成功地创造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变成只会肯定和维护现实的“单向度的人”。
在《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中,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资本主义需要一场由“新左派”领导的“文化革命”。
20世纪6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继续推动了批判理论的发展。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1)中,哈贝马斯鲜明地提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化和非商品化的领域,现在逐渐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金钱和权力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习惯于将一切都只作为自己实现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中,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进而在《沟通行动理论》(1981)中提出了酝酿已久的“沟通理性”。
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以韦伯和贝尔为代表。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其实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他还从“价值中立”出发建立了许多“理想类型”:科层制、合法统治类型、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等。
但是,到了晚年,韦伯逐渐认识到社会理性化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
所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韦伯满怀忧虑的写道“: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
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1]贝尔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力”(即“贪婪攫取性”)的强力冲击下,“宗教冲动力”(即“禁欲苦行主义”)节节败退,很多人不再具有“天职观”和“荣耀上帝”的心态,而只是一味地贪图享乐、攫取名利,造成普遍的信仰沦落、价值迷茫[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