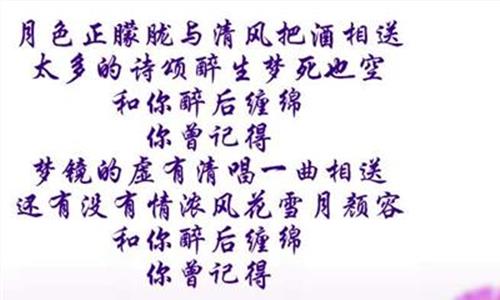范忠信逃离 范忠信:逃离 也算是一种劝谏(摘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范忠信教授的博客)
逃离,也算是一种劝谏 ----兼作中南离别之际的初步自我反省 范忠信 一个人调换一个工作单位,本是极其寻常之事。
一个教书匠,在一个学校工作了十二年之后,要调一个单位,就更加寻常不过了。
这种调动,应该是,放的悄悄放,走的悄悄走。谁也别在乎! 我本来就这样想,也在这样做。但是后来,事情有些出乎意料,听说有人很生气。在表示歉意之外,不能不有所说明。 一 因为我书生意气、自以为是、一根筋、认死理的为人处事风格,有同事很不喜欢,因而不想理我,这很正常,我很理解。
但是,若因厌恶我而无视中南法史学科的共同事业,不在乎把它赶快安排妥当或赶快理顺了,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也无法理解!
因为向校院领导两次呈交过正式书面请调申请(无人给我传达过正式答复),因为9月9日给全体校领导手写过一封纸质信函(而无一人一字赐复),因为近几天给有关校领导打通过多次电话(但都是通了而不接听),我无可奈何只好用这种博客发文方式了。
因为我怕耽误了学科点的公事! 自我9月1日象征性到杭州师大报到上班(实际离校手续直到10月15日才办完)以来,在我曾经工作十二年的母校中南法财大学,学校、学院、校直部门,没有一个人代表官方,跟我说过一句话,或传达过一个字的决定!
我傻乎乎地一直等着,等呀等,等了两个半月了。下面这些事情,总不是个人私事吧?总得有人理睬吧? ——我主持的法律史学科建设事宜,移交给谁呀? ——我主持的法律文化研究院事宜,移交给谁呀? ——我主持的法律史博士点事务,移交给谁呀? ——我作为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的事务,移交给谁呀? ——我主持的《中西法律传统》年刊,移交给谁呀? ——我作为“法律史学术网”负责人的有关事务,移交给谁呀? ——我掌握的研究院、学科点建设经费本,移交给谁呀? ——我掌握的学科建设多年档案材料,移交给谁呀? ——我作为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的职责事务,移交给谁呀? ——我的办公室及使用中的学校财产,移交给谁呀? ——我正在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移交给谁呀?未来还参与不参与指导呀? 这些事情,两个半月来没有人理睬,所以法律史学科的有些事情处于搁浅状态,部分研究生也处惶惶不安状态,学科经费报销都没有人签字……。
我一直想移交出去,因为我怕耽误公事,也跟学科点的有关同事商量过,但他们都不愿意接。他们说:学校、学院没有一个人明确地宣布我来接替你,凭什么咱俩“私相授受”呀!
所以直到今天,两个半月了,我既无法主动移交这些事务,也没有一个人奉命找我接替事务! 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大概是少有的! 大家众望所归应该接替主持学科点建设事务的陈景良兄,据说校领导曾电话或短信相约过一两次,要谈法史学科点之事。
但两个半月来,除了大约两周前与一位校领导相遇中匆忙谈过十几分钟以外,至今仍没有被任何正式谈话!更不用说有任何书面决定了!至于景良兄很认真拟呈的关于法史学科及研究院发展的一个书面建议报告,也是泥牛入海!
关于离开中南,我设想过一些结局,但做梦也没有设想过这样的结局! 这毕竟是我倾注心血、挥洒汗水十二年的地方!是我这一辈子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
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深深地感到挫败和凄凉。就是犯了罪被流放充军,还得有两个差人押送上路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而引来如此制裁? 二 出现这种情形,原因无非是以下三者—— 第一,因为非常讨厌我,所以不幸殃及了法律史学科的公事!
第二,因为领导们太忙,所以根本无暇顾及法律史学科的事情! 第三,因为没有恰当人选,或因为涉及的事情复杂,不好遽然解决或答复! 无论是那一种情形,我都感到痛心。 我相信中南的同事们,特别是法律史学科的同事们也痛心!
就第一种可能而言,领导都是有高度政治责任心和觉悟的人,应该不会如此呀。就算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讨厌一个人,没有必要株连他所在的学科专业。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十几人的法律史学科队伍,他们还坚守在此,还需要正常工作生活和发展。
目前这种空缺或乱象,对他们有害,他们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的! 就第二种可能而言,也会让法律史同事们痛心灰心。法律史学科毕竟是法学的三个重点学科之一,毕竟是原创型博士点之一,毕竟是我校法学一级博士点铸鼎时的三足之一,总不至于卑微卑贱到在其负责人离任之际长达两个半月都没有一个副处级以上领导拨冗来正式安排一下交接事宜吧?总不能说我上面列举的这些事情,对于学校,对于学院,都可以忽略不计吧?比起学校的大事而言,你可以说那些都是小事。
但是,学校的大事难道不是这些小事积累而成的吗? 就第三种可能而言,也不应该这样处理呀!就算没有满意的人选,就算景良兄提出的建议不好马上答复,那么至少先暂时明确授权一个临时接替事务的人总是可以的吧?就是把眼下的具体事务接替过去,免得耽误了学科点的共同事业,总是可以的吧?一句官方正式话语而已,一张官方正式决定而已,有那么艰难复杂的吗?两个半月了呀!
三 忠信在中南工作十二年,现在离开后反过来自省,发现自己的确是有很多缺点或错误,我是需要自我认真检讨的—— 第一,不太考虑中南的校情和现实,常自以为是地提出一些主张或建议,还没完没了地逼着领导同意,甚至对领导以有些不谦卑的口气慨陈理由,比如建立法律文化研究院就是典型(当时的确得到了校领导的宝贵支持,至今感激!
但是,不知何故,现在学校正式列出的下设单位目录表上,有“廉政研究院”,没有“法律文化研究院”!
),以至于有人说“这个人就是这么头脑简单,政治上不成熟”。 第二,常常对自认为不妥之事提出批评,自以为是。过去十二年里,就我校考试纪律败坏问题、开课选课缺乏公平竞争问题、法律史课程开课课时问题、研究生指导人数未定上限的问题、法学学科在全校资源分配中的公平份额及票决机制问题、程汉大教授的博导资格及实际招生问题、法学研究生西迁首义校区的问题、后勤集团承包校内工程报价是校外数倍的问题、校园内公共设施损坏而无人管的问题、绿化科砍树及割草剪枝噪音震天的问题、公共绿地水管破裂漏水无人管的问题等等,我的确先后提出过好多次批评建议,我的确把自己真的当成了学校的主人(因为我是学校教代会副主席)。
以至于有人曾说“这个人好是好,就是意见太多了”。 第三,比较在乎个人荣誉,名利之心较重,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尽力按照官方提倡的标准去做就应该得到好的评价。比如得到了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津贴专家这样的荣誉,也没有特别感激领导,好像认为是自己应该得到的(其实不是如此,只是不会表达感激而已;甚至认为进一步努力工作就是对领导的最好感激)。
如果因为对本科生打分严格一点、高分比低一点而导致选课人数下降,不是先检讨自己,而是责怪学校没有对认真、严格的教师进行适当鼓励和保护。
以至于有人说“这个人一贯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 第四,常常自以为是地认为在大学里即使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也应该受尊重、有尊严。
当看到在会场上把副科级领导都介绍完了以后再介绍教授代表时,当参加毕业典礼作为教师代表上台发言看到主席台上三四排领导干部座位竟然没有一个教师代表席位时,当知悉中原楼(校总部办公楼)落成典礼鸣炮奏乐玩狮子一两个小时大小官员悉数出席而没有一个教师代表参加时,当看到校庆成了领导的庆典而无职务的教授没有被安排出席一场活动时,就忍不住要说话,甚至采取一定的抗议行动。
以至于有人说“这个人真不知道自己是谁”。
第五,在学生面前常常以“名士”自居,常以“士大夫”口气对时事政治横加批评,常当真以为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公,当真以为党章和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就应该兑现,还曾起意起诉违反宪法原则滥调民选公务员的党内机关。
在校内每学期至少做一个义务讲座,常常以这种特色而听众爆满,这可能是最让人忌讳或讨厌的事。因此,有学生在校内网页上称我为“精神领袖”并多次热议之后,我就彻底地孤立于一切正式体制了! 第六,没有经常及时与学科点成员进行良好的沟通,“打成一片”的时候少,自己独自办自己认为对学科点有益之事的时候多。
很多事情,常常认为动员大家一块儿做很难,因为不是任何干部,没有法定的任何下属,手里没有任何资源。
与其去动员别人还做要布置说明、要检查修改、要看同事高兴不高兴的脸色,最后还闹一个别人只是私人帮你私人的忙之恩典,不如自己动手做完算了。当然,最关键的原因是,每次这种事情都是三五天的时间,而要找的材料浩如烟海,要填写的表格动辄几十页一大本,也根本无法按部就班地组织班子一起做。
这些年为法律史博士点、法律史省级重点学科、法律史国家精品课程、法律史优秀教学团队、法律史硕士点、法律史年刊和网站、法律文化研究院、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还有法律史学科申报没有成功的湖北省优势学科或特色学科、优质教材、网络课程之类)等等的申报、建设、检查、评估、统计,先后填写过上百种(本)表格……,那工作量,那麻烦,只有亲自主持或为主做过这类事情的人才能理解或体会!
除了近几年有武乾、会林、培锋、艳华、丽娟、李栋等同事帮着做了上述工作的一部分以外,其余大多数填表申报,我都是第一体力劳动者,好多时候是唯一劳动者!
谁关心过或同情过我呢?我一天工作十三四小时,谁给了加班费呢?(有人认为,教师站台上课才算上班,其余时间即使干了学科建设的事情,也不过是为了个人好处而已)当有个别误解我的同事到领导那里诉说我的不是时,领导找我说“不要搞内斗”,我深深地感到凄凉。
我有那么弱智吗?一个自己想多做点业绩出来证明自己有贡献的人,只会唯恐得罪人,只会尽量讨好身边的人以减少阻力,那里有精力去搞内斗呀。我要是会搞内斗,不早就政治上成熟和发达了吗? 以上六点反省,虽然有“诉苦”的因素,但的确也有此时的检讨自责。
试想,如果我在上述每一方面都更加讲政治、顾大局、懂国情、懂校情、懂人情、讲人缘、尊重现实、适可而止、不自以为是、不个人英雄主义、不书生气十足、不图名不图利、不“宽以待己严以律人”、与领导们打成一片,我不是就会得到体制的高度认可吗?这的确是该自责的!
一个人是不该把自己看得太有能耐了,不该把自己看的太干净清白了,不该把自己看得太一贯正确了!
人都是有罪的,都是有缺陷的! 四 因为进行了这样的反省,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10月29日晚的讲座后,同学们反复问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南,我当时真不便多说,说了就会造成友人的误解。
但不说又对不住敬重我信任我的同学们,如今只好把理由写在这里。 选择离去,是一个于公于私、与校与己都利大于弊的选择。不然,我陷在过去的利害恩怨格局里出不来,陷在“学科建设”蝇营狗苟里出不来,主事者们对我的看法也会在过去的固定框架里出不来,现体制对我也非常不好对待处理!
这一点我非常理解! 所以我选择逃走,算是落荒而逃吧。逃走,也算是一种劝谏吧!也算是实践“三谏之而不听则逃”的古训吧! 只不过,走出这一步,花的时间太长了点,整整五六年。
说走不走,领导和学生都听烦了、听腻了。所以有领导说“他哪年不说要走呀?不都没走吗”。出门偶尔碰到同事,有的半开玩笑地说:“怎么还没走哇?”“又回来了?”不过,我是中南政法从校外引进的学者中服务时间最长、走得最晚的一个。
迟迟不走,似乎现在成了一种过错了。跟我有接触的所有同事学生可以作证,这些年我真的没有故意声张要走之事,只不过关心我的学生比较多,经常有同学道听途说地谈论(也的确有联系他校之事从对方传出后有学生向我求证时,我如实回答),所以造成了是我自己老在喊“狼来了”的印象而已。
为何迟迟不走?孔子离开鲁国时说“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正道出我此时的心情,因为这是我的父母之邦,父母和兄弟姐妹近在咫尺。
为何迟迟不走?还有事业的留恋。十二年来自己主持、大家参与艰辛打拼建成的法律史基地——博士点、省重点学科、国家精品课程、年刊网站,特别是研究院温馨的小院子,特别是出色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队伍……。
当然,迟迟吾行,也是等着学校有些积极的变化,我期待的这些变化当然是公共事务方面的,不是个人私事方面的(自起了调离的念头以来,我没有向学校伸手要过任何“待遇”——包括经费、职务、荣誉。
此前也是自己主动辞去党委委员、科研处长职务的。据说这次我真的走了,还有领导问“他怎么会真的走呢?我们还等着他提条件呢!”)。最后,我感到这样的变化无法看到了,可能直到我退休也看不到了,就只好走了。
所以,“迟迟复迟迟”。 至于有领导说我是“数年求职多所大学均被婉拒”,我只好报以一笑。是不是被婉拒,我自己知道呢,领导心里也清楚呢,那几所大学力邀我者还可以作证呢。
“这种人,没人要才好呢!”有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 至于有人说我是冲着高额“转会费”而来,只说对了一部分。杭师大的确给了我更高的科研经费和工资。但是,如果仅仅有这些,远不足以吸引一个年过半百的创业者离开自己开创的基业、离开自己的故乡并远离父母和兄弟姐妹、离开自己的不小的“粉丝”队伍、离开自己大半辈子积蓄转化的住房之所在的。
我是一个生活极其简朴的人,生活条件比猪狗好一点就很满足。“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我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我到底要什么而在中南得不到呀?其实不过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希望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被尊重或重视一些,希望在因为自己较为当真地试行官方宣布的教学、招生、考试、答辩、科研评价标准而被孤立时得到来自有权力者的支持明显一些,希望自己过去的业绩或现在仍在进行的学术事业得到来自有权力者的肯定更多一些,希望书生气十足且没有任何官职的人在中南更有尊严一些……。
仅此而已!(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李汉昌兄,尽管他现在“进去”了,但他是中南校领导中我唯一可以坦诚交谈的朋友。
是他让法律文化研究院真的有院子。)当然,朋友也可以骂我:说穿了,还是人格不独立,太注重外在评价,名利之心太重——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老毛病!
五 要离开,真不能简单地说是对谁有意见。我与校领导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他们每个人私下都是我的朋友!虽曾跟两位校领导在开会讨论公事的场合有过剧烈争执,但那都是君子之争,且事后都相逢一笑了。
跟其余所有领导,包括校院两级领导,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快。他们个人肯定谁也不想多得罪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曾经在学校付出十二心血汗水并建功立业的直肠子的人。因此他们现在对我调动事宜这样的特殊处理模式我也很同情理解: ——自9月上旬就下令停发了我和妻子的工资及津贴(当然,后来经我妻子交涉,恢复了大部分,我很感激),尽管那时候我们的调离手续还一丝也没有启动(我们还在学校正常上班工作),且直到10月15日才办理完成。
——当因杭州方面手续困难要我妻子暂缓一步办调动手续时,人事处向我们传达了上面的意思“要走必须一块儿走”。因为程序反常被迫提前办手续,以至于我妻子至今还没有落实工资转接。 ——当法学院研究生工作秘书范敏老师代欲报考博士生的学生问我明年能否继续招生时,院有关领导转达上面的意思是“明年起不能招生,已经带的带完”(尽管与此同时所有从学校出去当副厅级干部的同事都被学校赋予长期继续招生、指导的权利)。
——我代表学科点与北大出版社已经签约并拟定大纲正在率同事编写中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也被院里宣布要“调整主编”(早在我提交正式请调报告前一两个月,教研室里就有人要废除我和景良兄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改用别的教材)。
还有一些,不必列举了。 这样做,我理解不是个人恩怨,是体制的结果。因为他们是在中国,是在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是在大学已经不是大学的体制之下,是在没有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体制之下!
他们也身不由己!我深深地同情他们! 至于在我离开中南的方式上,可能会使有的朋友不高兴,我也是要道歉的。 我的确不是有意如此的,我很害怕因我的行为惹朋友不快,更怕因此妨碍调动进程。
整个过程我是尽力谨慎、低调办理,诚恳说服人而已。至于杭师大在校园网上报道我加盟的消息,我事先根本不知;中南的学生转帖消息到“浓情中南”并大加评议、研究生会学生会在“10.29讲座”过后为我添加催人泪下的送别项目,我事先都是不知道的。
这一点,可以派人调查所有参与此事的学生就清楚了。如果有朋友一定要说是我有意“炒作”,那真是高估我的智商了。我要是真有如此聪明,还能落到今天“灰溜溜而去”的下场吗? 2010.
11.14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