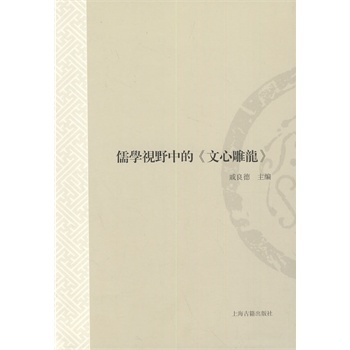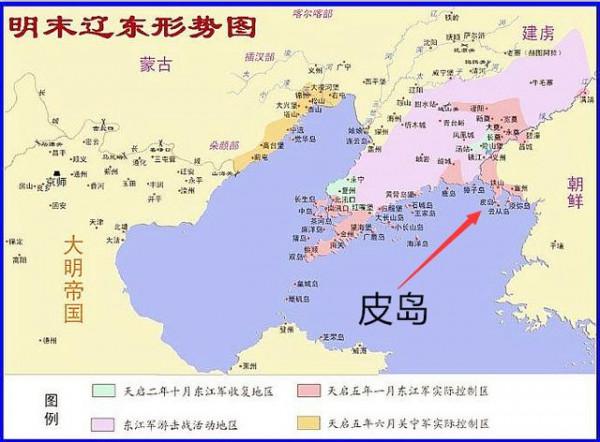刘勰的文心雕龙 也说林其锬与《文心雕龙》《刘子》的研究杂味
元旦前,林其锬先生送来他和夫人陈凤金合编的新著《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和《刘子集校合编》上下两册,这是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十六开本。沉沉三大册,共2300余页;历时三十载,凡220万多字。在日前举行的首发式上,与会专家学者称这三大册是“《文心雕龙》和《刘子》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是“我国古籍整理研究中的传世之作”。
我认识林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是“五缘文化”论的始作俑者。九十年代初,他和一些朋友创立“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研究室”,所谓“五缘”,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其后,五缘文化研究列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的《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重点课题。他们先后在上海和福建多次举行有关五缘文化学术研讨会。不久,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正式成立挂牌,他任所长。我与林先生常在五缘文化会议上见面,经常交谈,我知道他的学术研究兴趣点不仅在五缘文化,而且在古籍整理研究,尤其是在《文心雕龙》和《刘子》研究方面建树甚多。
现在《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和《刘子集校合编》上下册问世了。可是,面对这两部大著,林先生却感慨万千,他说可以用弘一法师的名句“悲欣交集”来形容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他又念了一首顺口溜:“‘刘子’‘文心’书,三十载寒暑。谁知个中味,字字皆辛苦。”
三十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林先生是福建闽侯人,在中学时代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上海航空学校,毕业后留校教书。六十年代初,我国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期”,那时,许多报刊贯彻“双百方针”,讨论学术。如《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就对《文心雕龙》的一些篇章展开热烈争论。时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深造的林先生对这场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当看到有关《文心雕龙》及其作者刘勰的文章,他就搜集、阅读,甚至剪贴,一有时间就研读,做了许多卡片,分门别类,编辑成册,题为《刘勰〈文心雕龙〉资料汇编》。《文心雕龙》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他都与《文心雕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弃不离,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研读。
八十年代初,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林先生带着研究《文心雕龙》的“心结”,投奔上海社会科学院,那时该院还没有文学研究所,他在经济研究所当了两年编辑,搞了六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不过,就在此时,他在寻找经济史史料时,发现了《刘子》一书。《刘子》将经济(《贵农》)置于政治(《爱民》)之前,体现作者的治国思想。而且在新旧《唐书》和诸多著录、著作和古版本中,赫然明题:“《刘子》,梁东莞刘勰撰”。刘勰,这个《文心雕龙》的作者,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林先生的脑中。所以,一看到“刘勰”二字,他便会神经质地做出敏感的反应。他开始将《刘子》与《文心雕龙》“捆绑”在一起研究,寻找两者之间的异同之处。
林先生有一股“闯劲”,一旦认准方向,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发现了《刘子》,兴高采烈,一头栽入故纸堆。他向所里申请要求研究《刘子》,但先后五次都遭到否定。理由是:这不属于经济研究所的专业!但是,研究《刘子》和《文心雕龙》的强烈欲望,驱使他下定决心:“不批准也要干。”他除了完成所里的课题规划任务之外,便在业余时间一心一意扑在《文心雕龙》和《刘子》的研究上。他一无经费,二无时间,“偷偷摸摸”,埋头苦干,最终还落个“不务正业”的骂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常以此自勉。他的夫人陈凤金是他的同学,供职于《上海文学》编辑部,是一位作家,夫妇俩互相鼓励、互相配合下,经过四年的“打拼”,《刘子集校》于1985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该书不仅集中了全国现存的所有版本和前人的主要校勘成果,尤其是对众说纷纭的《刘子》作者问题,以翔实的资料证明,《刘子》作者,即《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林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它的出版竟然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的认可和肯定,称是书“搜罗广博,考校详审,所取得的成果大大超过前人”。
1991年,林先生在上海书店又出版《敦煌遗书〈文心雕龙〉集校》,王元化为其作序,称这是“集大成之作”。
国内外朋友给予很高的评价。2000年,《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镇江举行,国内外“龙学”界名家荟集,高朋满座。为纪念这次大会,镇江市政府在南山风景区文苑公园建造一座“文心碑”。汉白玉石和红色大理石的碑体镌刻了两本书:一是元刊本《文心雕龙》,一是林先生的《敦煌遗书〈文心雕龙〉集校》。
这是对林先生学术成果的最大肯定和最高奖赏。此时此刻,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写下了《题镇江“文心碑”》俚句一首:“标心送怀有《雕龙》,己身疏才但雕虫;何见文苑容《集校》,知音亭畔望星空。”
现在,林其锬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和《刘子集校合编》又出版了,他可谓功成名就了。但是,谈起他坎坷的研究历程,他感叹地说,“酸甜苦辣三十载,功成不忘前辈恩”,尤其是张光年、王元化、顾廷龙诸先生对他的关心和帮助,他永远铭刻在心。
大家知道,张光年(光未然)是一位著名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和《五月的鲜花》就是他的代表作。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又是一位博学多才、功底深厚的大学问家。
他在《离骚》、《文心雕龙》研究方面很有成绩,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林先生认识张光年是在1986年3月。那时,院部办公室的同志通知他,说有一位北京来的领导要见他和他的夫人,要他们明天去静安宾馆403室。
这一突如其来的通知让他们莫名其妙,他们是一介书生,平时搞课题,写文章,与政治没有关系,北京的领导找他们,到底是什么事呢?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会儿“清污”,一会儿“反对自由化”,知识分子心有余悸。
林先生满腹狐疑,惴惴不安。次日,他和夫人鼓起勇气去静安宾馆。一进门便见到王元化和时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茹志鹃在那里,还有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先生,他们不认识。元化看到他们有点紧张,便向他们介绍张光年先生,还说:“光年老对你们的《刘子集校》很重视,不仅认真看了,而且还做了不少批语,今天请你们来,是想了解你们这本书的出版情况。
”接着,光年先生说:“《刘子集校》是一本好书”,“李一氓同志很赞赏。
在中央开中顾委会议的时候,李老见到我,对我说:‘我们古籍整理(按:李老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出版了一本同你有关的书,叫《刘子集校》,你看过没有?’我答:‘没有。’李老还开玩笑对我说:‘那你还当什么《文心雕龙》会长呀。’他随即叫秘书回去取来你们送给他的那一本转送我了……你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真要感谢你们。”他要林先生介绍刘子研究的情况。
听了王、张二位前辈亲切的开场白,林先生他们紧张了一昼夜的神经顿时松驰了。他向他们汇报如何进入《刘子》这个研究领域,又如何搜集版本进行校勘和考证的。在汇报过程中,二位前辈时而插话,时而点点头。他们交谈了近三个小时,临末,光年老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下个月在安徽屯溪举行的《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并要林先生在会上就《刘子集校》一书做个发言。林先生夫妇还不是《文心雕龙》学会会员,现在会长亲自邀请他们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这是对他们最大的信任和鼓舞,他们真是受宠若惊!
1985年4月15日,林先生自费和夫人赴屯溪参加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光年老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林先生他们的《刘子集校》,明确表示:“我偏重于接受‘刘子即刘勰’的见解,我认为林、陈的考证是有根据的”,“我相信《刘子》与《文心雕龙》两书很可能出于一人之手。
两书在政治见解、学术见解、文艺见解、人生哲学以及文体、文风、语言等方面,都有不少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还指出:“研究《刘子》,对深入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刘勰时代和刘勰思想定会有很大帮助。
”会后,光年老还特地挥毫写了《题赠林其锬、陈凤金同志》诗:“骐骥跨层峦,志在千里外。放眼花果山,登临成一块!附记:林、陈夫妇以四年业余时间,成《刘子集校》一书。
我深服其用力之勤,考订之精。题赠俚句,祝他们俩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成功。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八日屯溪。”林先生向我出示光年老的诗稿原件,深情地说:“光年老的鼓励是支撑我们以后不懈努力研究《刘子》和《文心雕龙》的巨大力量。”
王元化先生是国内外《文心雕龙》研究的权威。他最了解林先生,他知道林先生的研究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为了研究《文心雕龙》和《刘子》,林先生几次心脏病突发,送入医院治疗。在他看来,当今学术界,像林先生这样执着、勤奋、忘我,这样甘于寂寞、甘于清贫、甘于坐冷板凳的人是很少的,所以他对林先生十分赏识,另眼相看,尽力支持林先生的工作。
1985年3月,当林先生向所领导请假,要求出席在屯溪举行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时,所领导居然不批准他出席,理由还是“不务正业”。
林先生向元化汇报,元化先生“火”了,叫林先生直接去找刚由市委宣传部下来任职的副院长,并说:“告诉他,这是我王元化要你去参加的!”林先生说他很少看到元化发这样脾气的。
他生怕激化自己与所领导的矛盾,顾全大局,没有去找这位副院长。后来,他请了事假,自费和夫人去参加这个会议。在开幕式上,元化特地向大会介绍林先生夫妇,他们站起来向大家鞠躬。因坐在最后一排,人们看不到他们,元化又要他们走到前面和大家见见面。
同时,元化又向大家说林其锬单位不批准他来参加这次会议,他是请事假自费和夫人来参加的。元化话音刚落,全场哗然!与会者以热烈的掌声来表示对林先生的支持!
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外兴起《文心雕龙》研究热,人们称之为“龙学”,“龙学”研究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而且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学术成果越来越多。为了保存资料,促进交流,开拓思路,厘定课题,力避重复,经光年老同意,元化提出编纂一部《文心雕龙年鉴》(后改名《文心雕龙学综览》)。
“综览”是在元化直接指导下编纂的。他自己拒不当主编。主编是杨明照,林先生任副主编。1995年,“综览”送上海书店出版。但是出版经费一时未能落实,元化亲自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提出要求资助。
书出版之后,元化还特地写了一篇短文,指出:该“书的编辑出版几乎全由林其锬一人承担……主要应归功林其锬。至于关于此书的学术价值,我认为是一部很有用的好书,是学术性和工具性的综合读物”。
元化知道林先生编辑“综览”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所以,一向主持公道的老部长专门写了这短文,要林先生交给他们单位领导,希望能正确理解林先生。然而,林并没有这样做,始终把信放在家中,元化多次问起,他一直向元化隐瞒说是送了。林先生说,他不愿意让人误会藉名人以扬己,何况“综览”之成实赖众力。
尤其令林先生感动的是,元化身患重病时,仍然十分关心林先生的工作。他在病榻上为《刘子集校合编》题签,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遗墨;他在病情恶化卧床不起的时候,亲自提笔批准了《刘子集校合编》的出版补贴经费。这是他在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任上,亲自批准的最后一笔课题费!
说起顾廷龙先生,林先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顾老是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林其锬认识顾老是在1982年夏天。那时,为了校理《刘子》,搜集《刘子》资料,他有两个月时间,天天“泡”在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阅览室,中午两只包子、一杯咖啡果腹。
他的执着和勤奋深深地感动了“上图”的工作人员。一天中午,林先生去外面买点心,恰巧,顾老来到阅览室,问起阅览室读者情况。一位馆员向他汇报,说上海社会科学院有一位先生每天都来看《刘子》的资料,中午也不回家,每天早入晚出,现在去买点心了。
林先生的稿本、笔记、文具,放在办公桌上。这位馆员告诉顾老说这是他的东西。顾老顺便翻开林先生的稿本和笔记,仔细一读,不禁眼睛一亮,心中窃喜,便对这位馆员说:“看来这位先生在《刘子》校勘方面是花了许多功夫的,我们要支持他。
把我们馆藏的宋本《刘子》取出来给他看看吧。”林先生回来,这位馆员抱着牛皮纸夹有防蛀药的一包旧书,笑嘻嘻地告知他顾老来过,并将顾老的原话告诉他。
林先生又惊又喜,不知所措。他瞪大眼睛一看,是宋刻十卷本《刘子新论》。这部由著名藏书家孙星衍、黄丕烈跋的《刘子新论》是林先生朝思暮想的。面对这部国宝级的古籍。林先生一下子呆住了,喜不自禁。
因为他查过许多古籍目录学图书,知道曾经有这样一部《刘子新论》,但这部书已被收藏家傅增湘宣布“今已不传”。所以,当原以为不存世的《刘子新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怎么不惊呆呢?他告诉我:“当时我又惊又喜,对刺鼻的防虫药味全然不感觉,就像一个饿汉突然见到一盘又白又香的热馒头,恨不得把这部十卷本的《刘子新论》一下子全部吞进肚子。
”以后,他花了两个多星期,把《刘子新论》与其他版本进行了仔细对校,并记录了它们之间差异的细节。顾老慷慨借阅宋版《刘子新论》,开辟了林先生研究《刘子》的新天地。
从此,林先生与顾老结成“忘年交”,他经常去拜访顾老,向顾老请教版本。在顾老的指导下,他弄清了“影宋钞本”等版本问题。不仅如此,顾老还主动为他提供托人从日本影印来的(日本)宝历八年(1758年)刊的《刘子全书》五册,并亲手交到林先生手里,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搞《刘子》的,还是给你研究吧。”现在《刘子全书》五册已影印在《刘子集校合编》中。
顾老始终关注林先生的工作,他欣然为《刘子集校》书名题签。不久,林先生又在上海书店出版《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顾老初阅这部书稿,大为赞赏,特地为该书写序,序云:“其锬凤金努力于古籍整理之业,孜孜不倦,每承枉顾,颇闻校读所得,益我多多。今敦煌本刘子辑录成书,行将出版,忘其耄荒而乐为之序。”他还以充分的证据肯定林先生认为《刘子》作者即刘勰的观点。顾老的这篇序近千字,是用毛笔书写的,端庄凝重,是一份难得的书法艺术品,现在已经影印在这部“集录”的前面。林先生说:这样做“一补《刘子》版本之佚缺,二报顾老长期关注我们研究之恩”。是的,没有学术前辈的关心和指点,他是不可能实现研究《文心雕龙》和《刘子》的美梦的。他们的大恩大德,林其锬夫妇和学界同仁是永志不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