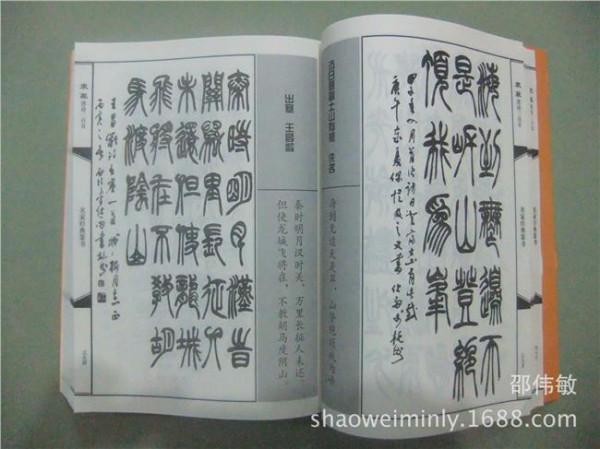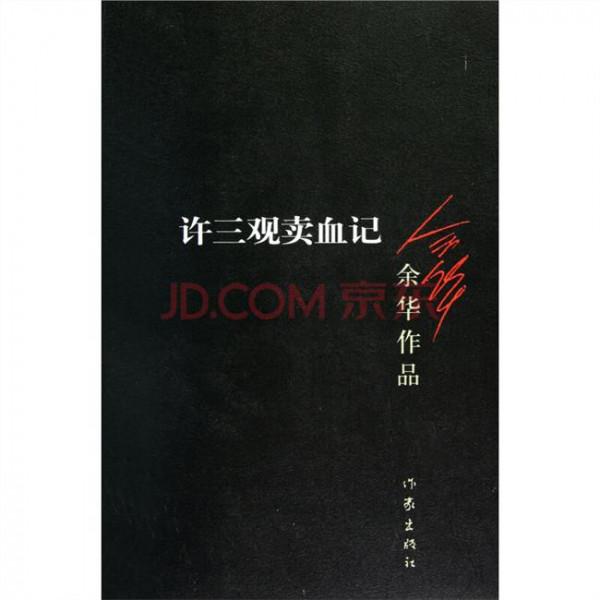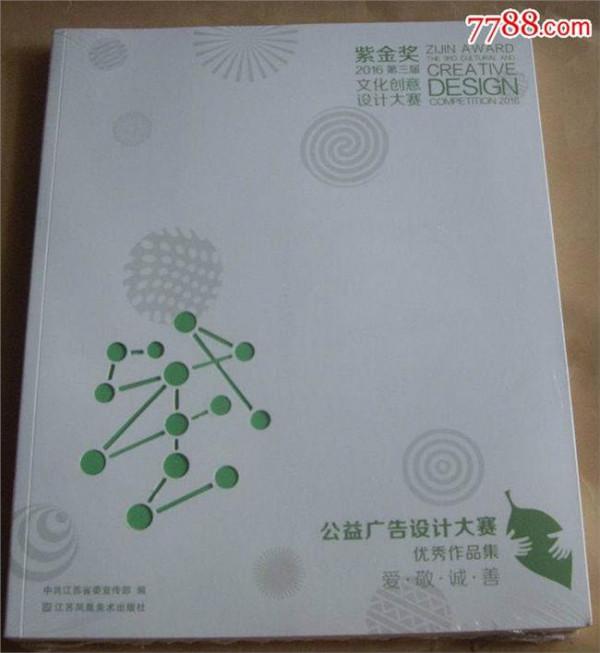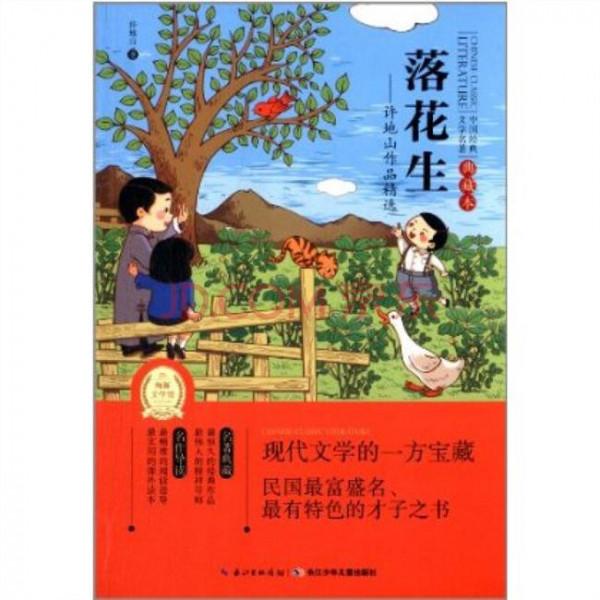许渊冲作品 许渊冲翻译作品的“三美理论”
许渊冲先生不喜欢逐字翻译,他不仅止步于“真”,而是要追求“美”。在这一点上,他和很多人有冲突,包括钱锺书。钱先生是许先生的老师,许先生认为他“学问之博,无所不知”,“但话又说回来,学博,但是他就缺我那一点。
”缺哪一点呢?正是“他太重真,不重美。他认为要忠实,要真。他认为真和美平等,甚至真比美更重要。所以他宁可得罪美,不可得罪真。”而许先生认为诗必须是美的,对“美”的追求本身就是对“真”的忠实。他喜欢引用贝多芬的话:“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不可以打破的。”然后忿忿然地直拍大腿:“那些拿清规戒律来戒我的人啊,放屁我当他是!”
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许渊冲的三美理论。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中提出来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三美”论。原文为:“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北京大学的许渊冲先生把这个学说移植到翻译理论中,形成了他自己的译诗的“三美”论,即:第一,意美,译诗要和原诗保持同样的意义,以意动人;第二,音美,译诗要和原诗保持同样悦耳的韵律;第三,形美,译诗要和原诗保持同样的形式(长短、对仗)等。
当然,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所以许先生才得到了他的老师,学贯中西的泰斗钱钟书的赞扬:“你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
那么,这三个“美”在译诗中的重要性又是如何划分的呢?许先生又说:“由此可见,译文不必‘形似’,只要求在传达原诗的‘意美’时,尽可能再现原诗的‘音美’,也就够了。”
我们从中可以明确,在许先生的眼里,“意美”是第一位的,“音美”次之,“形美”第三。“三美”的有机结合,正实现了对传统的翻译标准“信、达、雅”等理论的具体化,为译诗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和后学者。
“三美”是传统翻译标准在实践中的具体化
作为传统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以及相关派生出来的异曲同工的理论一直以来为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奉为标尺和经典。怎么去理解“信”呢?笔者认为,要做到文学翻译的“信”,尤其是在格律和压韵方面具有非常有特色的中国古代诗词的“信”,不仅要把原诗词所表述的内容给准确地翻译出来,还要把中国古诗词所表达的难以言喻的美给表达出来。
我们不妨把传统诗词的文字比做骨架,而其中所传递的美比做血肉。骨架和血肉的完美结合,也就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才是一首诗词所传递给读者的审美愉悦的完整性。
脱开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诗词都将是孤立的,苍白的。英国汉学家戴维司(J.F.Davis1795—1890)认为:“为了真正欣赏中国诗歌和其他诗歌,韵文正是翻译它们的最好形式。
”与他同时的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935)也批评过某些翻译者歪曲了《诗经》的原貌,他强调他本人的翻译将会尽力贴近原文的字面,不增译,不意译。
无论这些说法是否能够在实践中能够得以体现,我们可以看出,对中国古诗词的审美的追求,一直被译者,有时还同时为作品的欣赏者所关注。一首诗词,应该在表意和审美两个方面被看做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只侧重其中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翻译,都不能被认为是信。
如果能够在翻译中完美地做到“信”的要求,那么“达”和“雅”就不难完成,因为“达”和“雅”都是为“信”服务的。它们之间相辅相成,成为一个统一体。许先生提出的翻译的“三美”,即“意美”、“音美”和“形美”正是在“信、达、雅”等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个传统翻译标准的具体化。
许先生说:“解决理论的问题,最好是通过实践。”我们就按照他本人的话,来看看他在古诗的翻译实践中是如何做到“三美”的有机结合的。
我们先看王维诗《鸟鸣涧》的翻译:
原文: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译文:I hear osmanthus blooms fall unenjoyed;
Unenjoyed,无人欣赏的,副词。正是这个字,极其准确的道出了“人闲”的境界,连落花尚且不顾,不正是闲适吗?然后用hear一词,道出了幽谷之静。落花可听,谷中其静可知。虽然原文中并无“听”字,译文看似“不信”,实则为“大信”,试想,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翻译更能忠实于王维写诗时的心境呢?第二句的dissolve更是绝妙,dissolve into the void,融入空旷之中,那山色岂不正是有无中?人称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恐怕英国的读者未必了了,而许先生的此句一出,异域的读者们恐怕要惊叹得见庐山真面目了!
译文以aa,bb压韵,格律严整,在形式上极具英国古诗的风采。
通过以上许先生对这首中国古诗的翻译,我们不难看出,在他的翻译实践当中,许先生已经把传统的“信、达、雅”具体化为他的“三美”论了。从“意、音、形”三个方面去把握诗歌翻译,比“信、达、雅”的传统理论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直观性,在我国目前翻译理论丛生的环境中,“三美”论实则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方法论。
“三美”论是我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在扬弃中的继承和发展
在许先生诸多的文章中,尽管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的观点和看法,但是,他从来都没有使用过“翻译的革命”之类的句子。在他的著述中,他多次引用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直译”和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等等。
在有人认为他提出的“优势竞赛论”是要战胜出发语文化,从而进行批评时,许渊冲说:“至于文化交流的宗旨,到底是为交流而交流,还是为了双方都能得到提高呢?我认为应该是提高。”竞赛的目的并不是要“战胜出发语的文化”。
可见,他本人并无意于打倒什么,重建什么。我们可以认为,“三美”论正是在他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扬弃而来的继承和发展。在谈到严复的“信、达、雅”时,许先生说:“根据我自己的翻译实践,我认为严复的‘信、达、雅’到了今天,可以解释为‘忠实于原文的内容,通顺的译文形式,发挥译语的优势’。
”在谈到鲁迅的“直译”时,许先生说:“我把‘直译’理解成忠实原文内容放到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第三位……”他又说,当后两者没有矛盾的时候,“直译”就是“意译”,当两者有矛盾的时候,“就可以有程度不同的直译和意译”。
其实,在读过诸多许先生的译作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先生的翻译思想中,并无一定的法则,不去计较学术的派别,他的目标只在于使译文更“美”,让更多的读者“乐”。
综上所述,许渊冲的“三美”论是在他对前辈和同代的翻译家的理论和作品的研习中得到启发,在自己多年丰富的翻译实践中得到完善的翻译理论。“三美”论将此前的诸多翻译理论具体化,成为一个在翻译实践中可操作的标准。
对“意、音、形”三美的严格要求和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让我们看到这个理论和历史上与当今存在的众多翻译理论是并行不悖的,其主旨完全在于求“信”而致“达、雅”,以“音、形”相似而求“神似”,以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而入“化境”。“三美”论绝不是横空出世的“革命”,它是对我国传统翻译思想在扬弃中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