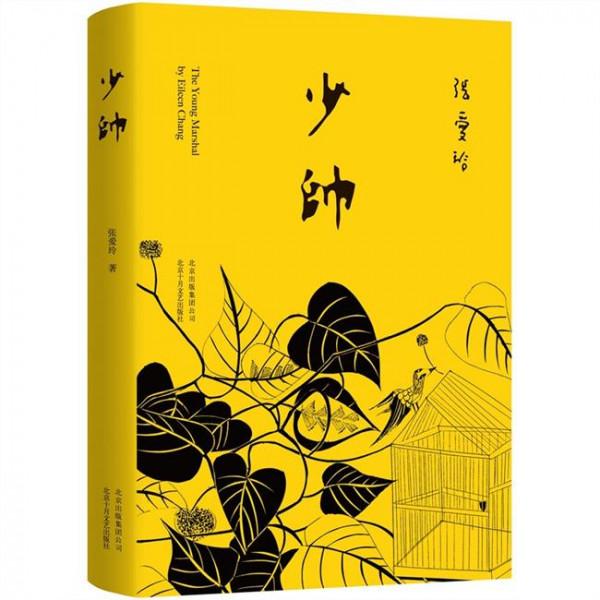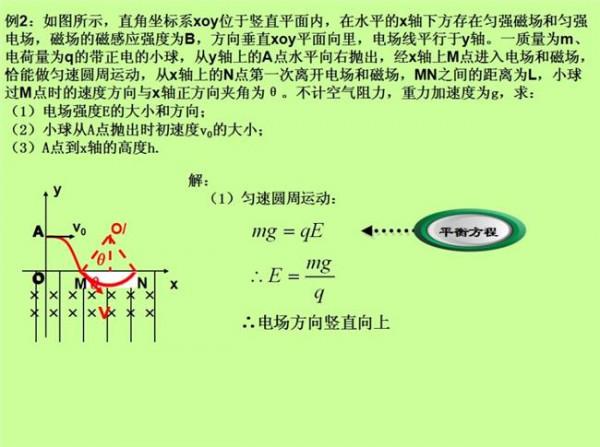余斌的张爱玲传 张爱玲传阅读附答案
虽然三年没碰中文,她肯定还是不能、也不甘把洋人设想成她的主要读者,何况她自小就钟情于小说,心心念念于那个更广大的想象空间。洋人要看而比较容易看懂的是介绍性的文字,小说对于他们显然是更费解的。所以就在“卖”洋文行情很不错的时候,她挟着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去叩上海文坛的门了。而且一旦在中国文坛上站稳了脚跟,张爱玲便与西文杂志挥手作别。
不知是因为以往投稿漫长的等待令她感到不耐,还是她学会了一点人情世故,抑或她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总之这一次怀着对成名急切渴望的张爱玲没有将作品投进邮筒,听任它到编辑大人的案上去碰运气。她宁可去“面试”。经母亲这一系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她带着稿子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周瘦鹃笔名紫罗兰庵主人,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作家)。
此次相会,二人谈得甚是融洽。张爱玲待人接物时给人“夹生”之感,但她在长辈面前似乎要松弛一些。她尝自言一向对年纪大的人感到亲切,对年岁相当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这一回她在周瘦鹃面前虽是执礼甚恭,却也还自如。让张爱玲高兴的却是这位主编对她奉上的小说十分欣赏。还未读正文,光看了篇名《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周瘦鹃便称名字起得好,大约他闻到了传统小说的气息。
周瘦鹃的直觉没有错,将两篇小说一气读完,他更可以相信这一点。它们与强调严肃性、思想性,鄙薄娱乐性的新文学大异其趣,从取材同可读性看似乎倒是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不无相通之处。难得的是周瘦鹃于坚守旧式趣味之外还是个鉴赏力较高的人,他通洋文,翻译过西洋小说,是旧丈人圈子中为数不多的对西方文学有所了解的人之一,他不仅看出张的小说有《红楼梦》的影子,而且看出张在写作中受到毛姆的影响,且断言它们可与毛姆的小说媲美。
周瘦鹃很快拍板:两篇小说都用。
虽然张爱玲的“二炉香”并没有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是文艺圈内却有不少有心人由此注意到这位后起之秀,<><>
几乎与《心经》发表的同时,张爱玲的另一篇小说《茉莉香片》在《杂志》上登了出来。
在此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使张爱玲青云直上,风靡上海滩的诸家刊物中,不惜血本、出力最多的,首推《杂志》。对《杂志》助她成名,她投桃报李,把最得意的小说都绘了《杂志》。
在小说赢来满堂彩之后,张爱玲又开始亮出她的另一样拿手戏一一散文,并且立即打响。
她将《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更衣记》,投给当时名噪一时的散文半月刊杂志《古今》,很快在8月、9月登了出来。
《古今》可说是男人的天下,张爱玲很可能察觉该杂志的种种气味与自己的性情不相投,而且纵能跻身其间,它亦不能让自己昂首鹤立,独上青云。所以两篇文章之后,《古今》再不见张爱玲的名字,她转向了苏青办的散文小说月刊《天地》。
由此我们约略可以看出张爱玲对刊物杂志取舍的标准了:档次高,实力强之外,还要加上志趣相投,肯于让她在上面唱大轴戏,虽非同仁杂志于她却有同仁杂志的意味。《杂志》《天地》遂成为与她关系最密切的两家刊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里,文坛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是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新人,而且均不吝于褒奖。
我们大致可以说,《紫罗兰》代表了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古今》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万象》坚持着新文学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新文艺腔”大张挞伐的《杂志》则想走纯文艺的路线,而它们竞一致对张爱玲表示推许。在新文学史上,这样的情形即使不是仅见,也肯定是少见的。
(摘编自余斌《张爱玲传》)
相关链接
①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一一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