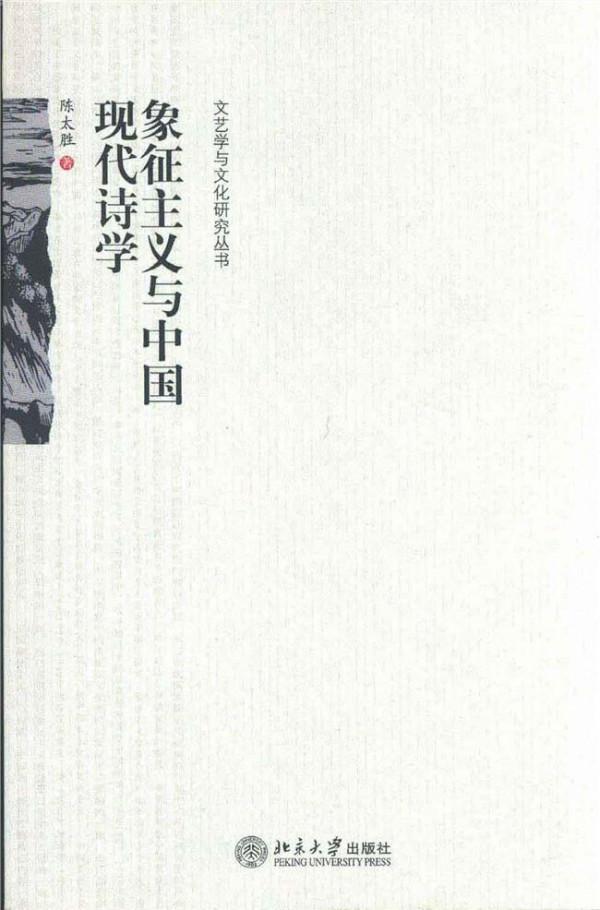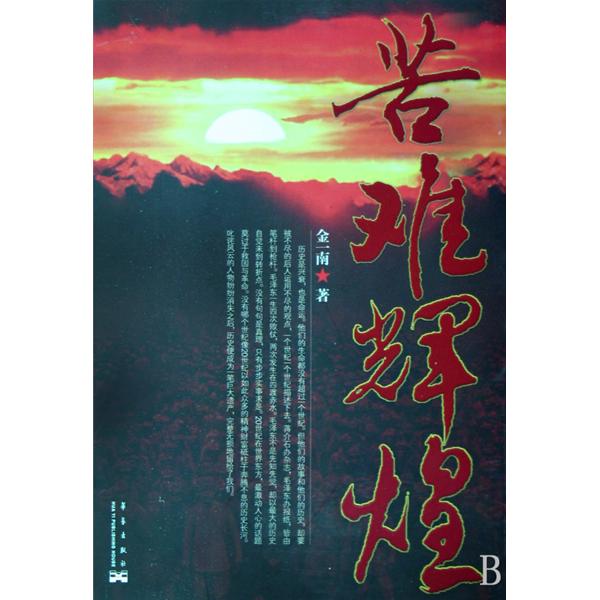李金发为学 李金发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
摘 要: 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意义,既表现在他所创造的色调奇异的诗歌文本上,又表现在他所倡导的诗歌理论上。他所提出的注重个人化的内心体验、把美作为诗歌创作的惟一目的、注重心灵世界的象征性传达、强调中西沟通等诗学主张,奠定了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基础。
关键词:李金发; 象征主义; 内心体验; 唯美主义; 新诗理论史 在20 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李金发首先是作为诗人而被书写的。显赫的诗名遮蔽了李金发作为诗歌理论家的一面。
李金发尽管没写下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却在诗集序跋、给诗友的书信、答问,以及若干篇文章中阐释了他的诗学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已是颇为新潮的理论了,不仅为解读他那些通常被认为晦涩难懂的诗作提供了钥匙,而且对于我们清理新诗史上时断时续绵延不绝的象征派诗学思潮,也有着很大的助益。
李金发是将象征主义诗学主张移植入中国的第一人。尽管“象征倾向”在早期白话诗人的作品中已经有所露头,比如在鲁迅的《野草》、郭沫若的《女神》,以及沈尹默、周作人、周无、田汉、宗白华等人的诗中,已能明显地感受到象征主义诗歌的味道,但是真正将象征主义诗歌引进到中国诗坛的是李金发。
还是在30 年代初,苏雪林就指出:“近代中国象征派的诗至李氏而始有,在新诗界中不能说他没有相当的贡献。
只这一点李氏的诗便值得我们讨论了。”[1]李金发是在法国留学期间开始写诗的。1923 年春天,他把已编完的诗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寄给不曾谋面的北大教授周作人,两个月后收到周作人的复信,称他的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
周作人还把这两部诗集编入新潮社丛书,后由北新书局出版。这两部诗集“在中国文坛引起一种微动,好事之徒多以‘不可解’讥之,但一般青年读了都‘甚感兴趣’,而发生效果,象征派诗从此也在中国风行了”。
[2] 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意义,既表现在他所创造的色调奇异的诗歌文本上,又表现在他的诗学思想上——他最先提出了中国古代诗歌所不具备、在他之前的中国新诗的前驱也未曾提出的新鲜的诗学主张。
本文不拟对李金发的诗歌文本做具体分析,而是想侧重谈一下李金发的诗学思想,看看他给我们的新诗理论界带来了哪些新的东西,希望能引起对李金发的诗学思想的重视,并进而对他在中国新诗理论史上的位置给予恰当的评估。
我认为李金发不仅是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移植者,同时也是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构建者。在李金发的诗学主张中,最有特色的主要有这样几项—— 一、注重个人化的内心体验 李金发留学时代,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正风起云涌。
当时的西方,城市经济急速膨胀,机械文明空前发达,人们日益陷入贫富差距拉大、生存竞争激烈,以及战争灾难的阴影之中。
曾经让人类以强烈的自信俯视寰宇的理性精神遭到了深刻的怀疑,诗人们在人性被扭曲的强烈痛感中,在找不到方向的绝望、恐慌与困惑中转向自己的内心,试图在幻想中,在最底层的潜意识中去追寻、重建人生的终极意义。西方现代派的基于个人写作的文学思潮,给正在新诗创作路上启步的李金发以重要影响。
从外部环境说,在法国的生活使他脱离了中国大革命正在酝酿和爆发的现实,听不见祖国人民在苦难中的呻吟,也听不见北伐军的呐喊与炮火;从内部因素说,基于个人写作的文学思潮,也正契合了他的创作个性。
李金发曾坦言过他对诗歌写作的态度: 我平日做诗,不曾存在寻求或表现真理的观念,只当它是一种抒情的推敲,字句的玩艺儿。[3] 我作诗的时候,从没有预备怕人难懂,只求发泄尽胸中的诗意就是。
……我绝对不能跟人家一样,以诗来写革命思想,来煽动罢工流血,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我不能希望人人能了解。[4] 这些话鲜明地表现了李金发当时的思想状态,以及他关于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向。
李金发的着眼点不在于外部世界的风风雨雨,而在于诗人的心灵世界,包括感觉的异常、情绪的变化、生命的体验乃至灵魂的困惑、心理的障碍等等。他认为任何人生的悲欢离合,极为人所忽略的人生断片,都可以成为创作的好材料,都可以暗示人生,但作为艺术,诗却不必以“真理”为追求的目标和责任,诗的价值并不因“时代意识”、“暗示光明”、“革命人生”等空洞的名词而决定,甚至可以“只当它是一种抒情的推敲、字句的玩艺儿”。
他把诗歌创作当作“个人灵感的纪录表”和“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应该说这是基于文学本位的对诗歌的很深刻的理解。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深刻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民族危机不容回避。
在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在诗人们大都积极呼应时代的召唤,投身到现实的火热斗争中去的时候,李金发的这种对诗歌个人化的表述就显得很是苍白无力了。
建国以后直到“文革”期间,诗歌更是被捆绑在“为政治服务”的机器上,李金发的主张就不仅是“不合时宜”,而且自然被扣上“资产阶级的颓废文艺观”的帽子而被打入冷宫了。只是到了新时期以后,随着文学上的拨乱反正,李金发的这些主张才有可能重见天日。
如果说新时期初期朦胧诗人更多地还是体现了一种集团意识,那么到新生代诗人以后,尤其进入90 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的势头愈加明显。诗人们冲破了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各自按自己的美学观和对诗的理解去静静地写自己的诗,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既与传统的主流文化不同,又与其他诗人相异的一种个人独特的话语世界,从而进一步促使诗向自己的本体复归。
当然,除去对80 年代的“群体写作”及其集体模仿行为的反拨外,个人化的写作也是对进入90 年代以后商品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机械复制的一种反抗。
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与人的交流变得越来越不易沟通。商品经济的大潮,社会围绕物质轴心的旋转,大众物质欲望的膨胀??给诗人带来强大的精神压力与生存压力。
作为社会的精英,诗人若想避免与流俗合流,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就必须在创作中强化自己的“个人”色彩,也就是说,透过诗人独具的话语方式与话语姿态,让诗人自身的形象兀立起来。
应该说,李金发在20 年代提出的个人化写作原则,到了90 年代才逐渐为诗人所理解和接受。李氏诗歌理论的超前意识可见一斑。 二、把美作为诗歌创作的惟一目的 李金发在法国留学的时代,也正是唯美主义盛行的时代。
包括象征派诗人在内的艺术家都坚信,美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艺术自身就是目的。他们不是把艺术看成传播、召唤和鼓动的工具,而是把它看成独立的形式结构,这种结构本身又是封闭的和完整的。
这样一来,重要的是艺术的内在形式结构,至于艺术创作的社会和道德目的就是无足轻重的了。王尔德在《英国的文艺复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
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往何方呢? ??这就是艺术的慰藉,是戈蒂耶的诗的主旨,是歌德所预示的现代生活的奥秘——我们的时代还能不要艺术的慰藉吗?”[5] (p. 100) 李金发对此深有共鸣。
他认为中国人生存现实环境是丑恶的,需要张扬美来与之抗衡:“从事艺术的人,非但不能身居此丑恶之环境,且必设法更正之,方算为人的生活,才好齿于文明民族之列。”[6]他提出:“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
艺术上唯一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所以他的美的世界,是创造在艺术上,不是建设在社会上。”[7]这些话表现出李金发的总的审美取向,那就是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以同丑恶的现实抗衡。
这样明确地表明自己是为了美而写诗,为了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升华而写诗,这在有长期的“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文学界,确实是一种新的呼唤。在李金发的时代,这呼唤显得微弱而无力,但是当历史进展到20世纪80年代,李金发的声音却有了异乎寻常的反响—— 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
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的童话,浅浅的脑海里就充满光辉。
[8] (p.115) 这是在李金发发出纯美的呼唤50年后,中国大陆诗坛传来的迟迟的回音。这声音不仅仅是一个诗人的,而是显示了崛起的一代青年诗人对诗的独立的审美性质的认同。
李金发是学美术的,他对于美有聪敏的发现。游览卢森堡美术院,在一尊石雕美女像前,他能在一簇发卷上,在白皙和丰满的前额上,在端正的鼻子和耳朵上,在盛开的花瓣般的弓形的鲜红嘴唇上,看出美来“,其时幼稚无邪的天真心灵,不知受了怎样的一种美丽的感动”[9] 。
不过由于中国与当时西方的特定社会环境,李金发不可能在诗中编织出纯美的伊甸园,而是从西方象征主义诗人那里感染了世纪末的病态心理,人生的孤寂、爱情的失落,以及死亡、虚无等成了他的作品中不断回荡的主旋律。
有人曾描述了李金发在法国留学时的思想与情绪:“他此时受了种种压迫,所以是厌世的,远人的,思想是颓废的,神奇的,以是鲍特莱的《恶之华》,他亦手不释卷,同情地歌咏起来,此时唯丑的人生——脱胎于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受其影响,是当然的。
”一次,一个刻大理石的教授来看他哪一个作品可以用到大理石上去“, 不料一开门,反吓得他连退几步,因为他的雕刻满是人类作呻吟或苦楚的状态,令人见之如入鬼魅之窟”。
[10]这表明颓废是李金发从美术创作到诗歌创作的基本色调。实际上在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及象征派大师波特莱尔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浓烈的颓废气息,这是用残酷的调子唱出的一种病态的美。
这种颓废与病态的美,在后来的战争年代与建设年代,都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的,因而就很少被人提及。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新生代诗人中,那种对崇高的消解,对人的琐屑生活与颓废心理的展示,以及种种化丑为美的笔法,都很易令人想起当年的李金发。
三、强调暗示,注重心灵世界的象征性传达 象征主义诗人不喜欢直抒胸臆,任内心激情奔涌而出,也不喜欢直接描写外部世界,展示现实生活的画面。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强调暗示,而暗示的手段主要是运用象征。
在这方面说得最明白的是马拉美,他指出:“与直接表现对象相反,我认为必须去暗示。……指出对象无异是把诗的乐趣四去其三。诗写出来原来就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想,这就是暗示,即梦幻。
这就是这种神秘性的完美的应用,象征就是由这种神秘性构成的:一点一点地把对象暗示出来,用以表现一种心灵状态。”[11] (pp. 262~263) 李金发对象征派的主张心领神会,他说:“诗之需要image (形象,象征) 犹人身之需要血液。
现实中,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美,美是蕴藏在想象中,象征中,抽象的推敲中,明乎此,则诗自然铿锵可诵,不致‘花呀月呀’了。”[12]这显示了李金发的艺术追求:讲究意象的象征性,也就是说重视心灵世界的整体象征性传达。
李金发给诗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诗是一种观感灵敏的将所感到的所想象用美丽或雄壮之字句将刹那间的意象抓住,使人人可传观的东西;它能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言而未言的事物。
[3] 诗的定义是一个人的诗歌观最浓缩的体现。李金发在自己给出的诗歌定义中,突出强调的是“刹那间的意象”,即主客观邂逅、灵感发生的瞬间从潜意识中升腾起来的意象,它是对生命的顿悟,又是全新的创造,所以才是“能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言而未言的事物”。
这种“刹那间的意象”很难用直白的语言加以描述,所以他的诗多用隐喻,往往通过象征性的意象来暗示诗人的情感世界,其表情方式较少直接的抒写而呈现某种曲折或间接的效果,诗的意境弥漫着一种神秘、朦胧的氛围。
而这正是李金发所着意营造的一个若明若暗的诗意葱茏的世界: 夜间的无尽之美,是在其能将万物仅显露一半,贝多芬及全德国人所歌咏之月夜,是在万物都变了原形,即最平淡之曲径,亦充满着诗意,所有看不清的万物之轮廓,恰造成一种柔弱之美,因为暗影是万物的服装。
月光的光辉,好像特用来把万物摇荡于透明的轻云中,这个轻云,就是诗人眼中所常有,他并从此去观察大自然,解散之,你便使其好梦逃遁,任之,则完成其神圣之梦及美也。
[13] 李金发之所以用这样充满诗意的语言描写“夜间的无尽之美”,是因为夜使万物只能局部的、朦胧的显现,月光给万物披上了美妙的轻纱,似梦而非梦,迷离而含蓄,这正是暗示所追求的效果。
在李金发看来,诗的意思不必合盘托出,它应有一点模糊,能引起人的深思与猜想,朦胧中有种神秘,这才是诗的最高境界。应该说,这些主张突出了暗示在诗人的艺术思维中的作用,也强化了读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是对新诗初期直白、浅露、缺少诗味的倾向的反叛,自有其拨乱反正的意义。
从中亦可看到,诗人对西方象征派诗人强调暗示的创作原则的认同。 李金发阐释的这一美学原则,除去在他稍后的象征主义诗人中有所共鸣和呼应外,长时间以来被漠视,被搁置一旁。
直到新时期,朦胧诗人崛起,在这些青年诗人创造的看来是全新的艺术境界中,我们却依稀看见了李金发上述描述的影子,可见他的诗学思想确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四、主张中西沟通 由于李金发是将象征主义诗歌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再加上他诗歌中的异国色调,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仿佛李金发是个主张全盘西化、数典忘祖的人物。还有人说他连中国话都说不好,对他的中国文化素养表示怀疑。
应当说,这是对李金发的诗学思想缺乏全面了解的结果。 1923 年5 月,在欧洲的李金发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百和,以为文学革命以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但从无人着实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
余于他们之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
[14] 就诗歌发展的途径而言,应当说,李金发这里提出的“中西沟通”的主张与设想,是极有道理的。新诗自发轫以来,相当一部分诗人视中国传统为敝屣,盲目崇洋,李金发还是在新诗出现的早期,就已敏锐地看出了这中间的问题。
他在《微雨》导言中指出:“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15]为了改变这种“无治”状态,他提出把中西诗歌“两家所有,试为沟通”的对策也是合理而有针对性的。
联系李金发的诗歌创作来看,李金发诗歌的外部形态与中国古典诗歌相去甚远,其欧化的句法,夹杂的外文,令习惯于中国古典诗美的读者望而生畏。但是若从内在精神来看,李金发的许多诗歌的意境、情绪却是非常中国化的,特别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常见的缠绵与愁怨,几乎是李金发大多诗作的情绪内核。
比如他这样抒写失去爱情的不幸:“我们折了灵魂的花,/ 所以痛哭在暗室里。/岭外的阳光不能晒干/ 我们的眼泪,惟把清晨的薄雾/ 吹散了呵,我真羞怯,夜鸠在那里唱,/ 把你的琴来我把全盘之不幸诉给他,/ 使他游行时到处宣布。
”(《不幸》) 这种缠绵悱恻的咏叹,不正是柳永、李清照等古代诗人最为擅长的一种表情方式吗?所以,那种认为李金发所开创的象征派诗歌只是对法国的象征主义做了简单的移植,而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无关的看法,明显是片面的。
不过,李金发的诗学主张尽管有合理的内涵,但是他的创作实践与他所主张的理论却有相当的脱节。
他最终并未能将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艺术和中国的诗歌传统加以融会,导致他的诗歌创作未能臻于完美境界。但在中国新诗史上谁又能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呢? 独特的个性,奇异的风貌,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引入中国,追求纯美和注重个人化情感体验,这一切都使他明显地区别于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同时也给中国诗歌注入了新的因子,仅从这点看,把李金发列为20 世纪中国诗歌史上最为重要的诗人之列,是并不为过的。
尽管李金发的诗学思想长期被忽略,然而,是金子总要发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掩埋不住的。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一代青年诗人的崛起,李金发诗学思想的在中国的超前意识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深入研究李金发的诗学思想并给予科学的评估,应是当代诗歌理论工作者一项重要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 苏雪林. 论李金发的诗[J ] . 现代,第三卷第三号. [ 2 ] 李金发. 仰天堂随笔·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A] .
异国情调[ Z] . 商务印书馆,1942. [ 3 ] 杜灵格,李金发. 诗问答[J ] . 文艺画报,第1 卷第3 期,1935年2 月15 日. [ 4 ] 李金发. 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J ] .
文艺大路,第2 卷第1 期,1935 年11 月29 日. [ 5 ] 王尔德. 英国的文艺复兴[A] . 外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丛书·唯美主义[M]1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6 ] 李金发. 少生活的美性之中国人[N] . 世界日报,副刊第六号,1926 - 07 - 06. [ 7 ] 华林(李金发) . 烈火[J ] . 美育,创刊号. [ 8 ] 顾城.
启开天国的门[A] . 顾城散文选集[ Z]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 [ 9 ] 李金发. 留法追忆[J ] . 西风月刊,1938 年9 月1 日. [10 ] 黄参岛1《微雨》及其作者[J ] .
美育,第2 期,1928 年12 月. [11 ] 马拉美. 关于文学的发展[A] . 西方文论选:下卷[ C]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2 ] 李金发. 序林英强的《凄凉之街》[J ] .
橄榄月刊,第35 期,1933 年8 月. [13 ] 李金发. 艺术之本原及其命运[J ] . 美育杂志,第3 期,1929 年10 月. [14 ] 李金发. 食客与凶年·自跋[ Z] . 北新书局,1927. [15 ] 李金发. 微雨[ Z] . 北新书局,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