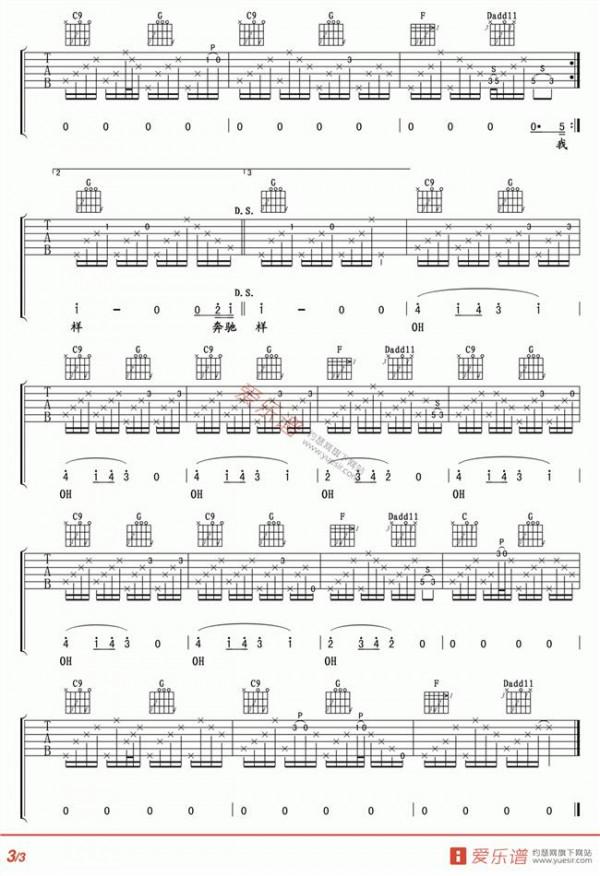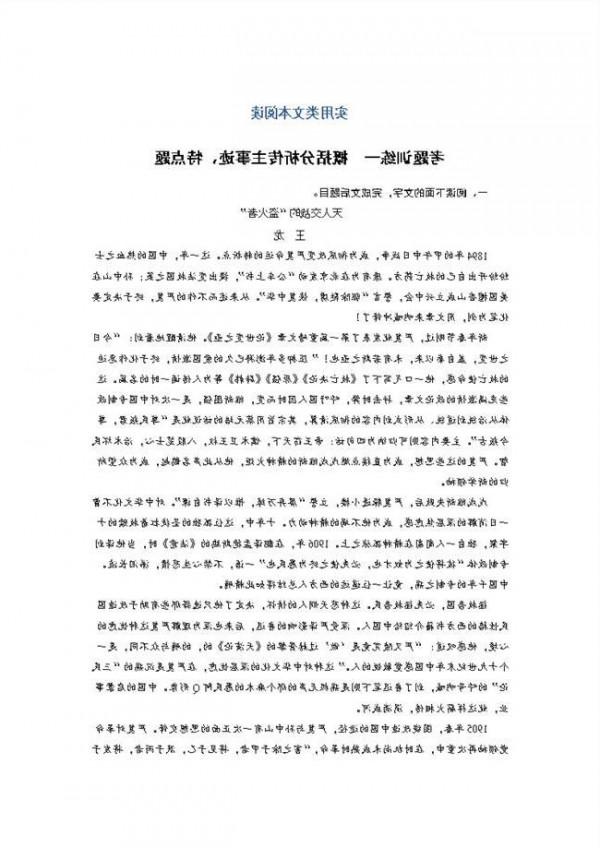阮义忠想念亚美尼亚 想念亚美尼亚 作者:阮义忠
亚美尼亚之行对我而言,仿佛是一种返乡;我现在想念它,也如同是想家。 每一次旅行都是一种离家与返乡的过程,每一次旅行都会让人对家有新的体认。 亚美尼亚之行对我而言,仿佛是一种返乡;我现在想念它,也如同是想家。
千里迢迢为音乐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姐姐的电话,父亲被检查出直肠癌,必须立即住院动手术。放下电话,我回想起与父亲之间的种种。我曾被他狠狠打过;初中逃家时,他从宜兰到台北找了我三天,问遍了火车站附近每一间职业介绍所,打探我的下落。
初二休学后,我跟着他当木匠,做了几个月的学徒。高一的整个暑假,我被他带到罗东的建筑工地打工,同住在工寮通铺…… 往事如影片倒带般地在眼前闪过,然后停格在我内湖山上新居落成,爸爸从头城老家来过夜。
隔天一早,他跟我借刮胡刀;我说我从来不用刮胡刀;爸爸无法置信: “哪有男人不用刮胡刀的?不是电动的也可以啊!”他那不信任,或是“你到底在搞什么”的表情,我再熟悉不过了;从小我就是被他那样看大的。
我老实告诉他,由于胡子稀疏,我一向都是用剪刀处理。爸爸摇头轻叹,无可奈何地摸着下巴:“今晚我到山下你弟弟那边去住。”之后,爸爸就再也没来我这里过夜。 想到这里,我觉得,一定要送爸爸一把最美最好的刮胡刀。
我立刻动身,在办公室附近的各个店家穿梭;行经一间唱片行时,一张CD的封面立即擒住了我。那是一座终年积雪的孤峰,山脚下只有一座小小的修道院,与世隔绝、孤立无援,仿佛就是我的心境。
到医院见过爸爸以后,我整个晚上辗转不能成眠,想起了白天买的那片CD 。清亮醇厚的歌声划破寂静的深夜,我整个人就像触电一样,仿佛被那分明陌生、却异常熟悉的旋律,重重地击在灵魂深处。 第一首是《上升的光》,接下来的一首又一首,有的让我几乎停止呼吸,有的让我无法抑止自己痛哭失声。
那时的我尚未皈依三宝,也从没向上帝祷告过,但在聆听 “艾契米亚钦”(Echmiadzin ,亚美尼亚位居首位的大教堂)时,却不由自主地合掌祈求老天:“让爸爸多活些日子吧!
” 最后的那首《上帝垂怜我们》没有任何伴奏,那精纯的女高音独唱,仿佛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生命独白。曲终时,尾音然而止,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死里逃生,从来不曾那样地感受到生命的可贵。
这些古老的赞美诗是在亚美尼亚境内录制的,为它们重新编曲的是饱受迫害、于1935年逝世的柯米塔兹(Komitas Vardapet)。被亚美尼亚人视为圣人与民族英雄的这位东正教教士,以其一生的努力,让亚美尼亚传统圣乐与民间音乐破土重生及流传。
是什么样的民族会创作出这样的旋律,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打定主意,要去亚美尼亚亲眼看看。但是,亚美尼亚在哪里?要怎么去?我查了查地图,方知这个国家与土耳其为邻。
1997年5月,我趁着去法国展览,到巴黎的亚美尼亚领事馆拿到签证,再前往伊斯坦布尔找《摄影家》杂志介绍过的土耳其摄影国宝阿勒·古拉(Ara Guler)帮忙。没想到,他正是已归化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父亲当年还是柯米塔兹唱诗班的一员。
多亏有他安排,我和太太才能在当时还没有旅行社、信用卡也行不通的国家,靠着当地的著名古迹摄影家波荷西扬(Poghos Poghosian)的向导,度过毕生难忘的一段时光。
飞越诺亚方舟停靠的山从伊斯坦布尔到亚美尼亚首府叶里温(Yerevan)的铁路早就因封锁而中断,一星期只有一班亚美尼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往返,乘客绝大部分是回去探亲的亚美尼亚后裔。
飞机是俄制的老型机种,唯一的空中小姐连推车都没有,餐点只能来来回回地从厨房一份份地拿到旅客手中;可以想见这个国家的经济困顿。空中小姐虽然亲切可爱,却让我不禁想到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的话:“幽怨悲凄、亘古伤感的眼神,是亚美尼亚人一望即知的特色。
在他们的眼底深处,闪烁着亚美尼亚人的失土 ─ 亚拉拉特山(Ararat)的阴影、无数次大屠杀受害者的幽灵,以及被迫流亡世界各地的子民的苦痛。
敝国人有谓,亚美尼亚人的眼中永远带着哀凄,即使他的脸上绽放着笑靥。”“看,亚拉拉特山!”一位乘客这么喊着。大家往右舷舱外看去,这座海拔 5165米的高峰,便是圣经上所记载的诺亚方舟于洪水退去后所停靠的位置,被亚美尼亚人视为圣山。
当那块土地于1920年割让给土耳其后,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就像是母亲被掳走了。飞机上的乘客,有的忙着照相,有的只是静静地凝视,或是擦着眼角的泪水。
机场空荡荡的,只有我们这班飞机的旅客进关;步出规模小到不能算机场的大门,波荷西扬和他的女儿安娜便迎了上来。他那部老旧不堪的苏俄制汽车,在塞了两大箱行李和四个人之后,底盘都快贴地了。然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就是靠着这部车行走过一条条千疮百孔的道路。
亚美尼亚有个传说,上帝在创造万物时,赐给每个地方的人们一个礼物,给着给着,竟然忘掉了亚美尼亚人。等到想起来,所有的礼物都送光了,只剩下石头。
这就是为什么亚美尼亚境内触目皆是岩石,而她的子民也总是称国土为“祖国的石头”,还自我解嘲:“我们真富有啊,石头多的不得了!” 正是靠着这些缤纷多彩的石头,亚美尼亚人完成了一座座庄严大度的建筑。在上世纪初,第一位探访古亚美尼亚首都阿尼(Ani)(如今已被土耳其占领)废墟的奥地利艺术史学家史卓果斯基(Strzgowski),宣称自己站在西方建筑史的一个伟大联结点上,认为只有建造圣索菲亚神殿和圣彼得大教堂的天才,才能真正了解亚美尼亚人在建筑上的先驱地位。
停留期间,我们一共造访了16所亚美尼亚著名的教堂,每一处都印证了史卓果斯基的见解。不只建筑,连葛里格圣歌(Gregorian Chant )的源头,都存在这个只有石头,而人民又受尽磨难的国度里。
让阳光照在墓地上 太太和我在亚美尼亚的第一餐,就是在波荷西扬家的晚膳。他已两季没有工作,手头应该是相当拮据的,可是,他的太太美拉妮亚依旧准备了满满一桌盛宴招待我们。
有好石头的地方,一定有好水。这个地方的矿泉水、啤酒与红酒品质之佳,与价格的低廉真是不成比例。 酒酣耳热之际, 当太太和我提到,在伊斯坦布尔必须于国内航线才找得到飞往亚美尼亚的航班时,竟勾起了波荷西扬一家不幸的回忆。
1915年,土耳其对亚美尼亚进行过一次几近种族灭种的大屠杀,据称死亡人士达两百万。最让亚美尼亚人不能释怀的是,土耳其到现在仍然否认这件事,因为不愿把所侵占的土地归还亚美尼亚。
在恐怖的亚美尼亚大地震之前,也就是1988年,土耳其又入侵了一些边界的乡村,杀害了近四万亚美尼亚人,却只承认了两万两千人。女主人美拉妮亚的双亲都是1915年的受难者。在这场举世罕见的人祸中,几乎每一户的亚美尼亚家庭都有人丧命或因此逃亡海外。
直到今天,亲人们还在互相找寻。安娜说,她的外祖父小时候亲眼看到爸爸是怎么死的。由于土耳其人专杀男孩,父母便给他穿上女孩的衣服,让他躲在地窖里,“外祖父与他的姊妹们也在那时失散,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下落”。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地放声痛哭,如同得悉自己亲人的不幸。虽然从史料上已经读过这场大灾难,但是亲耳听到的冲击还是令人受不了,直到客厅的录音机响起了鲁馨·萨卡扬(Lusine Zakarian)的歌声,才让我停止了哽咽。
这首我熟悉的旋律,编曲人也是柯米塔兹。安娜为我翻译了两句歌词: “让阳光照在坟墓上,引渡灵魂到天堂;让光线降落大地吧,因为它来自上帝。” “我们亚美尼亚人的生命力是很强韧的。
”这家人反倒安慰起我来,说他们一波波地被摧毁,又一波波地站起来。1988年12月7日的大地震,他们有五万多人丧生,五十多万人失去家园;全国的生产力降为零,邻国阿塞拜疆又趁机封锁了他们的对外交通。
“有几天温度降到了零下35摄氏度,每户人家每天只能点一根蜡烛;大家除了坐在黑暗当中,什么也不能做。可是,我们还是能彼此开玩笑,把所有的衣物都穿在身上睡觉,天亮时夸口自己起床穿衣的速度有多快!
那时,要为伤者动手术的刀都没有,医师们就用坚硬而锋利的石头片来代替。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亚美尼亚人就会好好地、有尊严地活下去。” 那夜回到旅馆已是隔天凌晨。我只觉得,不知道在哪一世,我很可能是亚美尼亚人。
因为才来一天,我就觉得来了好久好久,好像回到家一样。 绕着十字架打转的字母 极盛时的亚美尼亚领土,国界曾经大到从黑海到里海,现在却小到成了一个不靠海的内陆国家。古亚美尼亚曾被叙利亚、波斯征服,被亚历山大大帝征伐后,希腊也一度统治过此地。
约在公元前一世纪,提格兰一世(Tigranes I)才建立了强大的亚美尼亚帝国,并摒除波斯的影响,开始西化。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将波斯教排除,定基督教为国教,是世界上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
公元451年,亚美尼亚教会拒绝接受罗马教廷确认基督一身兼具神人二性的教义,坚持奉行基督一性论,成立亚美尼亚使徒教会,至今仍保持基督教的原始形态。 令人惊讶的是,全国没有一个文盲。
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亚美尼亚人,包括一位在田里拔草的老农妇,都能为我们介绍村里的教堂的起源和发展,侃侃而谈的风采,不亚于一位饱学的历史教授。亚美尼亚成人的识字率是百分之百,这个难得的成就,得归功于他们有一套了不起的文字系统。
早在公元396年,亚美尼亚的大学者梅斯罗普·马许托茨(Mesrop ashtots)就创造出了亚美尼亚的文字。这套文字是那么先进,以至于十七个世纪以来,它都一直存在,而且没有经过任何修改,就足以让现今的亚美尼亚人言语表达及文学创作。
亚美尼亚文的36个字母,笔画都非常简单,形状不是像“u”就是像“n”,或是半个“u”或半个“n”;要不然,就是“u”上多一撇或是“n”下加一拐。
据说,发明者是从观察十字架得到灵感,因为每个字母的笔画都是绕着十字架的四周打转而成。 我们特地到市区山丘上的马特纳达兰图书馆去参观。正门口就是一尊巨大的梅斯罗普·马许托茨石雕像,旁边用他所发明的文字刻了两句话:“欲求智能与学问者,唯通达理性格言矣。
” 被认为是亚美尼亚语言神殿的这座图书馆,收藏了大约1.3万件书写于羊皮纸和普通纸的亚美尼亚人手稿、10万件古代文物以及大批亚美尼亚人的小画像。
小学生经常被老师带着来这儿上课。看着他们好奇地用小手触摸十几个世纪以前留下的石刻字句,真是有如向祖先的心灵提问。 悲苦心灵的抚慰者 安娜告诉我,在亚美尼亚人的一生当中,至少要去一次的地方就是吉哈德(Geghard)修道院。
我所听到的第一首亚美尼亚圣歌《上升的光》,录制场所正是在此。我满怀盼望地随着波荷西扬一家前往;一路车辆稀少,离开首都之后,所见几乎都是马车、牛车、脚踏车或是徒步的行人。
路况之颠簸,令人担心轮胎随时会破;但沿途景色之美,实在是叫人心旷神怡。这里没大树,因此无所谓林相可言,有的尽是火山岩以及在起伏地形上的美丽草坡,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风景。“简单就是美”,这句话在平常听起来好像是意味着缺乏、单调,现在给人的体会却是一点不少的完整与纯粹。
吉哈德修道院是将一座石山挖空雕刻而成—亚美尼亚石匠的巧夺天工,在此处最能显现。我在神龛前屏息仰望这被凿掘而出的神秘空间,隔壁的祈祷室忽然传来我在台北家中经常播放的那首亚美尼亚圣咏。
那特殊的空间深度,以及在四周都是石头的环境里才能有的回音效果,都和家里所听到的一模一样。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人在播放那张CD吗? 我急急地循声而去,发现一位中年妇人泪流满面地在唱着这首歌。
她的嗓音美极了,最后一句的收尾也如同CD上的女歌手那样惊心动魄。她用先生递过来的手帕擦完脸,情绪平静之后,才告诉我们,她是出生在黎巴嫩的亚美尼亚人,这是第一次回来寻根。
她的父母于大屠杀时逃到国外,虽然在别人的土地上养儿育女,却把亚美尼亚的语言、文字和圣咏、民歌用心地教给了下一代。她今天能站在这里,把心中对祖国的思念借母语唱诵倾吐,真是悲喜交加。
这首名为《母亲,你在哪里》的歌,代表了多少海外亚美尼亚人的心声;而从坚石中挖出来的这间祈祷室,不正如同母亲的子宫! 这个国家的面积不过是29800平方公里,当时的人口才330万(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达700万),大大小小的教堂却有1000多座;与宗教有关的遗址也达4000多处。
波荷西扬带我们造访的教堂和古迹都极有特色。加尼村(Garni)当年是铜墙铁壁般的城堡,为古时亚美尼亚国王的夏宫,可惜的是,除了主建筑已被尽力修复,大部分古迹仍然呈现着被毁损的样貌。
村内的异教徒的寺庙,兴建日期可上溯到基督受难后不久,看起来就像小号的雅典卫城。 喀依扬(Gayane)修道院里的墓地是女歌手鲁馨·萨卡扬长眠之所,墓碑上刻着“亚美尼亚人的夜莺,1937年6月9日~1992年12月30日”。
她是亚美尼亚人悲苦心灵的抚慰者,出生于乔治亚共和国,从叶里温的柯米塔兹音乐学院毕业后,于1962年展开职业演唱生涯,足迹遍及欧洲、加拿大、美国、阿根廷、乌拉圭、中东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在她的灵前致敬时,安娜说:“我们在最绝望的时候,听听鲁馨的歌,就会觉得一切都可以熬过去。” 先进的古老文明 艾契米亚钦大教堂,我们当然也去了。
细心的波荷西扬特别挑礼拜天作弥撒时造访,好让我们听听唱诗班的优美歌声。这座全世界最古老的大教堂,从公元4世纪起即为亚美尼亚教会领袖驻锡之地,人称基督教的发祥地。那天,我不但听到了唱诗班,还拍到了来主持弥撒的大主教卡瑞金一世(Karekine I)。
艾契米亚钦大教堂旁有座刚落成不久、由美国一位亚裔富豪所捐建的博物馆,里面藏有亚美尼亚历代珍贵宗教艺术品。这里平时不对外开放,但波荷西扬曾受托拍摄这里的所有收藏品,因此特准他带着我们入内参观。
更难得的是,一个外人禁足的遗址也让我们进去了。当年建造艾契米亚钦大教堂时,无意中把一个兴建于公元3 世纪的拜火教圣坛作为地基,被湮没了1700年的圣地,直到十多年前进行艾契米亚钦大教堂整修时才被发现。
亚美尼亚的建筑、音乐和字母让我体会到,这个民族的祖先似乎特别了解时间的奥秘。他们盖的房子、唱的歌、用的文字,经过世世代代的流传,不但没有落伍,还在每个世纪都以新鲜的面貌打动着当代的人们。
以梅斯罗普·马许托茨为名的修道院,是这位先哲当初的驻锡所在。地下室入口的大石碑刻着他所创造的所有字母;大门正上方的一面大窗户也镶嵌着这36个字母所组成的彩色玻璃。在此,这个民族的字母就像是图腾一般,有着法力无边的震撼效果。
我们点了蜡烛也投了香油钱,默表对这位圣人的尊崇。若不是他发明了亚美尼亚文,亚美尼亚文学和音乐也无从流传后世,我也无缘来此亲炙这伟大的文明。 以伟人名字命名的修道院还有几所。
其中,以中古世纪的学者与作家,“戈夏凡克”命名的建筑,落成于13世纪,被认为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一。11世纪时,亚美尼亚被土耳其统治,一些僧侣遁隐至偏远的山谷或高崖上兴建修道院,在院内潜心著作,影响颇巨。
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虽与世隔绝四百年之久,却创造了亚美尼亚文明中最辉煌的“银色时期”。 塞凡湖(Sevan)边经常有人来写生。这座湖是前苏联境内最大、也是位置最高的,海拔1916米,面积1416平方公里。
湖边山头上的两座教堂,在水位下降之前是在湖水边,现在却高在山头上;可见湖水逐年干涸的情形有多严重。这也是亚美尼亚人非常担心的事,因为这个湖是全国唯一的水源。 我们坐在山头看台欣赏湖光水色;一群民众从山脚不远处的渡轮下到岸边,手拉着手围成一圈,齐声高唱圣咏。
这又是一首我听过的曲子,彼时伤感落泪,此刻却令我满心欢喜。 为什么亚美尼亚音乐有时听起来那么悲苦,有时又让人觉得无比甘甜?至悲与极乐,有时竟是那样的难以区隔。
这个体会,随着我在亚美尼亚停留的时日,越来越深刻。 终于来到了亚拉拉特山的山脚下。从我们驱车前来的角度看去,圣山就跟我那张CD的封面一模一样。圣霍尔维拉普(St.
Khorvirap)修道院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城墙下,几位流浪艺人组成了最简单的三人乐队:鼓手、黑管,和那令我神往不已的乐器 ─只有亚美尼亚才有的“杜杜卡”(duduk)。 杜杜卡看起来像笛子,声音却像萨克斯风那般宏亮,可以尖拔高亢,也可以浑厚低沉。
它是用杏木雕成,以两个簧片控制发音,是双簧管的前身;管身在正面有八孔,背面有一孔控制音阶。音色具有一种深邃而微妙的颤动感,被认为是最接近人类喉咙所发出来的声音。
杏树原产于中国,由丝路西传,变身为罗马人口中的“亚美尼亚树”。中国的种子在亚美尼亚开花结果,而其树身却化为人世间至为凄美哀怨的乐器。把我带进亚美尼亚的因缘,不也同样不可思议? 美拉妮亚带太太和我来到修道院城墙最突出的部位,眼角泛起了泪光:“我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最靠近圣山的位置。
前方的铁丝网是边界,眼前的一切看得到却摸不到。我们的母亲被土耳其人关起来了!” 玫瑰为什么要有刺让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经验,发生在波荷西扬的好友尤里·哈察都扬(Uri Khachatrian)家中。
一天傍晚,我们抵达“薄荷”村(Urzazor),穿过丛丛的果树林,来到一栋木屋前。尤里和他的母亲、儿子大卫塔就住在这里。
我们在亚美尼亚所看到的建筑,几乎都是石头做的。在这个树木稀少的国度里,木头可算是奢侈品。还没看到主人,已可料想到他是一位坚持品味的人。 一进门,尤里就冲着我们直笑,用极为精准的发音念出“苏东坡、李白、杜甫”这几个字。
若是闭着眼,还真会错以为遇到了中国同胞。原来,身为俄罗斯文学教授的尤里对中国文化十分心仪;藏书多且种类丰富,塞满了书房。 九岁的大卫塔漂亮清纯,简直就像是天使的化身。
虽然言语不通,他却能靠着比手划脚和在纸上画画与我们沟通。大人在讲话时,他就静静地在一旁看着;晶亮的眼神完全透露了他的聪慧。 陪客有两位:一位是壮壮的机械工程师阿玛西·米纳西扬(Amasir Minasian),一位是堤格兰·吉佛基扬(Tigran Gevorgian)。
和尤里一搭一唱的阿玛西非常风趣,由于总是他在讲话,以至于我们后来几乎想不出堤格兰是否开过口。 阿玛西和尤里这两位老友真是绝配。
前者天生有副好嗓子,开口就是歌,无奈记性不好,老是忘词;后者能背诵好几百首歌词,但是五音不全。整个晚上就是在尤里提词、阿玛西高歌的情形下,经常让大家笑得人仰马翻。阿玛西促狭,一忘词,就像唱片跳针那样不停地重复那半句歌,直到尤里从厨房或是厕所赶来提词,大家才能被解救。
有一首歌词,到现在依旧让我印象鲜明: “为什么找不着无刺的玫瑰? 这么久以来,我寻寻又觅觅, 每次接近玫瑰,总是被刺伤!” 大家畅饮伏特加,半醉的尤里兴起,放上录音带,把客人一个个拉进原木地板的客厅里跳舞。
亚美尼亚的舞曲高亢而欢畅,旋律就像哈察都量的“剑舞”那样令人惊心动魄。大家手挽着手转啊转啊转啊,把平时的矜持都转掉了。
有好几次,我们邀大卫塔一起共舞,这孩子却总是笑着轻轻摇头,清亮的大眼睛好像在说,他要当唯一的清醒者。 舞曲录音带放到最后,突然出现了半首没被洗掉的民谣。曲调幽怨,让所有人从狂舞之中醒过来,呆呆地愣在那边。
我和太太虽然听不懂歌词,也能判断是让这些亚美尼亚朋友不好受的。气氛大变,整个场景好像电影断片,不知何以为继。 大家回到餐桌上,沉默地聆听这首也是由柯米塔兹整理出来的歌。带子放完,录音机的按键“答”地一声跳起来,好像在我的心头狠狠地槌了一记。
我完全无法控制地失声痛泣;这已是短短几天内的第二次了,也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的经验。前一刻我还在狂笑,此时却泪流满面;这样的悲喜交集,到底要如何才能形容? 分手时已不知夜有多深。
车灯投射在漆黑的山间小径,显得格外微渺,好像随时都会被黑暗吞噬。美拉妮亚和安娜在悄声讲着我们听不懂的事,脸上带着忧伤。怎么啦?我们问道;得到的回答却让我们整个呆了:“你们看,尤里的儿子长得多好、多聪明啊,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孩!
可是医师说他得了一种罕见的、跟血液有关的怪病,活不了多久。” 我和太太心如刀割、泫然欲泣;美拉妮亚却只是淡淡地表示: “我们亚美尼亚人深知,悲伤和快乐,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父亲于1997年的11月28日过世,那是我从亚美尼亚回来半年后的事。这段时间是我这辈子和爸爸最亲近的时光。老天爷一定听到了我的祈祷。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