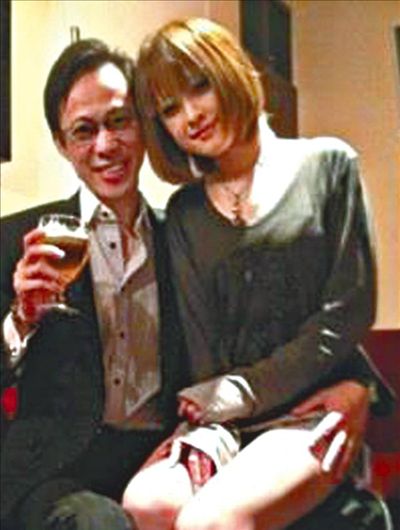【李小牧的老婆】 李小牧:在日本当皮条客的生活(图)
李小牧自费去日本留学,是东京服装学院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生。 2002年,李小牧的自传《歌舞伎町案内人》在日本出版发行后,迅速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参加了凤凰卫视的《歌舞伎町的皮条客》。
那么做案内人呢?“我做案内人,是为了生存。那些在东京陪酒卖春的中国女孩,也是为了生存。我站在新宿街头发纸巾,工作一小时是1000日元,而做案内人五分钟就能赚到3000日元,我当然要选择赚钱更多的职业。
刚做那会儿,我也痛苦过,思想上也激烈斗争过,我在国内跳过舞,当过演员,做过贸易,在日本一流的时装学校学习设计,现在却要站在大街上拉皮条,我要不要面子啊?”李小牧用力夸张地拍着脸颊。
最令他难受的是,有一次他和爱梅吵架,爱梅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没错,我是有个日本男人,那又怎么样?你这个丢留学生脸的拉皮条的,就凭你的本事,在这异国他乡能让我过上好日子?”那天,李小牧全身发抖地倚在角落里,强忍着声音,不断抽泣着……
“听说你在日本做案内人一直瞒着你父亲?”
“我告诉他,我在日本做导游。我无法想象在电话里能让他明白,歌舞伎町案内人都做些什么。我们在中国见最后一面时,他才知道我的工作。他看到我做这行,过得还不错,并没有说我什么。”
李小牧回到日本后不久,父亲就过世了。接到噩耗的那天,他站在新宿街头,跟一个陌生的日本人用中国话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父亲死了。”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说,看着他眼泪珠子一个劲地往下落。可是,仅仅过了五分钟,他就发现前面来了一拨台湾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脸,迎上前去问:“先生,你们要服务么?”
李小牧在房内演示着那一幕,低头哈腰,一脸讪笑。
“哭有什么用呢?没人会因为你父亲死了,就会多给你小费。活着的人照样要活下去。没有钱,拿什么养家?你拿什么交学费?那一刻,我对我自己说,今天我赚到了钱,我就是在赢。”
李小牧继续笑着,笑得极其异常。
“我想赢得一种承认”
“你到底想赢什么?”
“我很想赢得一种承认。我像一个悲剧,案内人让我在日本赚钱谋生,也是我创作的源泉,但它也成为永远贴在我身上的标志。
“我曾经恨过我父亲。如果没有他,我们全家人不会过着被人看不起的日子。我从8岁起就拼命跳舞,我只有利用这点特长来为母亲争光。可惜,条件、环境、资质都注定我当不了一个成功的舞蹈家。我没有读过书,可是为了办好文学院,我做得那么努力,结果学校被封了,我们被大众唾骂成骗子,全家人再次被人看不起。
“我父亲年轻时,极想通过实现自己的价值,来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儿女的命运,可是他一再失败,也让我在生活中处处碰壁。我从湘潭跑回长沙,从长沙跑到深圳,没有一个城市让我感到满足,感到安心。最后,我来到了日本学服装设计。
“我没有资格指责爱梅不忠,她来到日本后,也是为了生存,去了新宿相亲俱乐部作诱饵陪客,认识了别的男人。同时,我也认识了一个日本情人,就是书中所说的苇子。
“我刚开始站在大街上拉皮条时,我在服装学院的同学常常经过那里。我害怕他们知道我做这行,我总是装作在发广告纸巾,或者是等人。久而久之,他们发现我老在那条街上,我穿着变得好了,手里宽绰了,他们以为我是在那儿做“鸭”,在学校里,我又被人家看不起。
“现在想想,他们讲的也没错啊,我满足了苇子的欲望,她送给了我喜欢的东西。这种形式,在苇子心里,我不正是一只中国“鸭”吗?
“新宿这条街别说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在日本人眼里也是有名的3K街,又脏又乱又可怕。可偏偏在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地方,让我这样一个年纪大,又不懂语言的外国人找到了生存的位置。我的地盘位于歌舞伎町正中心,包括剧院广场在内的两条街。这是歌舞伎町的主街道,就像一块人人争抢的肥肉。
为了保住这块地,我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与黑白两道搞好关系.在这条街上,我和黑人,日本人,韩国人,甚至是自己的同胞钩心斗角,你争我夺。
“你看,我在日本付了那么高的学费,进那么好的服装学院学习,好不容易毕了业,我却成了一个拉皮条的。
“我结了五次婚,中间也没断过女人。我一直想寻找像我妈妈一样的女人。一个不仅能体贴我,关怀我,能为我生小孩,还能明白我心里想做什么的女人。
“无论是爱梅,还是我以前的日本太太久美子,以及与我一起在这条街上打拼过的莉莉,她们最终都不能理解我,所以,尽管有钱了,我还是感到压抑,我沉迷于赌博长达八年,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说过我没有中国朋友,我就没有遇到值得我信任的中国人。不是吗?我在书中,写过的那个中国人,我以前的部下金东,不就是一个小人吗?
“他刚开始跟着我时,穷得像鬼一样。我吸收他入伙,培训他上道,增加他的分成利润。他孩子病了,我半夜开车接送。结果呢?他被我开除后,立马来报复我,想瓜分我在这条街上的利润,还找人来绑架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国外整我的,偏偏还是我的同胞?你说我最恨金东,一点没错。他就像过去在国内所有伤害过我的人的浓缩版。
“我学成以后,可以回到国内,重新创业,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但我已经回不去了,我在新宿歌舞伎町投入太多心血,我爱上了这条街。
“在这条街上,我看到了很多发生在社会底层的故事,可以找到很多我年轻时的影子,它们都装在我的大脑里,成了我写书的丰富题材。同时,我也在想从他们身上探索,我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现在我出书了,也自己办过报,还被各大媒体采访。我父亲没有实现过的理想,我都一一实现了。
“可是,在日本人眼里,我是明星,也是怪物。
“在中国人眼里,我无论多么张扬,他们永远都会认为,我是新宿歌舞伎町的一个案内人。”
在谈话结束时,李小牧将自己比喻成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
“自封的吧?”
“呵呵,是自封的。”他狠狠地将手中没抽完的香烟摁在烟缸里,他没有发现,那一支支长短不一的残烟插在里面,还真像一朵白莲。
只是花瓣是烟蒂,底座更是一只脆弱的玻璃缸。
“你好!是从台湾来的吗?”
“你是从香港来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况没有我不知道的,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就是像这样从侧面主动搭腔。我保持笑容,问话方式尽量自然。
没有想到,“客人”听到问话,大都会停下脚步。几乎所有的人都因为终于能来到这亚洲第一闻名的红灯区看看而暗自庆幸。但去哪儿?看些什么?哪些店有意思?他们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礼地用中国话问他们,既像绅士又看上去亲切而值得信赖,于是,他们大都表现出在异国他乡突遇同胞那样听我给他们一一做介绍。
等到他们发现我不像是坏人,不会带来危险时,他们立刻就变得非常主动,不住地提出问题。到了这一步,我的买卖就基本成功了。
在日本学到的获得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向别人低头。按中国人的个性是很难这样做的。
以我在歌舞伎町多年摸索出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如果不保持低调,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只要稍稍低低头,对方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即使是那些平时看不起中国人的家伙,只要对他多鞠几个躬,多笑眯眯地问候几声,他们就会很快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我觉得,要想在日本生存,就要实际一点,首先把面子丢在一边。
我从不做欺骗同胞赚钱的事。我所选择的,都是一些公认的“优良店”。我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优良店”的信息,待我确信真是“优良店”时,才会正式签约。这和大多数“拉客”商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当中,很多都是采取着里应外合、共同骗取客人钱财的勾当。我曾对自己发过誓,绝对不做昧良心赚钱的事。
一天,认识的一个中国按摩师也站在我常站的位置拉起客来。那会儿我的独占意识已经非常强烈,本能地就想把对方置于死地。原本我喜欢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不管发生什么都不想与警察和黑社会有染。
但是,当时自己的力量还没有那么强大,同时还想看看会长到底会不会帮忙。讲信用的会长马上亲自带了几个手下帮了我。
“喂!小子!不赶快给我滚出这里,那可就不是断几根骨头就能了事的!”
平时温和的会长这会却一反常态,发出了如此的恐吓。那个人瞬间就屈服了。此后,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露过面。
在歌舞伎町时间呆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与此相对,这条街上还生存着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刑警。
在这条街上,没有黑社会做后盾无法生存。但同样,不和这些刑警打交道也同样没有出路。如果说有黑社会撑腰,可以保持在这条街上生存的最低条件的话,那么,有这些警察朋友,就等于有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杀手锏”。
可是,与这些人交往必须掌握好分寸。和他们太近了不行,会引起黑社会和周围的反感与怀疑。太疏远了也不行,那也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的。我这个外国人更是要小心,不然可能会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