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的妻子 陈思和: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有关陈寅恪先生的传记里,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不是最好的一种,却是最受人注意的一种。为什么这样说?第一,这本传记绕开了对陈寅恪先生晚年著述的学术价值估评,着重渲染其感怀寄托的弦外之音,这虽不能显现寅恪先生独立群山之巅的存在价值,但对现社会一般知识分子而言,极需从被称为“学人魂”的寅恪先生身上所获的,不是其学术本相而是其为学之魂,若真要详释寅恪先生学术真谛,恐非陆氏这本传记所能承担,亦非这本书的读者所真正需求,所以正逢其好;第二,这本传记与其说是成熟的史传著作,毋宁说是一部文情并茂的文学传记,书中不少文句夸饰而煽情,平平常常的事情一经文学笔法写出,就成了一部英雄传奇,使人想起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但对屡经挫折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彼此间相看两厌的,不过是折了翅、拔了毛的落水鸡而已,非是一只腾空飞出、遍体生辉的火之凤凰不足以振其聋而发其聩,所以,这本传记少了些含蓄朴质,多了些伤感矫饰,也正逢其时。
上述两点,虽可说是这本传记“不是最好”的证据,同时也似乎说明其受到读者欢迎的社会心理,这是当前读书界浮躁之气未除的表现,也恰好说明了当前中国大陆精神领域所想要什么和所缺少什么的区差。
一般来说,稼轩《采桑子》词说明两种写作和读书的境界,“少年不识愁滋味”是一层境界,为文学的境界,热烈伤感浓之,含蓄朴质缺之;“却道天凉好个秋”又是一层境界,那是历史的境界,深刻通达有之,生命热血淡之。
这本传记为文学传记,属第一层境界,而所传传主却是史学大师寅恪先生,恰是以少年之春风春情写生命的晚熟金秋,我们仅见一秋风秋雨、红妆素裹的寅恪先生,未见一老树枯涩、独立天地间元气浑成的寅恪先生。但以寅恪先生之大,后人实难传其精魂之万一,能有文学的寅恪先生再现于世,作为当前精神领域之偶像足矣。
或幸陆氏有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之心,才会睁大了惊异的眼睛去了解专制时代某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书中大量引用的未刊档案,尤其是寅恪先生服务单位中山大学年复一年暗中搜集、汇报的“陈寅恪材料”“陈寅恪近况”之类的动态报告,在当年都是作为内部分析知识分子动向的依据,以供权力者掌握“敌情”之用。
这种今人看来毛骨悚然的鬼魅行径,当年何止用于寅恪先生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据贾植芳先生著回忆录《狱里狱外》所载,先生于1955年因胡风一案入狱,在监狱里已闻有人搜集田汉、阳翰笙等人的历史问题,而田阳诸公此时还负着大陆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之职,正在举手挥拳声讨“胡风分子”。
对革命一生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绝情,遑论统战对象。这类视知识者为敌人的鬼魅行径,其实也不必发指,在中外专制国家里一向是很平常的事情,即便在号称民主的国家里也难绝迹。
记得有报载著名画家毕加索的档案披露,连他也曾在美利坚的中央情报局监控之下度过了几十年的春秋。但这本传记以秘籍档案入传,毕竟开了当代人物传记的一个新领域,使人公然获知,长达几十年的历史竟有阴阳两界之分,仅以公开披露的材料、文字等立传,不过是人物的阳界一面,而被鬼魅们操纵的阴界隐伏在昏暗中不见天日,“阳界”的许多现象终究得不到真实的逻辑的解释。
以寅恪先生为例,假若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许这些鬼魅行径终究是鬼魅行径,于寅恪先生也终究无损,先生寿终正寝之日,仍会像朱师辙那样,沐浴在一片光辉之下,知识分子几近宿命的悲剧因未能昭然幕启而呈现另外一种演出形式,??但或许是更深刻的形式。
现在似乎很难推究,当年寅恪先生决定留居岭南的真实心理。
这本传记从传主生命旅程的最后二十年写起,开卷即劈面遭遇寅恪先生去留大难之疑,海内外学界,庙堂草间,对此均有辩论,可是传记只用了“有着很深的原因”一句含混过去,这是过于轻巧之弊的一证。
作者用文学笔法渲染了陈序经等外部种种因素,却很少深入到寅恪先生的心理深处去寻求原因。寅恪先生是一个极其顽强而独特的生命个体,其在对自己后半生去留大事的选择与决定上,不会与张伯苓相同,也不会与吴宓相同,甚至连爱妻的出走都不会动摇。
倒是与寅恪先生为人很不相同的冯友兰先生,说出了一段很中肯的解说:“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之两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一者何?仁也。
”斯言者诚,以传统文化顾命人自居的两大学者,在风云突变的岁月里,一个选择自沉以殉文化,一个选择“突走”后的豹隐岭南,以生的方法来完成另一种形式的“自沉”。冯友兰先生识其“突走”却未识其留居之意义,也就是其与传统文化共存亡之心态,这就不是一般的叔齐伯夷不忍之心所能涵盖,也不是那些认定此举乃寅恪先生错着之棋的海外学者辈所能理解。
寅恪先生不会轻易走出国门,也就是他要用他的睿智与胆识,实践出一条现代知识分子终将会走通的,远离庙堂,续命河汾之路。
什么叫“续命河汾”之路,其典出自隋代大儒王通隐居河汾讲学,守先待后,使传统文化如汾水之流从自己身上流淌过去,发扬光大。寅恪先生一生为人师表,自叹“续命河汾梦亦休”,吟出此句时为1949年,若作广义解,“续命河汾”也不仅仅是设杏坛执教鞭,而应有更深大的意义,即守住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在政治权力以外,建构起自成一体的知识价值体系,并在这价值体系内实践并完成现代知识分子对历史对人生以至对文化的责任与使命。
在传统的读书人中,即便是苟且性命于乱世的诸葛亮王通之辈,其南阳躬耕也好,河汾教席也好,行文出处的最终价值仍在庙堂,庙堂不存,文化也难免看得轻些,所以有静安先生的自沉,而寅恪先生明知庙堂者旧朝既崩,新朝未卜,但他仍旧决定了自己的去留,以一具残废之身来尝试新的道路,即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坚定了这个心思,才会有他答复科学院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他是明知这两个条件不会兑现,而舞项庄之剑意在重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惊天动地的旗帜,凝聚了一代以至几代知识分子血泪与生命的精神标志。这篇“答复”是值得回味再三的,寅恪先生首先重申这“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出典,为1929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之际之首次提出,现又重申,表明不专对共产党政权而言;然后再次阐明“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只是为了划清庙堂的政治权力价值与民间的知识权力价值的分界,使晚清以来知识分子与庙堂权力者长期纠葛不清的对立、冲突、参与、争宠等恩怨孽缘得一了断。
或可追溯,寅恪先生提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在民国达成一统之际,也就是知识分子将永远告别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将重新确定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之际。
静安先生之死与寅恪先生首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看作是古代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即将完成。自然,一方面是庙堂的封建王者(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代表)的僵尸尚在作祟;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未必就脱胎换骨,根除了庙堂意识,以后几十年知识分子的坎坷史均可证明这一点,然而寅恪先生的超前意识和现代意识,也只有在半个多世纪的沉痛教训中,才会慢慢地被后来者所领悟、所感受,这正是寅恪先生精神不死的当下意义。
确定寅恪先生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转型期的奠基性贡献,寅恪先生在最后二十年间寂寞的生命旅程之谜就能迎刃而解。寅恪先生以洞察政治历史的明睿与通达,在专制体制下从容不迫地工作,如履薄冰又游刃有余,一次次在无数的“动态”“近况”边上有惊无险,终以庙堂民间两条平行线的方式安然无恙,至于 “文革”大限,那是超出了历史常轨的疯狂,为圣人所难料。
若以此说来衡量这本传记,陆键东先生功在于敏锐感受到时代对寅恪先生的理解所在,及时用文学笔法一一钩沉出日常事物背后之“象”??陆氏谓之“生命”,并以知识分子的家世背景、学术渊源参照之,或多或少传出了某种信息,这是时代风气所需,也是几代知识分子苦求之精魂所在。
但其病也在时代风气所致,现时代对寅恪先生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呼唤,依然是寄托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屡遭失败的广场意识,所以浮躁之气不绝,发扬的乃是抽象的独立人格与气节,却未见寅恪先生所以能实践这一民间岗位上的工作,还是有赖于他的为世人所不达的知识体系。
寅恪先生瞽目而著书百万言,临死前还念念不忘以其科学治学方法传世,这都表明了一个学者以生命来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古代的王通“续命河汾”仍不过是士人走通庙堂的另一种形式,相传其授弟子数千,唐朝开国功臣房玄龄、魏徵等人均出其门;而陈寅恪先生却更看重的是韩愈在文化上的“奖掖后进,开启来学”,在文化上薪尽火传开启后世。
他说: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韩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
其心向往之者,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在新朝开国之初,率先发出的是“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不是”的师训,以专业知识为价值取向,以民间岗位为立足根基,才有了不曲学阿世的根本所在。
若专业知识的一面不强调甚而漠视,那人格与气节,依然停留在梁漱溟式的士大夫品位之上,依然不能传出陈寅恪先生的现代精神之真谛。
读蒋天枢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传》,短短三章中有一章重点介绍了传主的学术思想和成就,相对照之下,这本传记回避对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接触,或可说是作者于学术的敬畏态度,但终是件遗憾事。其轻者,也是时代之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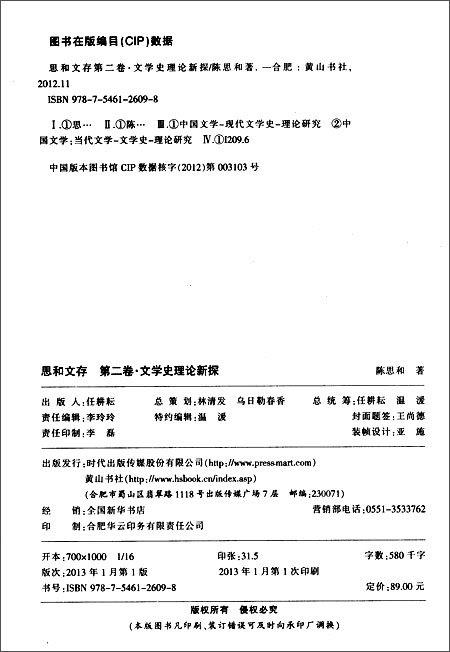


















![>陈思琪个人资料:陈思琪art微拍私房照片曝光[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7/d0/7d0abf1d9a663d698f43b8a83c6a4956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