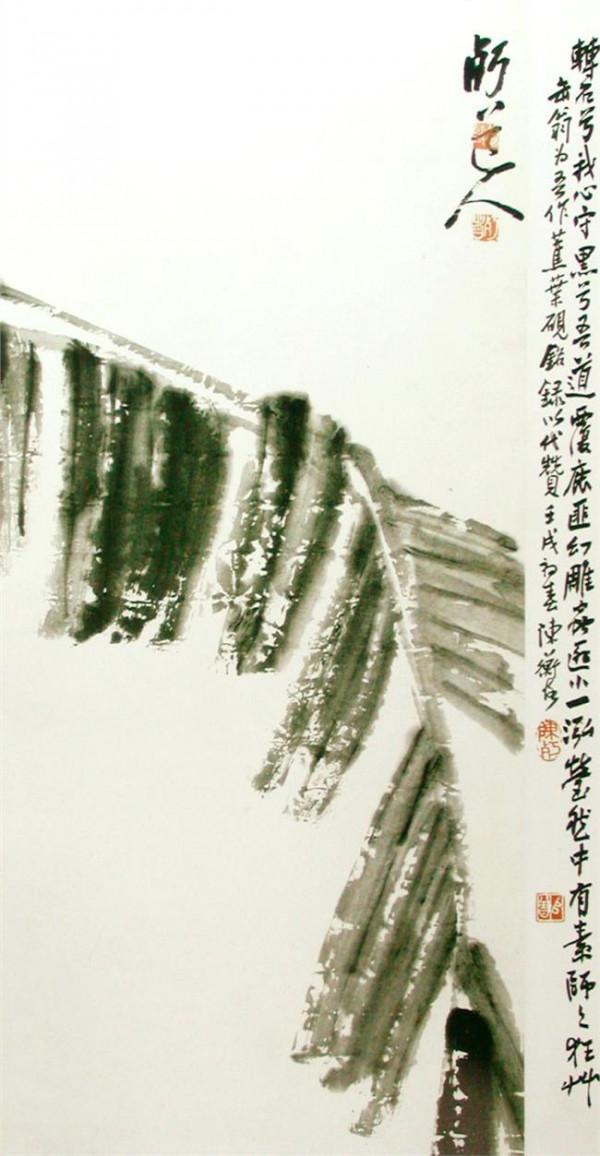中国画王微 为什么中国画发展的这么多年来 都没形成系统的透视构图的画法?
其实题主与很多朋友印象里的“透视法”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发明的”焦点透视法”。这是深厚的几何学与建筑学积淀下的产物。使用焦点透视法,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结果。
因此这个问题简单的回答就是:没有科学传统的中国,自然发展不出来这种焦点透视法。
当然,细谈起这个问题,又没有这么简单了。
在展开长篇大论之前,必须要提起所谓“散点透视”这一含混的概念。所谓“散点”到底是什么?是指的同一画面里焦点的平移?还是空气透视法?还是指的没有使用西方透视法的“透视法”?至今我都无法找到清晰可证的解释。
推测这一概念很有可能是用西方画论讨论中国绘画时生造出来的词汇,以图把中国绘画嫁接进西方绘画的评论体现中分析。但在使用“透视”观念的同时,却又拒绝用透视法的理论对中国画进行分析,反去附会传统语境中的“三远法”等视法。
以图证明中国亦独立地发展出了西方式的透视理论,最终使得水越搅越混,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这根本上涉及两套观念体系冲突时,常见的撕逼现象,类似于中西医之争。因此我不打算使用这一概念形容中国绘画中出现的透视法,而统一使用西方/现代的透视学理论讨论这一问题。
以透视法观念来审视中国绘画,可以笼统地认为中国绘画主要依靠平行投影中的斜轴投影,轴测投影与空气透视法来表现立体感与景深。而用的最多的主要是斜投影。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就是没有焦点,也不存在地平线与消失点的概念。中国古代大量使用的斜投影透视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透视法,在欧亚广泛地使用过,也并不是什么东方特色。
(三种透视示例 焦点透视法(线远近法) ,斜投影,轴测投影)
(明 仇英 園林清課圖 軸 透视分析)
正如开头说的,焦点透视法理论的形成与建筑学密不可分,最早发展出焦点透视观念的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以及系统地把透视理论引入绘画的阿尔伯蒂(Battista Alberti)无一例外是建筑师出身。
尽管在他们之前已经有马萨乔(Masaccio)使用了焦点透视法,但上升到理论层面还要等到建筑师们来加笔了。其实相比于焦点透视法在绘画中的应用,他在建筑学以及测绘领域中的重要性要大的多的多的多,毕竟房子画歪了也就是是张画,房子盖歪了就要出人命了。
(视觉锥体 Aberti,della pittura 1435)
(视觉锥体 Nicéron, La Perspective Curieuse, 1663)
焦点透视法的出现与建筑学密切相关,这一点你在中西方不谋而合。譬如我国古代的功能性绘画“界画”中,对于建筑物的透视把握的就非常精准。“界画”这个东西说的再直白一些,最开始就是建筑效果图。在宋代,“界画”达到了西洋透视法传入前的最高水平。这和宋代技术大发展的背景密不可分,尤其是《营造法式》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建筑学理论的巅峰。
故而我们在宋元时代的绘画当中可以看到大量精细描写建筑的作品,比如人所共知的《清明上河图》。也出现了诸如郭忠恕,王振鹏等一批精于界画的画家。他们都把平行透视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从这些画家的作品当中,我们依然是没有看到焦点透视出现的端倪。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古代建筑水平相对欧洲而言比较落后,而从事建筑设计的匠人阶级也毫无社会地位,他们的很多经验都不受知识分子的重视。而在科学方面,中国更缺乏几何学传统使得,匠人阶层的经验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建筑设计也得不到理论层面的指导。此外,古代绘画卷轴的形式约束了焦点透视法的应用,在一个极长的横轴之上只有斜投影能够做到既表现出建筑的立体感,又能保证足够的空间容纳大量景物。
最后一点则是由于中国自己的艺术理论成熟的很早,形成了路径依赖。而文人阶层则又垄断了艺术的解释权,他们强调作品的精神性与观念性,回避写实主义与透视学理论的应用。这种“艺术意志”在宋代以后愈演愈烈,对东亚绘画的发展路线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尽寸眸之明。《叙画》王微 南朝 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 《梦溪笔谈》沈括 宋
简单的说,这就是整个问题的答案。
然而这个设问中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画”?中国画仅仅指的是没有使用过焦点透视法的绘画么?又或是使用“线”来表现的绘画作品么?又或者是水墨画山水画?显然问题不是这样简单。
“中国画”“日本画”这样的提法本身又是西方民族主义观念下产生的分类法,其实在具体讨论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简单地根据国别进行归类,割裂了东洋固有画种(如水墨画,翎毛画,文人画等)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种分类造成的另一种情况则是把“中”和“西”彻底对立起来,完全排斥西方的艺术理论。
这一类观点仅依靠诸如谢赫“六法”,“南北二宗论”或《小山画谱》之类的古代画论,轻贱技术性和功能性为主的绘画作品与创作者,没有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类绘画作品归入“中国画”的范畴中进行讨论。
事实上在明清之际,中国的各个画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西方的写实主义风格对版画与绘画(山水,花鸟,翎毛,界画,写真等等)的浸透。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焦点透视法的应用。这一技法极大地丰富了东亚绘画的表现力,由中国之于朝鲜日本,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利玛窦:上帝送来透视法
中国对于西方的透视法学习与运用非常之早,早在明代就随着“西学东渐”传入了中国。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播上帝的荣光来到中国,却意外地带来了透视学的知识。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各种以西方透视法制作绘画作品开始传入中国。利玛窦所绘制的《野墅平林图》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以西方透视法绘制而成的作品(尚有争议)。而各种宗教书籍中的插图则影响更为广泛,从《天主降生出像经解》等书之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透视法绘制的图像在华的传播。
而通过考察明代刻印的《程氏墨苑》,我们甚至会发现著者甚至从利玛窦处索取了四幅版画,以期提高销量干掉竞争对手《方氏墨苑》,可见时人对西方图像的兴趣之深,除去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魅力,透视法所营造出的奇妙空间亦是引人瞩目的重要原因。
( 利玛窦《野墅平林图》16世纪)
(《天主降生出像经解》1640年,一点透视与成角透视)
尽管此时西洋透视法知识更多地是应用在天文与测绘领域。但图像文化的交流已经催生了本土国家对于新技法的兴趣,虽然很多本土画家没有系统的透视学知识,但是通过对西方图像的摹写,透视法已经悄然地进入了中国绘画之中。从吴派画家张宏与吴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察觉到这种变化。
*(张宏 《越中十景》17世纪,吴彬《岁华纪胜图 大儺》17世纪,《全球图解》(Civitates Orbis Terrarum 1572年))
其中对于桥的刻画方式明显有别于传统绘画,我们可以看出张宏作品中的桥试图模仿一点透视的效果,而吴彬似乎也有这种倾向,但最终无法和传统技法相互调和。尤其是张宏的桥与《全球图解》版画中的桥非常相似,有可能直接受到了它的影响。(尚有争议。)
自利玛窦起,西方绘画给南方留下的深刻影响一直贯穿了整个清代,而在北方,宫廷绘画的兴起又为透视法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
2焦秉贞:为艺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
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清廷对于西方文化的浓厚兴趣,大量擅长科学与艺术的西方传教士得以出仕宫廷,西方文化的传播在清代中期达到了高潮。这一点在艺术上体现的异常明显,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焦点透视法”在宫廷与民间的广泛应用。
清代运用焦点透视的画家不计其数,最早精于此道者,当推清初画家焦秉贞。焦秉贞的代表作品是广为人知的《御制耕织图》,在这一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到西洋透视法与古典题材的结合,然而这一作品中透视法的运用水平相比于焦的山水系列而言,还是略为逊色。
*( 清 焦秉貞 山水 原籤山水楼閣 第7開 )
焦秉贞的这套山水图(原籤山水楼閣)对于一点透视与多点透视的精准运用异常的精准,如不说明,很多人甚至会误以为这是今人伪作,可这确实是清朝中国画家的手笔。
焦秉贞之所以能够如此纯熟地运用透视法是有其特殊的原因的。首先焦秉贞起初并不是一个职业画家,他的正职是钦天监五官正,正经理工男。其人不仅是汤若望的徒弟,还在南怀仁门下学过视学基础,临摹过当时欧洲刚刚出版不久的《建筑绘画透视》(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Pozzo, Andrea,1693),非常熟悉西方那一套。
作为科学工作者,焦掌握了一般画家所不具备的数学知识,而这也是使其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西洋透视法背后的科学原理。后来焦也因其出色的透视法绘画,深得康熙皇帝赏识,最终“供奉内廷”,走上人生巅峰,成为了清朝前期最重要的宫廷画家。
其实无论以中国的传统画论还是西方视点来看,焦绝称不上是一流画家,但是由于满洲皇帝对于透视法绘画的浓厚兴趣,才使其能在宫廷画家中脱颖而出。
(康熙朝通景画 《桐荫仕女图》屏风 17世纪 传 焦秉贞作)
相比于对油画中阴影描写的厌恶,对于透视法的迷恋贯穿了清代宫廷绘画的始终,成为西方绘画风靡清廷的重要线索。透视法营造出的错觉艺术深为清人所倾倒,著名艺术票友乾隆皇帝就痴迷地爱上了焦点透视法所营造的空间感,因而他所有的寝宫几乎都画遍了“通景画”。
另一方面在于透视法在工程学上的重要作用,圆明园的设计与装饰都少不了掌握了透视法的西方画家的参与,而满洲皇帝修园子的异常热情亦推动了这一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在皇室的推动下,焦点透视法与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逐渐融合,形成了折衷主义的宫廷绘画风格。
3郎世宁:皇上已经钦定了,透视大法好。
欧洲传教士很早就意识到透视法对清国人的吸引力,这使得透视法的意义远超过了绘画本身,在宗教上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传教士为了传教,无不勤学苦练透视大法,甚至在1700年从欧洲请来一位专业画家杰凡尼·切拉蒂尼(Giovanni Gherardini)来清廷授课,其人曾绘制北京的基督教堂“北堂”的内饰画,围观群众无不称奇。
然而切拉蒂尼仅仅呆了4年就受不了宫廷的约束与耶稣会的叽歪,匆匆打道回府了。紧接着清廷将迎来对中国绘画史影响最大的西方画家:郎世宁。
自1715年到达中国以后,郎世宁就因为精于绘画,很快便被召入宫中,开始了他在紫禁城漫长的绘画生涯。尽管在郎之前的数位中西画家已经把透视法带入了宫廷绘画之中,但直到郎为止,才最终将其融合在了中国绘画之中,开辟了折衷主义的“新体画”风格。
在清廷供仕期间,朗与其他传教士一道,在画院处与如意馆中系统地传授西洋绘画技法,许多包衣出身的画画“柏唐阿”(听差人)和宫廷画家都在其门下学习过。这些课程与今日应考的艺术生接受相差不远,其中不仅有素描和解剖学,自然也包含透视法的知识。
有许多例证可以证明在此学习的中国画家扎实地掌握了焦点透视法。比如在郎世宁去世后,为乾隆帝绘制宁寿宫倦勤斋通景画的王幼学(他可能也是最早掌握巴洛克风格的中国画家)以及日后主持圆明园设计的伊兰泰,他不仅擅长“通景画”的制作,还大量采用焦点透视法绘制了圆明园的施工效果图。
(倦勤斋 ,通景画 ,伊兰泰 圆明园相关绘画)
这种折衷主义风格的产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皇帝的审美取向,相较于雍正帝对西洋“写真”的偏爱,乾隆皇帝则更喜欢富有中国情趣的风格,在皇帝的授意之下,郎世宁与其他传教士的画风不得不做出了调整:平光无阴影,写实又透视精准是这一风格的典型特征。
同时,由中西画家合力完成的“合笔画”也调和了这种两种不同的风格,比如由丁观鹏与郎世宁合作的《太簇始和》图就是一例。由郎世宁绘制的草图与底稿确立构图与透视关系,余下的则由丁独力完成,最终呈现的就是既有透视法的“骨”又有中国画的“意”的绘画作品。
(《太簇始和图》18世纪)
然而对于焦点透视法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皇帝们的艺术细胞,数学家年希尧就是另一个精研透视学的人。当然他的着眼点并不是绘画本身,而是数学的运用与传播。在其牵连进弟弟年羹尧案后不久的1729年,年希尧出版了东亚最早的透视学专著《视学精蕴》。
为了研究透视学本身,老干部年希尧曾专门到郎世宁门下学习过透视法,其著作中也引用了焦秉贞当年临摹过的《建筑透视学》内容与图片,出版后觉得不够料,自己又添了五十多张增补之,中西融汇,内容翔实,可谓理论界的盖世奇书。
(《视学精蕴》附图)
这一书出版不久就流入了日本,然而对日本的透视学启蒙则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即便是在中国,这部书也最终如石沉大海,没有惊起任何波澜。该书过于精深的透视学理论即便在今日,也不是一般人所能领会的,更别提18世纪的清朝学人画工了。年希尧去世后,中国对于透视学的研究就止步于此了。
由于1773年耶稣会解散,终止了派遣传教士的活动,西方文化输入宫廷的重要途径断绝。在最后两位传教士潘廷章,贺清泰去世后,西方绘画在宫廷的影响逐渐式微。进入19世纪后,曾经在风靡了整个18世纪的“透视法”从宫廷绘画中消失的无影无踪,仿佛不曾存在过一般。
不过在南方,则完全是另外一翻景象。
4.姑苏版:与浮世绘分享一点绘画的经验
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清代的海外贸易极为发达,以浙江去往东洋,由广州去向西洋,中国物产跨越波涛远销世界各地,走入公侯百姓的生活之中。除去传统的瓷器与茶叶,“画”竟也成了出口创汇的重要商品。而这就是苏州版画与广州外销画的故事了。
无论是姑苏版还是外销画,都广泛地接受了西方绘画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透视法”。相比较于文人阶层对于气与意的艺术追求,这些绘画则是纯粹的商品,完全是依靠市民阶层消费的文化制品。老百姓是不大懂文人那一套“气韵生动”的画品的,他们更惊异于透视法所营造的视觉空间,仿“泰西笔法”成了销售的重要的保证,版画商人自然也不放过这一商机,洋风“姑苏版”就这么诞生了。
*( 一个常见的题材 姑苏万年桥)
随着清日贸易的隆兴,苏州版画也流入了日本。由于长时间的锁国与禁书令,江户时代的日本起初只得依靠中国作为中介输入欧洲知识。到了1720年日本虽然解除了禁书令,“兰学"才有了生长的空间。(注:这次解禁仅仅解除了“汉译洋书”的流入,对于西方书籍的直接翻译与引进是极其有限的。
)除去天文历算,农政兵学的新知识,新的图像风格也引起了日本人极大的兴趣,根据17-19世长崎贸易的货物调查,发现版画是贸易品中的一大宗。仅1754年的一艘清国贸易船就运来了三万余枚版画。这其中自然包含有使用了“透视法”的姑苏版。
中国版画的传入对日本浮世绘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影响,其中就包含“透视法”在日本版画中的应用。与中国一样,“透视法”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机,引来许多本土画家竞相模仿。自称第一个在浮世绘中使用了“透视法”的奥村政信就是如此。有明确的证据表面他直接拷贝了中国传入的版画,创造了日本风格的透视法版画“浮绘”。
(上《莲池亭游戏图》下 《唐人馆图》奥村政信,这张图中的场景很显然是对《莲池亭游戏图》的摹写,人物和位置虽然改变了,但其实是拷贝自另一本中国画谱)
那么话说回来,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西洋的透视法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版画呢?时间又要退回到明朝,就在利玛窦来华前两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已经开始了在南京一带的传教,而由他带来的西洋铜版画一时间引起轰动,使得不少本地画工竞相模仿,比如前文提到的《程氏墨苑》。
到了清代,西方透视法对江南的影响则变得更加多元。除去对西洋书籍中的插图进行直接模仿,苏州刻工们可能受到了宫廷绘画的影响。由于江南的版画制造业最为发达,南方出身的刻工经常参与到官方的版画制作中去,临时工结束以后,自然把西洋的透视法带回了南方。
其中有名可考的例子便是朱圭,他曾经参与过焦秉贞《御制耕织图》以及冷枚的《万寿盛典图》的刊刻工作,这些作品都使用“焦点透视”的技法。考虑到朱圭在苏州拥有自己的版画工坊,他很可能把西洋的透视法从宫廷带回了老家。
另一个有趣的来源则是天主教。有证据表明在苏州专门制造这种洋风“姑苏版”画的刻工来自天主教家庭,如活跃在康熙年间的丁允泰。他的作品上的“洋味”明显大过了传统版画的风格。作为天主教徒,他们很可能直接参与过教堂中传教书籍的刊刻工作,甚至可能直接得到过传教士的传授。但是由于缺少史料,这一方面的真实情况就难以得知了。
《西湖图》丁允泰
不过从这些洋风“姑苏版”画的风格来看,作者大多并没有什么精深的透视学知识。他们创作的主要手段在于模仿。甚至直接拷贝西洋图像的透视关系,然后将其置换成中国的景物。虽然没有太多的史料证明这种行为,但从日后日本浮世绘师摹写中西版画的行为来看,这种可能性是极高的,反正要的就是个效果,卖的好就成,透视法的原理到底咋回事,随他便吧。
( 翻刻的欧洲版画《西洋剧场图》)
具体分析姑苏版绘画对于透视的运用,我们不难发现两种情况,一部分作品偏爱简单的一点透视,这种透视塑造出的景深非常具有吸引力。另一种更为普遍的做法则是用"鸟瞰图"来描写城市场景,这种作法多见于使用纵轴构图的版画之中。现在保留下来的洋风姑苏版中,这种纵轴构图的作品数量最多,其用途可能是用作中式屏风的屏风画。
(《西湖十景图》,《清国南蛮渡来屏风》《苏州景 新造万年桥》)
然而随着乾隆中期厉行禁教,持有西方图像也成了煽巅罪的罪名之一,带有透视法的版画自然成了活靶子。各路体制外画工明哲保身,纷纷放弃了西方邪路,洋风姑苏版也就此衰落,只剩下一些走街传巷的“洋片”艺人苟延残喘。
然而最致命的打击还要等到太平天国的到来。同是一群“拜上帝”的人,席卷了东南各地,文物毁坏无数,苏州的版画行业也被彻底摧毁了。上帝带来的,最终又被“上帝”带走了,姑苏版在中国就此绝迹,如今的我们只得从日本人的藏品中一窥究竟了。
不过在广州,透视法与中国的故事,仍在继续。
5.广州外销画:闷声发大财,清朝的“达芬奇村”
无论北方的政局如何的波涛汹涌,似乎都惊动不了广州这一方净土。画工们的笔下的风物,随着风帆由此远涉重洋,走入了欧美公侯百姓家。自18世纪以来,直到照相术发明为止。广州的外销画贸易兴盛不已,这里不仅出现了艺术风格紧跟欧洲的油画专家,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艺术产业园。同时也可能是最早的海外代工厂。
如果说江南地区的版画是把西方传来的“透视法”融入了传统绘画之中,那么广州的画业则走了彻底相反的路线。在全盘学习西方绘画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绘画的风格。
珠江地区的洋画历史渊源流长,早在罗明坚利玛窦进入不久,珠江地区就孕育出了本土的油画行业。在澳门,诞生了中国第一位油画作者:游文辉。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为利玛窦所绘制的肖像。
传 游文辉作 利玛窦像
进入清朝以后,大量西方商人来华,然而在一口通商的约束下,几乎所有的贸易都要经过“十三行”中介进行,唯独绘画不在此规制之中,如此以来使得广州本土画家有了和西方商人直接做生意的机会。起初西方商人只是购买一些出自中国画工之手的绘画作为纪念品,但很快精明的广州人民就抓住了商机,搞起了绘画代工业,“中国制造”的廉价艺术品从此开始流入欧美。
由于这些作品本质是为了服务欧美市场,广州的绘画工坊从一开始就是全盘西化的,西洋透视法的使用亦是自然。无论是油画水粉水彩玻璃画,还是西洋风景人物风俗,广州画家都一应包揽。尤其在油画领域出现了史贝霖(Spolilum),关乔昌(Lamqua)这样毫不逊色于西方的画家。
凭借高水平,低价格的优势,彼时委托广州画工制作绘画的事情早已不是稀罕事,无论是荷兰使臣范罢览的《中国画册》,还是宫廷委托下的《平定西域战图》。甚至有直接来自欧洲与美国的订单。根据19世纪中期的资料来看,由中国画家完成的复制画或肖像价格大约在10-20美元不等,比西方画家的作品便宜5到10倍不等。
上 Portrait of Martha Goodhue Wheatland, wife of Captain Richard Wheatland, 1799-1800,史沛霖,油画
美国定制的玻璃画:
尽管广州外销画作者中,有技艺高超的大家。但更多的从业者却只是没有受过多少训练的“画工”。广州的绘画工坊采取了流水线式的组织形式,作品线稿或有专人摹写,或直接用印版印刷,画工们分别负责不同部分的作画,很多人不能从头到尾完成一部完整的作品,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代工工厂。因此这些人多没有精深的西洋绘画知识,对西方技法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僵硬的模仿与复制。
上 庭呱(Tingqua)画室中的画工
这些作品主要以廉价的“通草画”为代表。通草画的主要作画材质是水彩与“pith paper”(通草纸),在19世纪中后期,一张通草画的最高价格仅有0.098美元。意外的是,这些蹩脚的作品却催生了一种中西折衷的独特风格。这种廉价的作品极大地满足了西方的猎奇心态。在“东方想象”的心态之下,广州生产的“通草画”却成了富有异域特色的抢手货,占据了外销画的统治地位。
这种独特的风格首先在于作品对透视相对精准的把握,与姑苏版仍旧生涩甚至错误的透视应用,这些廉价的通草画在这一点上始终拿捏的很好,而且采取的形式多种多样。此外,与宫廷审美异曲同工,这些通草画都刻意地忽略光影效果,人物刻画回避“阴阳脸”,甚至投影也一并省略。
这种对光的处理显然来自于中国绘画的传统审美。而由于没有受过什么解剖学的训练,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大多摹写西方版画的风格,不过存在结构错误与比例的失调的问题,又或者干脆按照传统绘画的方式绘制人物。
上 Tending the Silkworm Cocoons, about 1790,不透明水彩
下 Packing porcelain for export, about 1825,水粉
总体来讲这种作品在技巧上大多拙劣生涩,艺术价值不高,但无论在怎样的题材之中,使用透视法的使用都已经变的不可或缺,显然这种手法已经被广州画业广泛地接受,成为了外销画的重要特征。
外销画产业链一直发展到19世纪末期,终于同许多西方画家一样,遭遇了时代变迁带来的困境。照相术的发明,大大地削弱了绘画的功能性,西方绘画也由此跳脱出写实主义,开启了印象派的探索之路。而在中国的南方,外销画产业链则被悄无声息地埋葬在历史深处,于画史中觅不到一丝踪迹。
回想当年这些画工的命运,再看看如今的达芬奇村,不由唏嘘:时间没有焦点,凡人亦不能透视历史,命运只是在画纸上绕了一个圈,同样的地方,又一批人循着相同的轨迹展开了自己的人生绘卷。
历史不会循环,但会押韵。
参考资料(部分)
施世珍、中国画透视研究
桶田洋明; 波平友香; 山元 梨香,絵画と遠近法1東西の比較から絵画教育の可能性をさぐる-
杨泽忠、利玛窦与非欧几何在中国的传播
刘振华、关于《程氏墨苑》之“宝像图”的研究
高居翰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
黄素娜、中国写实风格山水画研究-以张宏的山水画为例
苏立文(Michacl Sullivan)、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应
李启乐(Kristina KLEUTGHEN)、通景画与郎世宁遗产研究
聂崇正、中西艺术交流中的郎世宁
邓耀明、中学西渐与西学中传——论15-19世纪中西版画交流
张烨、洋风姑苏版研究
岸 文和、江戸の遠近法―浮絵の視覚
黑田 源次、支那古版画图录
永积洋子、唐船输入品一览1637-1833
冷东、广州十三行与中西绘画艺术交流
徐堃、十八,十九世纪广州十三行和外销画
潘瑶、晚清广州外销画的贸易 生产及订件
部分图版出处
国立故宫博物馆
结语(可以不看...)
每每谈到中西交流的话题,总会遭遇到同样的质疑,既:“为什么要用西方的视点评价中国的XXX”。首先必须要说的是,无论我们用不用这样的视点去审视历史,交流是地客观的,不可否认的,而如何解释这种交流,如何评判“高下”,就涉及到了观念体系的碰撞。
无论是否接受西方视点的审视我们的历史,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都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完全排斥西方的观念体系,必然是固步自封,因为传统世界已经消亡了,传统观念的土壤丧失了,而现代文明的“底盘”也并没有诞生在东方。这就意味着中国虽然很多方面都有自成一体的体系,但都必面临着如何与西方/ 现代文明的体系进行对接的问题。
现实的背景是,近代以来公立教育与大学的建立,标志着学术体系本身的西方/现代化。“艺术”的观念,“历史学”的观念无不是由西方传入的。如果不加以分析,把传统观念与西方/现代观念混为一谈就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譬如民国时代的一干史学家,他们有着比较扎实的传统史学训练,又进入了现代学术体系,但没有处理好中国古代的“经史”和西方传入的“历史学”的关系,继而得出了一些今人看来值得商榷的观念,这其中钱穆就是典型。
邻国日本就没有这样的负担,因为他们在江户时代并没有本土的画论与史学,中国与西方的理论对其而言并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没有必要紧抱传统不放,观念体系上的转换比较轻松。这是日本现代化比较顺利的直接原因。
在看待艺术问题时,也是这样。“艺术”(art),“透视”本身就是纯粹的西方观念,艺与术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与之截然不同。故而当我们使用这两个词汇讨论问题的时候---即便是打着反对西方的旗号---事实上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观念体系了。发明“散点透视”的观点也好,反对使用西方理论审视“中国画”也好,甚至认为自己是“东方”本身,其实都是站在西方观念的“笼子”里面跳舞。
除非有人能够继续使用中国古代的画论进行评论,并使这一体系存续下去。否则,我们就无法摆脱西方观念的影响,很多试图弥合两种体系的行动,多以错乱的概念搅成一潭浑水为结局。因此,并不是说一定要彻底抛弃传统画论,而是采取西方的视点更不容易出问题,更容易为专“现代人”所理解。
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何要摆脱西方/现代观念的影响?真的有这样的必要么?如果按照我们的传统观念来审视“艺术”,民间版画也好,广州的外销画也好,甚至带有“匠气”的作品可能就会永远地埋没在历史之中,得不到重视与保护,更无法为人所知,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算“画”,亦不入品。
探讨透视法的话题,其实并不涉及传统绘画理论的冲突,因为中国压根没有这个系统,冲突的其实是评价体系,也就是画论的问题。不过吊诡的地方在于,相比古代文人对这一手法的彻底鄙视,现代人更试图证明其“自古以来”的存在。
这种倾向性,首先已经把“透视法”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以致于要竭虑地证明我们自己搞出来过,才显得不输西人,跟的上时代。这种举动根本是一种对“西方中心论”的默认,既对本土的传统画论没有信心(换做古人就直接对透视法呵呵了,用这东西就是掉价儿,who cares.),又拒绝承认西方的影响与先进,但又太把这当回事,以致于造出了“散点透视”这一不伦不类的概念。
不过这种行为却又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是民族国家面对现代化压力时提升自信的常见手段,所谓“发明传统”是也。无论是“资本主义萌芽”还是曲解郑和的“大航海”,再到对焦点“透视法”的非议。都是在近代化过程中焦虑的表现,我们深知西方的先进之处,却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故而要在西方超过我们的关键节点问题之上找回颜面,挂着东方的龙头,卖着西方的罐头,观念世界在深处早已西化了。
抛弃艺术评论体系的不同所带来的困扰,有关焦点透视法的争论的核心是有关科学的争论。附会中国古代有原生的焦点透视法,或有自成一套的所谓“散点透视法”本质是对古代科学体系落后所产生的焦虑。因为焦点透视法的广泛应用必须有深厚的几何学作为基础,而这正是其他文明所缺少的东西,亦是走向现代化时所必需的燃料。
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化”的焦虑会逐步轻减,观念体系亦会整合。“中”与“西”的位置与高下也将变成次要的话题。因为无论何种文明的成果,在今天都是世人所共享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