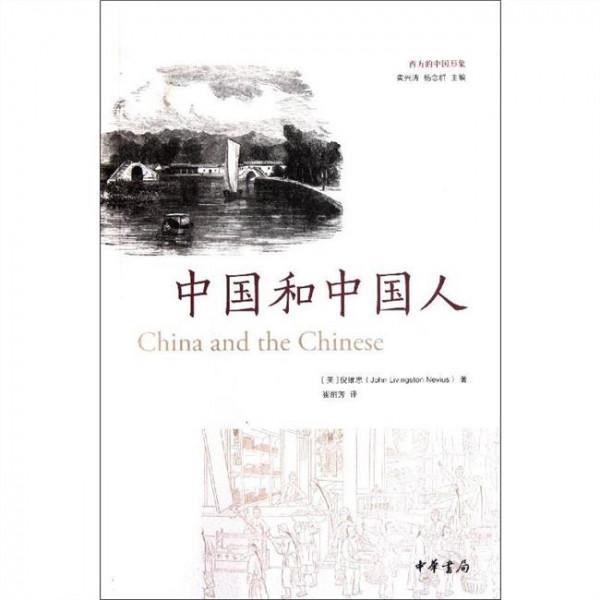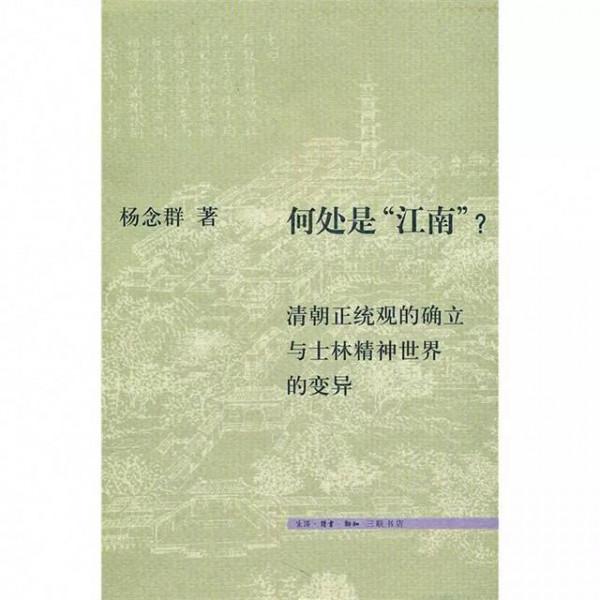杨念群和妻子 学者杨念群:“呆子治国论”可以休矣!
《儒林外史》有一段胡屠户打女婿的故事,说老童生范进考了二十多年的科举,五十四岁才中了举人,没成想,一看到报帖就狂喜过度一跤跌倒,不省人事,被几口开水灌醒过来,傻笑着往外飞奔,一脚踹在塘里头发跌散,两脚黄泥,淋淋漓漓淌着一身水,拍着笑着一路走到集上去了。
到集上一个庙前已是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一只,嘴里径自叫着“中了”,众人一看劝不住,赶紧把他的老丈人杀猪的胡屠户叫来,胡屠户凶神般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么?”一巴掌扇过去顿时打晕,众邻居替范进抹胸捶背,舞了半天,方才苏醒,等他眼睛明亮起来,胡屠户却觉手掌生疼,向上弯曲,心里懊恼,觉得天上文曲星果然打不得,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
这番话细说胡屠户打了“文曲星”,好象一副知罪的样子,可这范进怎么看都像卡通中的荒诞角色,哪里有半点文曲星的影子。“屠夫打贵人”的桥段被刻意从小说中截出,硬性插入当代中学课本,貌似经典般代代传诵开来,目的当然不是讲一个乡间俗人从潦倒到腾达的励志故事,控诉科举的虐人灭性,揭露旧社会的丑恶才是背后的真意。
这段妖魔化科举的戏言经反复引证,不知成了多少人少年时代的愉快记忆,大有提神洗脑的奇效。在人们的眼中,“科举”完全就如一枚精神致幻剂。研习八股文章恰似注射毒针迷药,沉溺惯了无论轻飘在空中还是横行于陆地不外是变成疯人或者化为僵尸。这些疯人僵尸平时就会呻吟出点无用的诗词歌赋,或满嘴叫嚣出言不及义的道德说教。
科举使人化为病态僵尸的传说大约源自后世对宋人的印象,宋代文人受宠骄纵远过于武人,他们整天就喜静坐发呆,无所事事,如果谁看见某人心事重重打蔫愣神,一定是在苦心琢磨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或是“理”。他们穿戴服饰尖顶峨冠,言语怪诞,行为乖僻,连仪态模样都羞与人同,他们逢人鞠躬,姿势缓慢低深,说话不打手势,据说某个道学大师的门人见到宾客还使用一种奇特的敬礼方式,好象不如此疏离俗人就显不出那份高人雅士的范儿。
这帮“怪物”说的种种闲话后来堂皇入室,竟成了官学考生必须死记硬背的教条,“怪物”们的举止虽不合群,然他们的冷僻言论一旦被编进考题,世世代代的考生就须无奈仰之以为衣食父母。有趣的是,科举鼻祖们大多闲散淡雅不愿做官,如道学掌门朱熹勉强干了十几年的地方小官,在朝廷内只呆了四十几天就不耐烦了。可朱熹编订的《四书集注》却成了考生当官必备的应试圣经。
在人们的想象中,既然宋代文人都是一帮呆子,平常束手闲心到处游逛,写出满篇的疯话呆话,却阴错阳差地引得无数考生竞相折腰献媚,那背诵这些疯话的士子就难免染上一些举止乖张的毛病,所以胡屠户的巴掌应该扇醒的就是这帮怪人。更为可怕的是,如果满朝任由这些呆子颐指气使地瞎闹下去,武人又劝不住管不着,岂不是咱们中国自宋代以后就是个疯人无端横行把持的世界吗?那还成何体统?
这种“呆子治国论”在近代尤其流行,“呆子治国论”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无论是皇上还是官僚,都坚决从前朝(主要是宋朝)僵尸语录中寻找管理王朝的经验,管理的支柱是无休无止的道德训诫,管理的方法是文牍往来。
道德说教至高无上,不仅能指导行政,而且能代替行政,皇上同样要以身作则,不停忍受呆子们枯燥无味的讲经布道,尽管经筵仪式繁冗无趣,讲官们唠唠叨叨让人哈欠连天昏昏欲睡,也要傻呵呵装出津津乐道不厌其烦的乖巧模样。
“呆子治国论”遭受抨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用“道德”替代“行政”太依赖人情善良的一面,因为人性多样复杂难测,一般没法预料谁的“道德”更加可靠,谁又能一定当上好人,就更谈不上给别人做标兵当模范了。这个判断疑似击中了呆子治国的软肋,那就是谁都无法精确掌控人性的无常,即使假设人人天生充满善性,有做善事当活雷锋的潜能,也无法测知在何时何地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这一面。
有一个笨办法是持续不断地灌输教化,慢慢让人群对善人当道有个企盼,可一旦“公义”与“私利”之间出现紧张,又必须面目可憎地假装扛着道德招牌晃来晃去,就极易训练出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的小人。
加上无可靠法律契约做保证,管理中的技术含量太低,即便朝中官员个个好心,指天发誓拼命向善,也不能弥补制度运行的不足。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好象只有一种,那就是把这帮呆子统统赶出朝去放逐到民间,让他们过过当文人骚客的瘾,朝里剩下的都是单纯质朴的行政官员,全靠契约和法律架构起“非人化”的制度程序,这样一来效率陡增让人放心,毫无人性的机器化作业才是人间正道。
尽管痛扁呆子治国早已变成控诉旧社会灭绝人性的习惯套路,尽管科举考场早已被嘲弄成锦心绣口的无聊文人尸位素餐混迹其中的是非之地。我还是要说,人性“无常”中西皆有,都需调控,却最好不宜做“道德”与“制度”绝然二分的割裂判断,好象中国人天生只会“以德治国”,庸陋不堪,完全不懂法律运转的奥妙,西人一生下来就理所当然拥有生活在“法制国家”的一条好命。
法律、制度、道德、礼仪都是通过人来操控的,对道德的控制并非只有一张刻板得令人窒息的丑陋面孔,幻想全部实现“数目字化管理”,构思虽然美妙,实际也许恰是个无法验证的乌托邦陷阱。
我的看法是,科举制是呆子生产线,明清全由呆子治理的说法肯定令人生疑,就拿清朝来说,试想,一个到乾隆时期人口已达3个亿的帝国,如果全凭一个呆子皇帝或者一帮只会满嘴说胡话连胡屠户扇都扇不过来的庸吏在操控将是个什么模样?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在明清两朝,科举制可能生产呆子,却也丝毫不差地输出能吏人精。
它还和体制配合,不时把一些舞文弄墨的呆瓜或贬斥不用或干脆踢出门去,《儒林外史》中,范进的恩师周学道发现童生魏好古用诗词歌赋来搪塞考官,遂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
看你这样务名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话,看不得了。”这是科举选拔远离纯文雅装X范儿的小例子,“杂览”在这里特指诗词歌赋。一般明清官场上对同科中卖骚做秀的文人同样也不感冒,张居正就因对同时考取的文人王世贞那股只会卖弄文采的酸腐气反感,故意抑制他的升迁。
表面上看,贬抑诗赋骚人未必就能撇清科举出产呆子的恶名,恢复它的清誉,因为参加考试的童生们都要戴上理学这顶大帽子招摇过市,脖子被大帽压疼的人难免憔悴伤神,牢骚满腹,稍感不逊就纷纷生出“理学杀人”的怨念。翻阅清代官员的文集,也都是套话连篇,满纸冠冕堂皇的理学说教,开口闭口全是道学圣人的语录,个个活象迂腐的道学老儒。其实这不过是些骗人的小把戏,就像领导做报告喜欢穿鞋戴帽,当不得真的。
我们可以举出清朝封疆大吏陈宏谋做个例子,用来戳破“呆子治国论”的荒唐。陈氏在历史上常被硬性站队,被归类到最坚定的理学弟子之列,甚至正当乾隆爷大倡考据,恢复汉家风仪的时候,他却满嘴言必称朱熹,似乎是个不折不扣不知与时俱进的腐儒。
不过千万不要被他那谦恭呆滞的姿态给蒙住了,陈氏的许多言论完全与朱熹的教导南辕北辙,此话怎讲?仅举一例可知,在宋朝,像朱熹这类道学先生都爱大谈特谈“夷夏之别”,意思是汉人与周边的族群相比具有绝对的文化优势,环拱在周围的族群都似未开化的禽兽,只有老老实实接受管制的资格,别指望还有脱胎换骨进入文明世界的一天,理学虽讲“变化气质”,不过这只是汉人的专利,没野蛮人什么事。
然而在陈宏谋的眼里,无论“汉人”“蛮人”皆是我朝“赤子”,都有改造成文明人的潜质。不像朱熹非要在汉人和野蛮人之间划出那条永生永世无法弥合的界线。
在雍正皇帝的嘴里,这叫“中外一体”,意思是不仅满汉一家,其他族群也应谐和共存,同享一种公认的文明生活,陈宏谋的“赤子论”与他遥相呼应,能不能做到暂且不论,至少在赤裸裸的反理学立场上,陈氏和这位皇上终于搂抱在一起,穿上了一条裤子,这分明是“口是心非”地说着“团结在……周围”的套话,用的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策略,从中丝毫看不出“呆子”的痕迹。
再引申得远一点,陈宏谋承认只有“文化”差别而非“种族”之分的言论,很接近现代史学的看法,例如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唐代就有用“文化”而非“种族”区分内外的观念,只不过到宋代以后才埋没隐去不见踪影。
在具体的经济举措上,陈宏谋也经常是阳奉阴违,不会死守僵化的道义规则。如逢灾年,按照朱熹制订的方略,政府一定要强力介入和干预救灾过程,地方士绅也要出于道义责任捐粮纾困。但陈宏谋却主张使用现钱流通的市场运作方式,反对单纯发放救济粮。
这在理学呆子们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见死不救。如果换一种场合,好像专和朱熹作对的陈宏谋又是理学原则的坚定贯彻者。比如在地方治理中,陈氏坚持政府干预应该划清界限,给宗族、乡约这些自发势力预留出足够的自治发展空间,这个思路又是不折不扣的朱子家法。
因为在理学家的地方治理设计中,给民间组织让渡出更多地盘,减少政府涉足的程度可能是降低治理成本的一个最佳途径,这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一套思路,带着鲜明的理学特征。
那么,我们要问,这些明清史上有名的循吏既然都是科举出身,为什么没有像范进那般疯成了呆子,也再没机会挨上胡屠户们的巴掌,其中到底有何奥妙?清朝科举试题除第一场法定测试朱子语录外,第三场必考“经史事务策”,考生大体会围绕历史上的事例引申作答,看看对解决当下问题有何帮助。
这场应试最考验考生是否能在经史文献中提炼出有用经验,由此渠道也可窥测这些未来候补官员处理政务的能力。但如果我们想指望中举后的官僚们运用这点可怜的经史知识就能直接治理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即如陈宏谋逆反朱熹传统思维搞赈灾就真不是靠应举积攒的那点僵化知识。他们能干的本事到底来自何处其中必有蹊跷。
破此谜局的关键还是不能吊死在科举这棵树上,只要把观察视野稍稍放宽,搜检一番官员阅读的书目即可知他们原来全是“自学成才”的典型。晚清官僚张之洞在四川当学政管教育时,特开出《书目答问》作为士子的阅读书单,居然洋洋洒洒列出了两千多部书。
除必读的经史书籍外,还包括金石、地理、诏令、奏议、地理、医家、兵家、法家、农家、小说家、释道、术数、天文历法等,仅门类目录一眼望去就林林总总多得吓人,更别提内容之庞杂多样,看了几乎令人绝望。
如果相信他举荐的这些书自己都浏览一过,那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巨大工程,哪里是科举时文的品质所能包容下的,更不可能是范进之流的案头必读之物。不禁让人惊诧这些官员的时间都到哪去了?何以有如许多的精力沉潜其中。
我由此坚信,官僚们治理国家的经验大多与科举的应试训练无关,主要靠后来恶补修习而成。陈宏谋在湖南推广一种水车,旱时可车水到耕田高于水源的地界,在陕西推广薯类种植,解决粮食紧缺问题,都与科举研习的内容无关,而是后天用心补习的结果。
他脑子里储藏的精耕、除草、嫁接、轮作、复种、施肥的技术都是从一本叫《授时通考》的书里学来的,这本书脱胎于明代的《农政全书》。陈宏谋养蚕纺织的知识则来自一位关中地方学者的专著。他们的阅读书单常常不拘于官学指定的经典,只要对治世的经验有用,均属他们杂览的范围。
陈宏谋赈灾时用现金流通替代直接发放实物救济的思路就得益于明代福建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学者著作。清朝官员对经济事务的重视甚至渗透进义学的教育之中,陈宏谋治云南时给七百所小学规定的必备藏书中,经他自己缩编加工的明代经世读物《大学衍义补辑要》,收藏的数量要远远高于朱子格言等理学读物,这本书充满了各种有关刑律、武备、贡赋等民生现象的讨论,期待就读义学的少年自小就打下关心实学的底子。
一般认为,普通人做官是出于道德的责任,科举应试都是为了体现自我道德修炼的正当和完满,仿佛这种培训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和日常生活挂不上联系,只是充当记诵先人语录的复读器。这也加重了人们的误解,以为科举熔炉中淘洗出来的不是呆子就是傻子。
实际上,大多数能臣循吏,都是在上任后经过多年摸爬滚打的历练才提升了自己的治世能力,当年科举的训导只是为获取一种入官资格,与治世的阅历经验和见解并无直接关联。更严重点说,从科举生产线中脱颖出来的官员,其成就大小恰恰与科举训练的程度成反比。
同样是科班出身,“流品”却有高下之别。陈宏谋有一句话说的贴切:“自古流品,诚不足以限人也。……有志者,正可乘时自奋矣。”这句话的最浅显也最易领会的意思是指,家庭没有世袭荣耀的背景并不重要,只要经过努力就可弥平身份差异。
还有一点是本文所要揭示的,流品的高低实在于你能否真正冲破应试程式的束缚,给自己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明清为官功绩的大小确也证明,谁对应试八股规定的阅读范围超越得越彻底,谁就越有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创造一个新世界,这就是“流品不足以限人”的真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