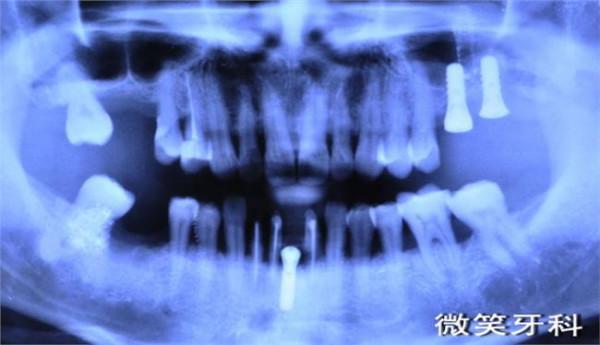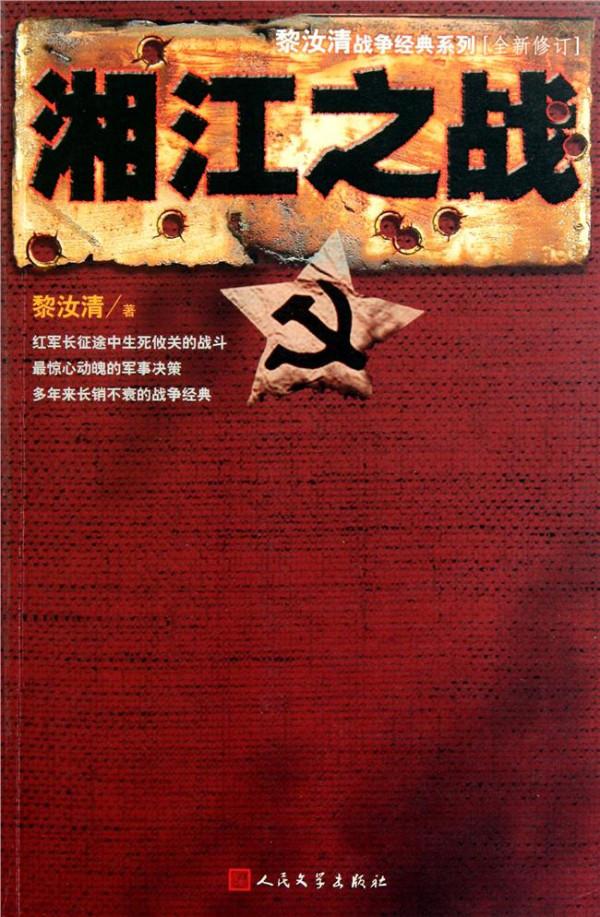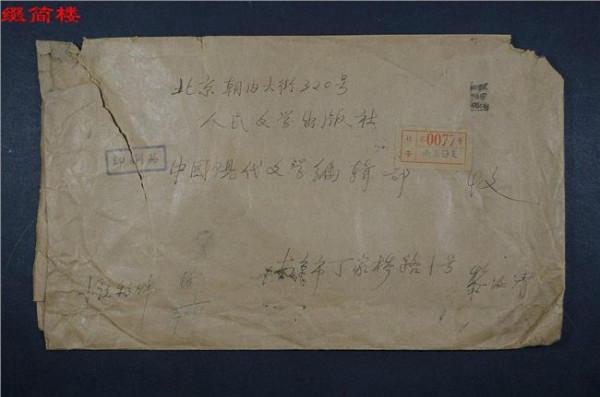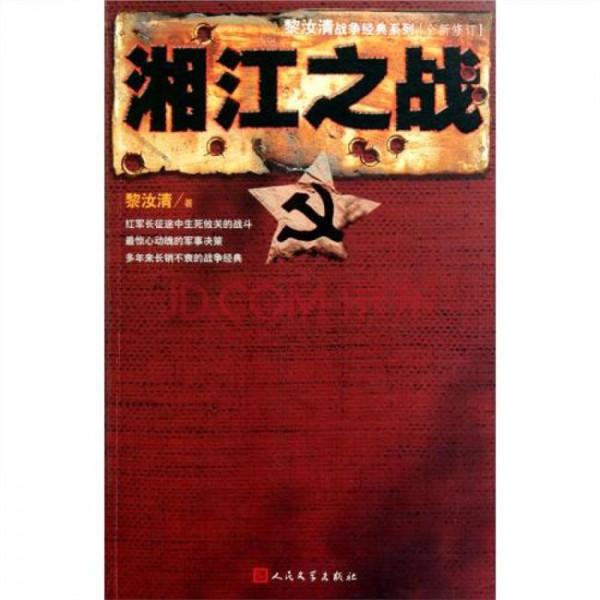黎汝清的资料 黎汝清的“命运启示录”
我遍搜网络,看到的的确只有报道黎汝清去世的短消息,和一篇很短的友人悼念的文章。
一代军事文学巨匠,中国党史、军史纪实小说第一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悲剧史诗作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黎汝清,只读过四年小学、半年私塾和三个月中学;17岁入伍,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过老山前线;在战争年代曾立过两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获得过三级解放勋章。
创作上,他有儿童文学、中篇小说、电影剧本,最重要的是有17部长篇小说——其中既包括“文革”期间妇孺皆知的《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也包括迄今无人能及的“战争悲剧三部曲”《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
他用17部长篇涵盖了中国革命史里所有的阶段,甚至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如果说,波谲云诡的中国革命史本身足以让所有的艺术门类黯然失色的话,那么黎汝清的作品至少为文学保留了一份发言权,甚至保留了一份尊严,不让历史彻底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人固有一死,历史和现实中也不乏轻如鸿毛者备极哀荣,重如泰山者黯然远去的例子。死本身和怎么被哀悼本身并不值得过分注意,然而,这样一个作家死之后,怎么被时间和历史记忆,却值得关注。
中国最著名的两部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和陈思和的文学史,对黎汝清的记录文字都屈指可数,尤其是对于真正奠定他文学地位的“战争悲剧三部曲”,几乎没有阐述。文学研究界对黎汝清的研究也是非常有限,迄今只有一部1983年出版的评论集,之后全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跟黎汝清的鸿篇巨制比起来,远不匹配。作家生前的情形已是如此,身后则可想而知。
好在,“面对稿纸,背对文坛”一直是黎汝清的志向,否则,以他的资历和成就,不知道要在军队和文坛如何呼风唤雨,知名度与今天相比也一定是另一番天地。他追求的是书比人活得更长久。
“两个”黎汝清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因而文学界最常发出的感叹,就是人有人的命运,书有书的命运。因缘际会之中,总有生正逢时和生不逢时的差别;也常有先走一步是烈士,晚走一步是英雄的感叹。尤其是建国后到“文革”结束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书和人的命运之变幻跌宕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点,只需要看一下建国后到“文革”结束期间的文艺界就可见一斑: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对胡适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再到1955年的胡风案、“丁陈反革命集团”、1962年批判小说《刘志丹》、1966年对遇罗克《出身论》的批判等等。
与此相对的,自然也有红极一时的作家和作品,比如赵树理,比如浩然,比如刘绍棠,其中也包括黎汝清。
1966年,黎汝清发表根据洞头女子民兵连的英雄事迹创作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全国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南京到北京,《海岛女民兵》”。之后小说被改编成各种剧种,尤其是1975年被改编为电影《海霞》之后,更是家喻户晓。
如今这部电影已经成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共同记忆。尽管拍摄的过程一波三折,但最终该片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最终与《创业》和《黑三角》一起,成为“文革”电影的三部曲。
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黎汝清又发表了描写我党我军建立根据地、坚定地走井冈山道路的长篇小说《万山红遍》(上下),还是写英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那个年代“高大全”“三突出”的痕迹,出版之后依然盛况空前,全国二十几家电台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联播。说黎汝清是那时候的当红作家,一点不为过。
但就是这个“文革”期间的当红作家,突然转型,在1987年出版了震惊文坛、也震惊了党史和军史界的《皖南事变》。之后,他顶着巨大的争议和压力,相继出版了关注我党我军历史上重大挫折的《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好评如潮。仿佛一夜之间,黎汝清从一个中规中矩、甚至有点遵命听命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敢于触碰雷区的、敢于“揭短揭丑”的作家。
如今看来,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神秘。在文学和生活、文学和历史、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处理上,黎汝清只不过遵循了更为禁得住时间检验的规律。他始终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让自己的创作远离生活实际,彻底变成图解政治的传声筒;也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历史观和现实观的局限直接转化成了创作上的困境,以至于脱离了特殊的时代背景之后就变得一筹莫展。
而且,因为他个人的气质和选择,他始终有意识地远离意识形态中心,远离权力,专注于文学和创作本身。当然,革命资历和军人身份也给了他远离这一切的便利。
黎汝清曾对记者如此回忆“文革”期间的状态——他说自己完全是“观潮派”,没有毒草可批也没有权位可夺,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参加任何学习班,而是到越南北方采访,到中央苏区深入生活,重走了一段长征路,《万山红遍》即是那时候积累素材的产物,以后的创作往我党历史上的悲剧转型也是萌芽于那个时期。
而且,无论是“文革”期间还是之后,他阐释自己的创作观时,始终不曾回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他说:创作固然应该写“生活就是这样”,但也应该写“生活应该怎样”,这是“我的理想主义”。
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这种“理想主义”,没有让黎汝清成为某一特定年代的作家,也没有让他成为只能作为“现象”传世而不能以作品传世的作家。当然,也因为这种“理想主义”,黎汝清能够始终被阅读。
《皖南事变》的价值
和黎汝清的命运转折
时至今日,阅读这部出版之后即获金钥匙奖的《皖南事变》仍旧能够带给人文学与历史的惊奇。
所谓“文学的惊奇”,首先是作家选择这个题材的勇气。当时的文学界,正在为现代派小说引进之后,重新发现小说的讲法而惊奇。尽管有些历史题材的先锋小说也被命名为“新历史”,但从作家的创作初衷而言,与其说是对重新发现历史、更新历史观的内容的兴奋,还不如说文学形式革新的快感来得更直接。
在“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爷爷”“我奶奶”(《红高粱》)的形式感召下,整个文坛认为坚持现实主义都是一种落伍的表现,(这一点,从《平凡的世界》在文学界的命途多舛,路遥被主流文学界忽视的郁结中也可以窥见一斑)更何况选择这种纪实小说的形式呢?
而且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党史和军史研究“宜粗不宜细”、注意研究分寸不要“抹黑”等已经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一部小说选择中国革命史上这样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敏感事件作为讲述的核心,必然要“细化”,甚至必然要触碰某种“禁区”,以黎汝清在部队的工作经历和创作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文学风险之巨大。
现实熄灭文学之火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作家在现实的缝隙中寻找到文学生机的能力也是非凡的。
读者获得“文学惊奇”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书本身了。《皖南事变》能够紧紧抓住读者对这个国共两党由合作抗日变得兵戎相见的事件“耳熟不能详”的心理,用人物,尤其是新四军的领导人的心理活动,引人进入历史现场:跟项英一起在中央的命令和个人的志向之间权衡;跟叶挺一起感受项英有形无形的冷落和轻慢,感受自己作为新四军军长有名无实的痛苦和纠结。
在这本书中,党的领导人第一次和普通的士兵、群众一样,褪去了天然的光环和英雄色彩,只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被作家平视、揣摩、理解,甚至审视。这本书第一次令人信服地塑造或者说呈现了项英和叶挺这两个我党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令人过目不忘。
书中写,在我党的历史上,项英曾经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一度比毛泽东同志高;他作为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曾受到斯大林的亲自接见,斯大林还以手枪和钢笔相赠;他曾经亲自处理过“富田事件”;他有过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经验,又用三年艰难缔造了新四军,因而他不愿意去江北,而是希望到国民党后方打游击。
《皖南事变》在深入研究这些党史资料的基础上,写项英的历史优越感,写他的家长式领导作风,写他和叶挺之间的矛盾,写他对北移的抵触,写他的拖延,写他最后的死于非命。
对于叶挺的描写也是如此。作者紧紧抓住他在《皖南被囚抒愤》中写的:“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同时也紧紧抓住他“两次出走”的历史史料,写他在新四军中的处境,写他与项英之间的矛盾,写他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特殊处境和特殊地位。
所谓“历史的惊奇”,就是作者通过这一本书,将一个史学界始终争论不休的问题讲得有血有肉、条分缕析。所谓小说以文学的真实保留了历史的肉身,即是如此。人物和事件、局部和全局、党派利益和家国矛盾、党性和人性、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等等,都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使得这场牵涉到9000人生命和热血的“同室操戈,千古奇冤”的大悲剧,第一次以完整清晰的面貌示人。
这种完整,不仅包括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外部原因,还包括党内矛盾纠葛和权力斗争的内部原因。仅仅这一点“文学的发现”,就足以使《皖南事变》在当代文坛占有不容置疑的一席之地。
然而,对于读者是“美学的和历史的”惊奇和惊喜,对于作家则是史识、史笔,尤其是史胆的考验。这种“史胆”不只是如前所述,敢于闯入云里雾里的党史军史,敢于试探雷区和禁区,敢于把党的领导人当作普通人来写这些方面,同时还包括敢于承担书写可能造成的全部后果——历史的、文学的,尤其是人事的。
事实上也是。《皖南事变》出版之后,一方面是文学读者的好评如潮,一方面则是史学界的质疑和争论,最厉害的则是很多直接和间接的当事人的“告状”。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那就是,一个作家不断自我突破,作品写得越来越好,甚至整个创作气质都发生了“破茧为蝶”般的改变,而读者也为之“惊艳”和欢呼的时候,其文学地位却越来越边缘,越来越被遗忘。到底是历史反思的戛然止步所致还是人事的力量太强大?还是勇于打破创作禁区的作家不配有好命运?
一位俄罗斯当代作家曾经说:“俄罗斯人不是历史变迁的牺牲品,而是不断变化的阐释的牺牲品。”而普列汉诺夫在回顾沙皇专制统治下血雨腥风的俄罗斯文坛的时候,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一切历史,自然包括文学史,都可称为一篇大坟场——其间,死者多于生者。”
好在,在思想解放的大时代环境中,在反思文学逐渐深入的文学氛围中,《皖南事变》经受住了考验,黎汝清也经受住了考验。而且,那个时候的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命运的吊诡之处。于是,他不仅没有止步于《皖南事变》,而且沿着书写我党我军历史上的悲壮篇章的路子,一走到底,相继又出版了《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
《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
这两部书,依然可以用“文学的和历史的惊奇”来概括。有了《皖南事变》的成功尝试,黎汝清驾驭起后两部来更加从容圆熟。同时,他对待历史的态度,尤其是文学把握历史的分寸,并没有因为《皖南事变》的争议而变得拘谨,相反,乘着当时思想解放的东风,乘着相关历史资料解密的东风(当时有关西路军的史料大量解密,以徐向前元帅出版回忆录为代表,大量当事人回忆自己的悲壮历程;而且黎汝清在建国后曾经走访过许多四方面军的首长),他更为理性,更为注重用史料本身说话,更注重人性深度的开掘,更注重史料之间和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也更注重深层次的探讨:比如湘江之战中的“抬轿子”问题;比如西路军的失败和抗战全局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的认识;比如西路军战术上的“以弱掩强”的问题等等。
因而,关于长征路上的“湘江之战”,关于西路军的悲壮历程,这两部书能够提供给读者的并没有更少,而是更多。
《湘江之战》中,红军在几次反围剿斗争中的英勇表现,长征路上不断变换的局势以及对路线选择的要求,党的领导集体中各自的革命履历和性格表现,乃至蒋介石和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等等,无不在以湘江一战为辐射点中被投射进来。
军事上这一场血流成河的悲壮抗争,折射着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面临的危难局势。《碧血黄沙》则将西路军的出征放在全国抗战的大局中,将他们路线变化的悲剧与全国局势未定联系起来,同时也将西北五马放更久远的历史中来看待他们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
两部书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了一场战役和一次远征本身,同时,两本书的悲剧气氛和悲壮精神,包括作家借由悲剧所进行的幽远的历史反思,都远远超过了失败本身,甚至远远超过了那段历史本身。
《湘江之战》的结尾,结束于1978年10月,结束于地下党员万世送经历过“文革”的九死一生之后,送别老战友何文干,重返起义旧地宁都;《碧血黄沙》则结尾于1984年对西路军战士的寻访……
《皖南事变》的结尾,战地记者白沙留给陈毅军长一封信,信中说:“历史是多面的,每个人只能用一双眼睛看世界,千秋功罪评说不一。阴谋拉开悲剧的序幕,性格才是悲剧的主角;在万古常新的悲剧人物身上,总能找到那个阿喀琉斯之踵。
”在黎汝清的书中,总能找到类似的议论。比如他在《湘江之战》中说:“生活中,人事关系大概是最复杂的,智莫难于知人。博古、李德、项英,在人事安排上花的时间和经历也最多。”在《碧血黄沙》中,他则说:“你是英雄,还要有命运之手把你放在英雄的底座上。”
在把握敏感历史题材的时候,黎汝清有两个法宝:一个是以人物性格和人性规律讲述事件的逻辑;第二个是善于驾驭放射式结构,以点带面,以人物带史料,注重在史料的相互联系和辩证统一中寻找事件的逻辑。
他反复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自己的创作立法,不断申明要“把历史的还给历史”。当然,这是他用文学的方式阐述自己的辩证唯物史观的方式:他一方面反思英雄创造历史和不能创造历史的必然和偶然,一方面也承认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也会扮演重要的历史角色(比如项英之死于忠诚的勤务兵之手等等)。
当然,他也用了足够的笔墨关注普通士兵在历史洪流中,尤其是历史悲剧的洪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选择三大悲剧,未尝不是为“无名的牺牲者立传”的考虑。自然,其中多少也包含着规避被误读的不得已的苦衷。
历史小说,在史传文学发达的中国历来争议颇多,因为围绕“真实”,围绕“真实的历史和讲述的历史”,其实有很多认识论上的疑难。涉及党史和军史小说,疑难更多,单单是党性和人性,就会让文学面临有可能无法逾越的高峰。
当然,如果一个作家生活积累和史料积累足够,如果一个作家拥有面对历史和剖析历史的能力,也愿意用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感选择这样的题材,那这些疑难就会变成挖也挖不尽的富矿。至于宽松的文学环境和合适的历史时机,或许永远不是靠想象和等待的,需要用有艺术说服力的作品来检验。
黎汝清会成为“被遗忘的大师”吗?
黎汝清一生创作了近一千万字,据他的家人和朋友回忆,他有“听一个故事就可以写一部小说”的才情,也有倚马可待的文思。而且,纵观他的全部创作履历,他从未囿于历史观的局限而放弃独立思考。
即便是在写《万山红遍》的1977年,他也还写了长篇小说《叶秋红》,在文学史上首次写红军内部斗争的残酷性,写领导权的争斗和路线斗争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同时期,他也有短篇小说《自白》,写党内优秀的党员被战友诬陷致死。
革命,是一个充满了艰难困苦的过程,这种艰难困苦,不只来自于敌人的强大,有时候也来自内部的消耗。这是黎汝清的革命历史观。应当说,在中国文学沉浸在“伤痕文学”的哀伤中的时候,黎汝清已经用自己的笔开始了反思之旅。他是文学的先行者。
之后,军旅文学才开始越走越远,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比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徐怀中的《西线无战事》、乔良的《灵旗》以及周梅森、朱苏进、莫言、刘震云的小说等等。考察文学史上1987年前后出现的所谓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潮流,有很大一部分是军旅文学,或者说跟战争文学有关。而这一切,其实跟黎汝清的探索和开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的“战争悲剧三部曲”至今都是党史小说不可逾越的高峰。多年之后,部队作家王树增和金一南的党史和军史的“非虚构”写作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按照黎汝清写《湘江之战》的时候说的,“95%的内容都是有史实可考的,可以当历史来读”的话,那时隔多年的“非虚构”文学只不过是纪实小说的另一个说法而已。应当说,黎汝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历史真实所赋予的充沛的文学性,无形中也为当下的历史写作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只是,他作为先行者,已经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了。
当然,即便是现在,党史和军史作家被专业评论“冷淡”的现象也存在,比如,与巨大的读者和媒体反响相比,对王树增和金一南的专业评价也并不多见。但愿这只是专业分工的盲区造成的问题,但愿后人在党史和军史面前的精神矮化问题能够得到相应的重视。
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大师的人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创造了新的讲故事的方式;另一种是打开了认识世界和认识人性的新窗口;还有一种是闯入了题材禁区,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而呈现了超越历史的普世的价值观。用这样的角度衡量,黎汝清称得上大师,只是,按目前的情况看,他可能会成为“被遗忘的大师”。
恩格斯说,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经济细节方面的所得比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那里得到的更多,因为,他用故事的方式保存了一种生活的真相。同样,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从黎汝清的小说中的所得也比党史专家的所得更多。
黎汝清用小说保存着一种历史的面貌,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现在,它都成为了人们借以全面了解那段历史的有效的、不可多得的途径。甚至可以这样假设,如果黎汝清的反思之路能够被足够重视和评价,能够有更多的追随者,那之后有关历史的创作恐怕不至于会走向“手撕鬼子”的地步。
有时候我会想,以黎汝清的创作资历和创作成果,以黎汝清的文学勇气和历史勇气,以黎汝清作为知识分子的“说真话”的勇敢和担当,以黎汝清上过战场的家国情怀,如果不是他身在部队,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某种奖项跻身于世界大作家的行列呢?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作家的命运更不容假设。
普希金在《纪念碑》中曾这样呼喊:“不,我不会死亡——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以此纪念黎汝清逝世近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