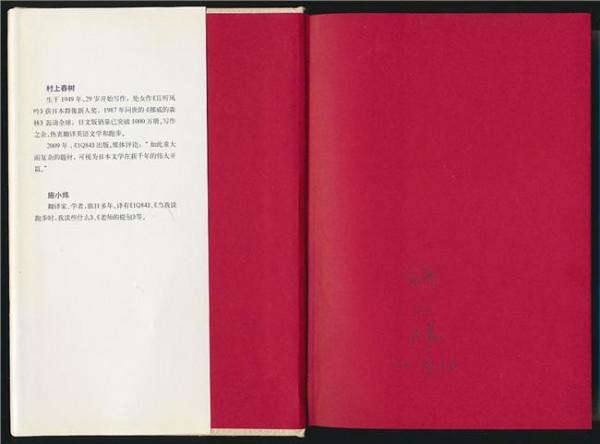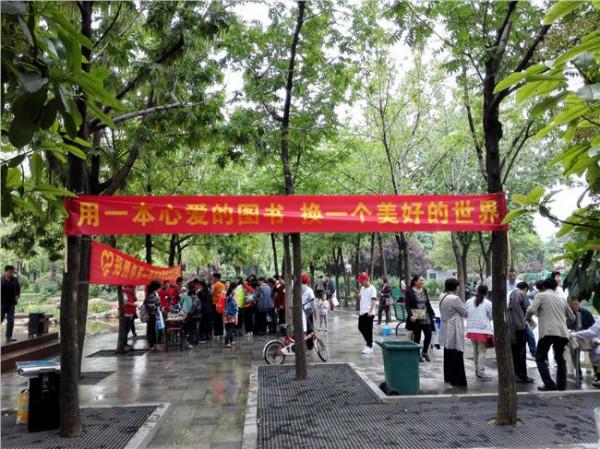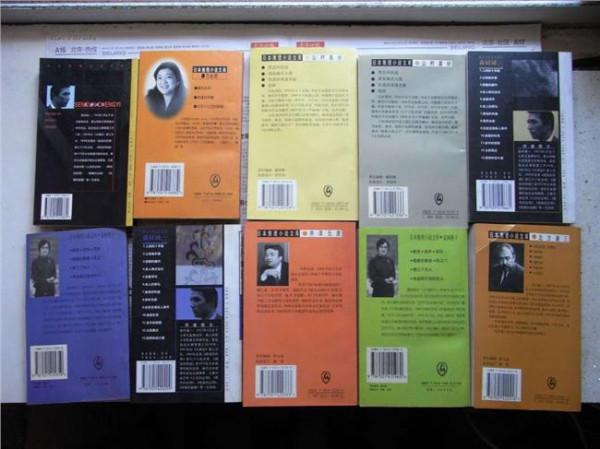止庵南方周末 义和团:当整个社会拒绝现实 止庵为什么写《神拳考》(南方周末)
在“耳听为实”的年代,义和团各种传说深得人心,人们只愿意听取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哪怕距离几条街,也没有人愿意去核实。直到北京城被攻破,义和团彻底失败时,大家还在传说义和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CFP/图) 止庵本打算写个“义和团神谱”,但发现没法写,因为神太多了。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其实意思就是,这个神不行,还有那个。
被人邀请演讲时,作家止庵经常建议:我讲讲义和团吧,特有意思。但很少有人对那段陈年旧事感兴趣。 对生于1959年的北京人止庵来说,义和团不过是两代人之前的事。他生活的城市里散落着义和团的隐秘。
上大学时的宿舍比邻义和团在北京的主战场西什库教堂,另一主战场东交民巷挨着他成年之后一度的工作单位。今天巍峨的前门楼子也是后修的:庚子年义和团一把大火烧了大栅栏一带的精华,慈禧回銮时,只得在前门楼子的废墟上临时搭上彩楼。
离开北京,义和团也会出其不意地跳进止庵的脑海。有一次走在巴黎街头,他突然想起了义和团乩文的句子:“大法国,心胆寒。” 2016年3月,《神拳考》出版,这是止庵关于义和团著作的最新修订版。
几次修订,学医出身、一点不相信怪力乱神的止庵慢慢觉得,隔着一百来年简单地笑话前人愚昧,太容易了。 止庵:我想看看,下到义和团团民,上到慈禧,他们中具体的一个人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些想法怎么汇总为整个社会的想法。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写部“人类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我觉得史家总是放过虚妄的一面,但现在看起来虚妄的,起初对当事人也许反倒是实在,而实在的可能要很久之后才能为我们所知道。
举个例子,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到印度河就停止了脚步,因当时欧洲人以为印度河是世界的尽头。后世谈到亚历山大东征,都强调此举将欧亚打通,让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其实亚历山大根本不知道这层意义。尽管他的动机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可笑。
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动机或思想,尽管不能用于其行为,却有助于理解。动机可以分成大动机和小动机。历史学家不是不关心大动机,他们甚至经常赋予当年人物这种动机。
史可法、张煌言的抗清曾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行为,后来历史学家对明清关系看法变了,爱国主义这一层就被弱化了。至于小动机,对历史学家往往没有意义。而我写的是一本关于小动机的书:具体到一个人,他为什么那么干。
南方周末:关心小动机是为了让历史叙事更丰富吗? 止庵:不忽视小动机,这样当年人物的举动才合情合理。其实我关心的主要是“合情”,合理的事是历史学家经常考虑的。但是合情才能合理。一个义和团的团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面对八国联军或清兵的枪口,对他个人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他把命都搭出去了。
他的确是在“反帝”,但这又不仅仅是“反帝”所能概括的。 南方周末:了解一个人做了什么事相对容易,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非常难。
止庵:义和团正盛的时候,礼部尚书启秀对慈禧说,“臣即义和团,幼时亦曾习练拳法”。而当义和团打西什库教堂打不下来,启秀建议:从山西请一位老和尚,肯定管用。老和尚提出需要庄王的马和一口大刀,然后选定时辰,老和尚骑马在前,后面跟着红灯照,再往后是义和团——这是当时笔记里的记载。
教堂里避难的人的日记也这么说:远远来了一个和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走近了,一枪将他击毙。于是后面跟着的人溃散了,红灯照的小女孩有被踩死的。
如果把第一件事理解为启秀的逢迎,第二件又怎么理解?如果他不真心相信义和团,没必要提具体建议,因为很容易得到验证。还可以结合另一件事来看:当年五月,有官员外放贵州主考,启秀对他说,“俟尔回京销差时,北京当无洋人踪迹矣。
”记载此事的作者说:“盖启秀真以义和团为可恃也。” 南方周末:看了七百多万字的史料,写了11万字的书。在史料选择上,你有什么考虑? 止庵:书里没有任何秘闻,我使用的都是1949年后公开印行的材料,只有一个当年的石印本。
在史料的甄别上,我依从历史学家,已经被他们证明是假的,如《景善日记》,我就不用了。再者,这本书使用的材料,无一处无来历。义和团这件事已经附会了后人太多的传说色彩,虚构与想象只能添乱。
我尽量把史料都给看了,再去看后人写的关于义和团的历史,两相比较,我发现我有一个写作的机会。荣孟源在《义和团史料》的序中说:“‘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
”我感兴趣的恰恰是: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 庚子年间,义和团一把大火烧毁了大栅栏一带,慈禧回銮时,只能在前门楼子的废墟临时搭上彩楼。(CFP/图) 南方周末:“神助拳”的前提是有神,神是怎么造起来的? 止庵:这方面的笔记,我抄了很多。
本打算写个“义和团神谱”,但发现这东西没法写,因为一人一神,太多了。“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这里面好像是有个神的系统,其实“一请”“二请”不是秩序,而是杂凑。这人心目中的神是黄汉升,他就成为黄汉升,那个人知道孙悟空,他就成为孙悟空。
人与他所成为的神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慈禧和光绪西逃途中接驾的怀来知县吴永,后来在《庚子西狩丛谈》里说,当时人民所受教育,不外乎小说与戏剧。陈独秀1918年所写《克林德碑》也说:“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津京奉戏剧特盛,所以义和拳格外容易流传。
义和拳神来之时,言语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这是当时京、津、奉的人亲眼所见。
” 义和团的“神谱”与太平天国不一样,太平天国的神到天父为止,但义和团的神可以不断地生成。按理说,孙悟空之上应该是如来佛,但义和团说,如来佛不行,我还有关公,关公不行,还有柳树精……所谓“一请”“二请”,其实就是这个不行还有那个。
南方周末:如果没有洋枪洋炮,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止庵:如果它不进入现实,它就是死循环,但义和团的法术是要应用的。人变成神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战斗。义和团的法术有一退一进两套——退可以“刀枪不入”,进可以将敌方的枪炮“闭住”。
这是一个看来非常周全的法术,一个人相信了,确实敢上战场。但一上战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时候解释系统就派上了用场:封不住枪口炮口或者做不到刀枪不入,那是因为对方有比我们的法术还厉害的法术,于是不断斗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再就是所有的挫折都是因为自己一方人不行,而法术没问题,于是不断换人——有义和团,更有红灯照,还有黑团、老团——这个解释系统可以按照义和团的神谱不断生成新的东西。
南方周末:可是这种生成也是有限度的。 止庵:很多与义和团相关的事情,当时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传闻尤其是讹传中发生的。历史学家在写这段历史时,往往忽略了这点。那是个“耳听为实”的时代,很多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都在传说中发生了。
他们听到的,都是自己希望发生的,对自己有利的;不希望的、对自己不利的都被屏蔽掉了。譬如:“愚民传说义和团法力甚大,不畏刀斧,能御枪炮,团中用一铜釜造饭,釜容米二升许,数千万人随取随满,永无尽竭,练拳三日,即可出战……每战但念咒,敌军枪炮皆不过火。
”直到北京城被攻破,义和团彻底失败的那一刻,大家还在传说义和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南方周末:注释里多次提到一个叫刘孟扬的天津人,他表达了很多怀疑。
止庵:传闻就是三人成虎,可能有第四个人说没有虎,但他的声音大家听不见。因为传闻体现的是普遍的愿望、社会化的信仰。 这种社会化的信仰,甚至会造成一种压迫感,不与之步调一致,就是非我族类,下场可能相当悲惨。
我在书中写了很多义和团的忌讳系统,都有赖于社会化信仰的压迫感。 色彩是义和团忌讳系统的重要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女性的态度。一方面,妇女经常被义和团认为冲撞了他们的法术,因为妇女代表污秽,要限制她们的行动范围。
另一方面,义和团又把取得胜利的希望放在妇女身上,所以就有了红灯照。参加红灯照的都是“十二三四岁未通经之闺女”——这些女人是“洁”的。
法术的成与败都可以归结到女性身上,这个解释系统其实特别简单,但也特别“圆”,大家都能接受,都能依从。 止庵: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论小说教育》,谈到庚子年间的事时说:“中上级社会的见识渐与下级接近,其重大性也极值得考虑。
”当时的中国,从团民,到一般读书人,到各层官员,到“当轴诸公”,再到慈禧,处事和思维方式其实是一样的。 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好像是半信半疑,但她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实际上回避了朝廷中个别人对义和团的法术到底是否灵验的追问。
而这实际上是关键所在。 大学士徐桐号称理学大师,怎么说也是有点学问的人,而且他家就住在东交民巷,那里就是战场,要验证真假应该非常容易。但他根本不去验证。
当时有个自称“微末小臣”的人,曾经给徐桐写过一封信,描述了自己认同义和团的心理过程:“初闻亦不信,逐日推求其理,考其行事,真有神奇不可解者。”这话的逻辑很有意思:承认“不可解”,也就是“解”了,“信”了,一切也就成为事实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读书人中应该有相当的代表性。
南方周末:书里还写到一个读书人,在北京城破的时候心如古井地读起书来。 止庵:他叫恽毓鼎。义和团兴起时他特别激动,认为“拳民必可成事”。
北京沦陷之后,他深居简出,引导自己进入一种奇特的心态中,并且为此自我陶醉。他说以前曾国藩剿贼,越是“濒于危”,心越镇定,“羽檄纷驰,不废吟诵”,所以我现在也要专心看书,定心养气。这种思维方式最后成了避难所。
还要提到李秉衡。1896年他是山东巡抚,因为镇压义和团不力,被外国人告了,朝廷任命他当四川总督,不降反升,外国人不干,改任长江巡阅使。八国联军要攻打北京,慈禧要封疆大吏来勤王,谁也不来,只有李秉衡遵命前来。
当时主剿、主抚的两派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他也高调表态:一切都交给我吧。他出师时带着的人包括义和团的八个大师兄,“手握八宝,曰阴阳瓶、雷火扇、引魂幡、飞剑、火牌、混天旗、九连套、如意钩”。
可是到战场他就服毒自杀了,写了一封遗书说“天下事从此不可问罪臣”——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忠臣的人格塑造,其他的事就不管了。大军临阵没了主帅,不战自溃。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事件中,从慈禧以下的当局主脑都是务虚的,或者说他们的“实”,其实都是虚的。
南方周末:义和团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像梦魇一样不断扩大不断膨胀,可是说停也就停了。 止庵:北京城破的那一刻,众人醒了。醒了之后,就把它扔了。
当然扔掉的只是形式,背后那个拒绝实证、违背逻辑的处事和思维方式并没有变。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讲了一件事,很有意思:“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
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当我们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评历史上的一些人或一些事时,我们其实是置身事外的;与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设身处地”的书。
然而在设身处地地体会时,我们未必觉得也要像当年人物那样做,或只能那样做,甚至应该那样做,反倒可能认定自己不会这样做。而不这样做就需要比他们在知识、思想、学问、修养等方面做些修正和补充,这也就涉及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