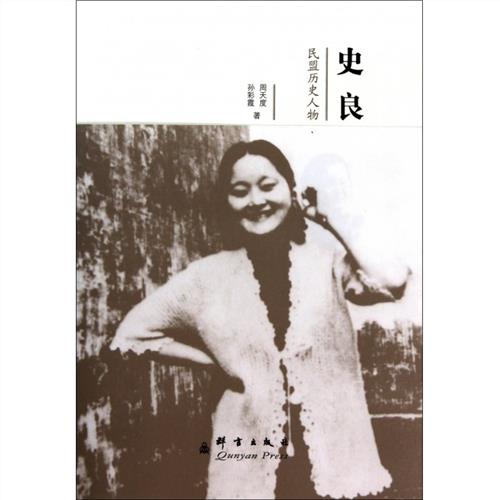心中的桃花源——梁衡评点中国历史人物
陶渊明为晋代柴桑人,即现在的江西九江县、星子县一带。九江我是去过的,这次为写这篇文章又重去两地寻找感觉。结果这感觉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在陶渊明纪念馆,我看到了许多历代、各地甚至还有国外对他的研究资料及出版的各种书刊。像东北鞍山都有陶学的研究团体,日本亦有专门的陶学社团。一本专刊上这样说:“渊明文学在日本的流传,不论时光如何流失,人们对他恬淡高洁的人格的憧憬,对其诗文的热爱从未中断。
”而更未想到的是陶渊明的墓是在一座部队的营房里,官兵们用平时节约下来的经费将其修葺保护得十分完好。我们登上营房后的小山,香樟、桂花、茶树等江南名木掩映着一座青石古墓。
墓的四角,四株合抱粗的油松皮红叶绿,直冲云霄。只看这树就知这墓在数百年之上。陶卒于乱世,其墓本无可考,元代时大水在这附近冲出一块记载陶事的石碑,官民喜而存之,因碑起墓,代代飨祭。现在这个墓是部队在2003年重修,并立碑记其事。
一个诗人,一个逝去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古人怎么会引起这么广泛、久远的共鸣呢?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确是以艺术的魅力激起了我们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和美好山水的不断追求。他设计出了一个人心理的最佳状态,这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永是平和自然,永葆一颗平常心。他以亲身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接着又用自己的作品定格、升华、传达了这种感觉。
他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埋下了一粒桃花源的种子,无论如何斗转星移,岁月更换,后人只要一读陶诗、陶文,就心生桃花,暖意融融,悠然自悟,妙不可言。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家应该具有诗人的思维,他说哲学最好的表达方式是诗歌。陶渊明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始终是用诗歌来表现人生的。
人生在世有三样东西绕不过去。一是谁能没有挫折坎坷;二是任你有多少辉煌也要消失,没有不散的宴席;三是人总要死去,总要离开这个世界。与这三样东西相对应的心境是灰心、失落与恐惧。怎样面对这个难题,克服人精神上的消极面,让每一天都过得快活一些,历来不知有多少思想家在做着不尽的探索。
过去关于奋斗、修养的书不知几多,现在“励志”类的书又满街满巷,而所谓“修养”,已经滑进了“厚黑”的死胡同。而你就是励志、奋斗、成就之后还是绕不开这三点。
你看现实生活中有的人生活并没有到了谷底,甚至还有几分殷实小康,但还在没完没了地嫉妒、哭穷、诉苦、牢骚;有的人已身居高位,还在贪婪、虚荣、邀功;有的人已退出官场,还在回头、恋权、恋名,苦心安排身后事。陶渊明官也做过,民也当过;富也富过,穷也穷过;也曾顺利,也曾坎坷,但这些毛病他一点也没有,他学儒、学道、学佛,而求静、求真、求我,从思想到实践较好地回答了人生修养这个难题。
陶渊明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民不聊生。他虽也做过几次官,但“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归隐回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为避战乱他曾两次逃难,仇家一把火又将他可怜的家产烧了个精光。但在他的诗文中却找不到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式的哀叹,反倒常是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
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回归,回归自然、回归自我,不为权、财、名、苦所累,永葆一颗平常心。他为官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丢人格;穷困时安贫知足,不发牢骚,不和自己过不去,也就是《桃花源记》里说的“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我们没有理由责备陶渊明为什么不像白居易那样去写《卖炭翁》,不像陆游那样去写“铁马秋风大散关”,不像辛弃疾那样“把栏杆拍遍”,陶所处的时代没有辛弃疾、岳飞那样尖锐的民族矛盾,他也未能像魏征、范仲淹那样身处高层政治的漩涡之中。
存在决定意识,各人有各人的历史定位。陶渊明的背景就是一个“乱”字,世乱如倾,政乱如粥,心乱如麻。他的贡献是于乱世、乱政、乱象之中在人的心灵深处开发出了一块恬静的心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一生大多身处逆境,但他却永是开朗。不是说这逆境不存在,而是他能精神变物质,逆来顺推,化烦躁为平和。他以太极手段,四两拨千斤,将愁苦从心头轻轻化去,让苦难不再发酵放大,或干脆就转而发酵为一坛美酒。
陶渊明也不是没有做过官,但他不把做官当饭吃,他一生五隐五出,那官场的生活只不过是他的人生实验。他对朝廷也曾有过一点忠心,甚至还有对晋王朝的眷恋。自晋亡后,他写诗就从不署新朝的年号。但是他把人格看得比政治要重,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看人的脸色。
政治生活一旦妨碍了他的人性自由,就宁可回家。他高唱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何等痛快。朱熹评陶渊明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他岂但只高于晋宋人物,也远高于现代许多跑官要官、贪财受贿、争权夺利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