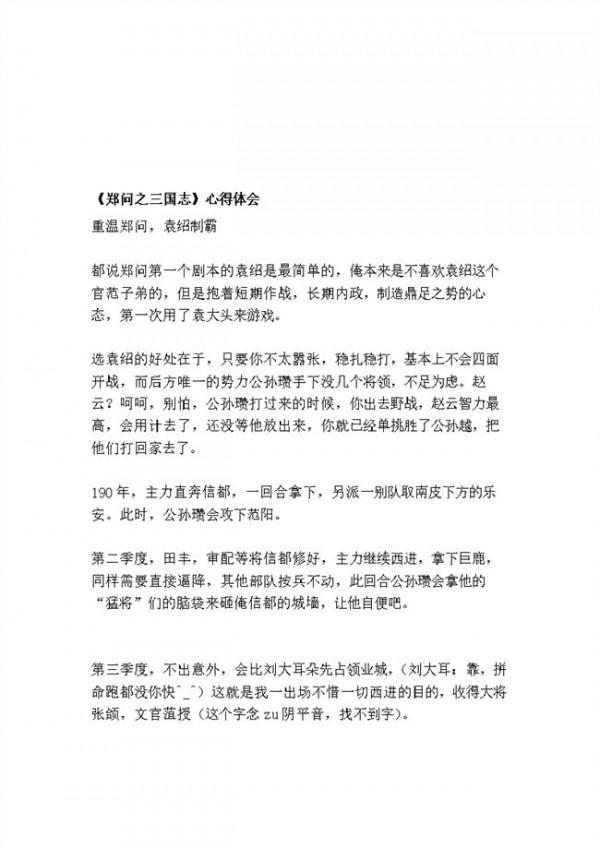郑问的儿子 潘道正 李进超:论康德的“丑的问题”(下)
崇高同美、丑之间的关系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我们不妨先从崇高同美之间关系谈起。古罗马作家朗吉努斯的《论崇高》(On sublime)是公认现存最早的相关文献,正是这篇文章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激起了人们对崇高的强烈兴趣,其深远的影响自不必多说。
朗吉努斯主要把崇高当作一种强大的文学风格,并视之为文学的至高标准,由此也奠定了崇高和美之间的密切关系。到了近代,这个传统为法国古典主义大师布瓦洛以及英国美学家夏夫兹博里、哈奇逊等人所继承。
然而,现代崇高范畴的奠基者埃德蒙·博克却极力强调崇高和美的差别。按照博克的观点,崇高和美之间有着“显著的对比,[……]它们的确是本质上非常不同的理念,一个见于痛苦,另一个见于愉快,虽然它们可能会因其直接原因的不同而有多种变化,但这些原因之间始终有着内在的区别,而且是那种能够影响激情、不会被任何人忽略的区别”(Burke113)。
按照博克的观点,崇高属于自我保护的激情,其源泉是恐怖,“任何能够激起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西,也即是说,无论何种恐怖,或恐怖的对象物,或以类似于恐怖的方式行为的东西,都是崇高的源泉”(Burke36)。
崇高的效果则是“震惊”;而美则被视为一种属于社会的“特性”,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爱”,“那种特性,或者说那些内在于身体的特性,能够产生爱,或某种类似的情感”(Burke83)。
这样,博克就在崇高和美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用后来的英国美学史家鲍桑葵的话说就是:“崇高同美之间的联系被博克完全斩断了”(Bosanquet203)。然而,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博克赋予了崇高全新的内涵,开创了现代崇高理念的传统。
鲍桑葵是朗吉努斯传统的坚定支持者,而比起对博克的尖锐批评,他更担心康德对崇高的传统的偏离。《美学史》中,鲍桑葵在评述德国哲学家罗森克兰兹的审丑理论时颇有些离题地写道:“崇高终于实实在在地被列为美的种类之一,这是对康德理论的巨大进步”(Bosanquet401)。
在鲍桑葵看来,康德像博克一样把崇高排除在了美之外,而且他对此显然一直无法释怀,直到罗森克兰兹把崇高重新纳入美的领域。然而,事实上,康德(至少在主观上)并没有把崇高排除在美之外。
恰恰相反,“崇高的分析”一开始,康德就先入为主地把崇高归于“审美判断”,并指出了崇高和美的两点“一致”:第一、“本身都是令人喜欢的”;第二、“都以反思性的判断为前提”(康德82-83)。
毫无疑问,这两点对崇高判断来说都是原则性的。当然,康德对两者的一致并没深入分析,一带而过之后就立即强调两者之间“引人注目的”“显著的区别”。按照看康德的分析,崇高和美至少有四点不同:一、美涉及的是对象的形式,而崇高涉及的是“形式的缺失”(absent of form)或者说“无形式”(formless);二、美同概念、理性无关,崇高则是“理性概念的表象”(康德82);三、美产生的愉悦是直接的、积极的,崇高带来的愉悦则是间接的、消极的;最后,“最重要的和内在的区别”是美在客体对象,崇高的根据却只在“我们心中”(康德83-84)。
这些为康德高度重视的“显著的区别”足以让人得出结论:崇高同美是完全不同的范畴。
那么,崇高和丑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朗吉努斯的崇高传统肯定没有丑的位置,但博克却把两者实实在在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我看来,丑同崇高的理念具有足够的一致性。”博克颇有总结意味地写道,“但是我绝不会说丑本身就是一个崇高的理念,除非它同能够激起强烈恐怖的那些特质结合在一起”(Burke108-09)。
尽管博克并没有把崇高和丑等同起来,但按照他的看法,崇高和丑似乎也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鲍桑葵就指出,博克虽然仍跟随在朗吉努斯及其现代追随者的后面,但他对崇高的论述极大地拓展了审美领域,结果是把丑也包括了进来,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康德,“博克就承认丑和崇高是部分地一致的。
这是极为重要的认可。他在崇高中发现的很多特性,如无形式、强力、巨大等,后来都被康德用于主体的探讨”(Bosanquet204)。
当然,康德同样跟随在朗吉努斯及其现代追随者的后面,而且至少在主观上没有把崇高同丑联系起来,因为在他的美学理论构架中,崇高被先在地置于审美判断之下——这是他进行“崇高的分析”的前提。
然而,在客观的分析中,他所谓的崇高判断同审丑判断却呈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甚至远过于博克的“部分地一致”。这也正是让鲍桑葵困扰的原因所在。
首先,崇高的根据无须外求,“只须在我们心中”。这是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中反复强调的要点,“必须被称之为崇高的,是由某种使反思判断力活动起来的表象所带来的精神情调,而不是那个客体”(康德89)。“真正的崇高必须只在判断者的内心中,而不是在自然客体中去寻求”(康德95)。
康德同时解释,人们之所以把崇高视为客体的特征,是因为内心中存在着“偷换”现象,“对自然中的崇高的情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的敬重,这种敬重我们通过某种偷换而向一个自然客体表示出来(用对于客体的敬重替换了对我们主体中人性理念的敬重),这就仿佛把我们认识能力的理性使命对于感性的最大能力的优越性向我们直观地呈现出来了”(康德96)。
康德如此重视崇高的主观特征,不仅仅是为了把崇高同美区别开来,更是对崇高的本质“很有必要的一个说明”,它同“发生在我们感觉中”的审丑是相同的。
其次,崇高判断需要理性的参与。这显然不符合康德对“审美判断”的定义,毕竟理性理念总是和概念结合在一起,而“判断之所以被叫作审美的,正是因为它的规定根据不是概念”(康德64)。但另一方面,崇高和美虽同在审美判断之下,但终究还是要有自己的“尺度”,对此康德说的很清楚:“激动,也就是在快意只是借助于瞬间的阻碍和接着而来的生命力的强烈涌流而被产生出来时的感觉,是根本不属于美的。
但崇高(它结合着一种激动的情感)则要求另一种不同于鉴赏以之为基础的尺度”(康德62)。
据此,崇高得有个“阻碍”的过程,同对美的直接欣赏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关键的问题是:“瞬间的阻碍”是如何解决的?“愉快感的唤起”又是如何可能?康德的解释是:“崇高的情感是由于想象力在对大小的审美估量中不适合通过理性来估量而产生的不愉快感,但同时又是一种愉快感,这种愉快感的唤起是由于,正是对最大感性能力的不适合性所作的这个判断,就对理性理念的追求对于我么毕竟是规律而言,又是与理性的理念协和一致的”(康德96)。
这儿,康德非常谨慎地引入了“理性理念”(审美理念的对立面),后来又说:“审美判断本身对于作为理念的来源的理性,也就是作为所有审美的东西在它面前都是小的这样一种智性统摄的来源的理性来说,便成了主观合目的性的了;而对象作为崇高就被以某种愉快来接受,这种愉快只有通过某种不愉快才是可能的”(康德99)。
按照康德的分析,“智性统摄”对于崇高判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而“智性统摄”能否实现显然取决于理性的参与,这同审丑判断的实现需要借助“理性的解释”并无二致。
第三,崇高判断是复合判断,其实现需要有个过程。这同样不符合康德美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康德始终强调“不愉快感”同时“又是一种愉快感”,两者是共存关系。然而,尽管人们似乎普遍能够接受“痛苦和快乐”“不愉快和愉快”并存的说法,但这并不能否定这种观点是矛盾且不现实的。
肯定和否定的结合,要么中和成中间状态,要么转化成程度不同的肯定或否定状态,但绝不可能产生奇怪的“肯、否定状态”。事实上,康德对崇高所作的客观分析也足以证明崇高判断必然是个过程,这在“力学的崇高”表现的尤其明显,“如果自然界要被我们从力学上评判为崇高的,”康德写道,“那么它就必须被表象为激起恐惧的(尽管反过来并不能说,凡是激起恐惧的对象在我们的审美判断中都会觉得是崇高的)。
因为在(无概念的)审美评判中,克服障碍的优势只是按照抵抗的大小来评判的。但现在,我们努力去抵抗的东西是一种灾难,如果我们感到我们的能力经受不住这一灾难,它就是一个恐惧的对象。
所以对于审美判断力来说,自然界只有当它被看作是恐惧的对象时,才被认为是强力,因而是力学的崇高”(康德99)。随恐惧而来的不愉快同灾难被克服后的愉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共存。康德随后所作的比喻更能说明问题:“由于放下一个重负而来的快意就是高兴。
但这种高兴因为从一个危险中摆脱出来,它就是一种带有永远不想再遭到这种危险的决心的高兴;甚至人们就连回想一下那种感觉也会不愿意,要说他会为此而自己去寻求这种机会,那就大错特错了”(康德100)。
要想获得“高兴”,就必须“放下重负”,“摆脱危险”,而非共时性地纠缠在一起,而这必然有个过程。首先,对象必须是令人恐惧的,唤起的是不愉快感,这其实就是丑的判断;随后借助理性理念,“克服障碍”,一方面认识到“感性能力的不适合性”;另一方面“心灵力量得到提升”,“揭示了一种胜过自然界的优越性”,愉快感由此被唤起。这就是崇高判断,但显然也是审丑判断。
结语
按照康德的说法,崇高的对象的首要特征是“无形式”,而在后来罗森克兰兹《丑的美学》中,无形式正是丑最基本的特征。其实,鲍桑葵早就说过:“康德关于崇高的论述[……]是把表面的丑引进美的领域的所有美学理论的真正先驱”(Bosanquet275)。
当代的研究者们显然也无法绕开康德崇高范畴的审丑之维。比如,涉及到无形式,格拉西克说:“崇高的判断是补偿无形式的一种方式。尽管康德从未具体述及,但我认为没有此种补偿发生的例子就被判定为丑的例子”(Gracyk52)。
也即是说崇高判断若没有实现的话就成了丑的判断,那么,如果实现了自然也可以叫做审丑的判断。汤姆森则困惑于康德崇高理论中“丑陋”“恐怖”“可敬”“崇高”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判断某物是可怖的,同时它又是可敬的?当可怖应该激发敬畏和崇高的情感时,又怎么能判定其不是丑陋?”(Thomson113)。
艾利森试图为康德辩护,认为“无形式”是“扩展意义上的形式”,也是一种“形式”,“否定鉴赏判断下的形式的缺失或无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尽管是令人不快的一种),既然它为反思提供质料。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丑等同于这种无形式,因为康德把崇高同后者联系在一起,他当然不希望把崇高视为一种丑”(Allison138)。艾利森敏锐地认识到康德主观上“不希望把崇高视为一种丑”,但以此断定“不能简单地把丑等同于这种无形式”就过于“想当然”了。
尽管康德的崇高判断同审丑判断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是不争的事实,但自朗吉努斯以来,把崇高纳入美之领域的传统(鲍桑葵就是坚定的拥护者)显然是太过强大了,以至于博克就算已经捅破了窗户纸、发现了崇高和丑的“一致性”,也还是不忘补充一句“绝不会说丑本身就是一个崇高的理念”。
影响到康德,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把崇高判断设定为一种审美判断。这不仅造成了他自己崇高理论中的诸多矛盾,更让后来的研究者困惑不已。然而,诚如鲍桑葵所言,美学在博克那儿就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崇高已经外在于美的领域(Bosanquet204),而经康德强有力的“分析”,崇高更是不能简单地被纳入美的领域了。
相反,自博克以来,崇高就越来越走向审丑。康德则事实上实现了两者的合一。因此,与其说崇高属于审美的一种形式,不如说崇高是审丑的一个范畴。
当我们揭示出康德美学中崇高判断和审丑判断之间的一致性后,康德的“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不妨先像麦康纳那样设问:康德可能会怎样分析丑?答案是:首先,“纯粹丑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因而不会有“丑的分析”;其次,纯粹审丑的判断是可能的,康德也作了简短的分析(§48),但是鉴于崇高判断和审丑的一致性,“丑的分析”的深入展开,不过是把“崇高的分析”再重复一遍,因此完全没有必要。
而像康德这样比任何哲学家都更在意细节的人,对此肯定心中有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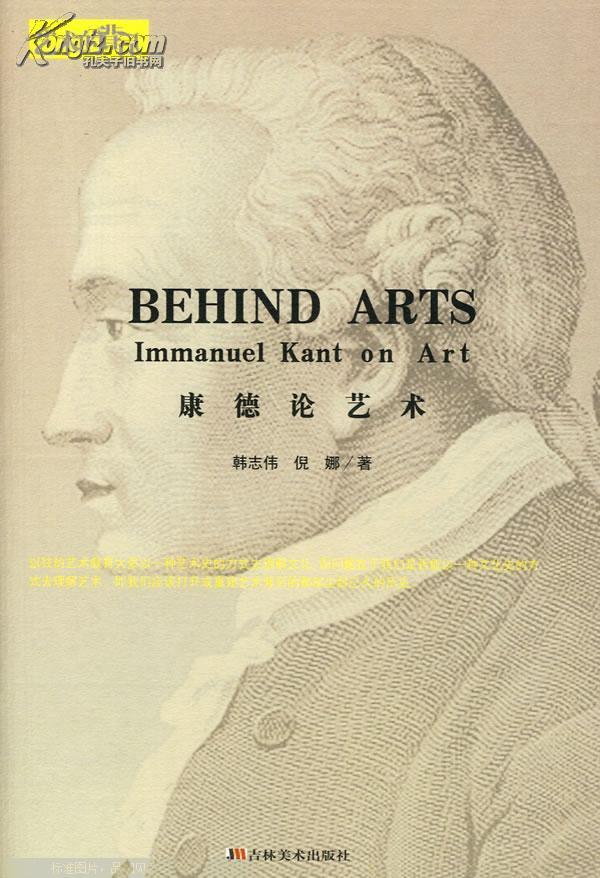









![郑裕彤的儿子郑家成 郑裕彤]郑裕彤儿子郑家成](https://pic.bilezu.com/upload/b/bc/bbca29550f789b713c04120266422168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