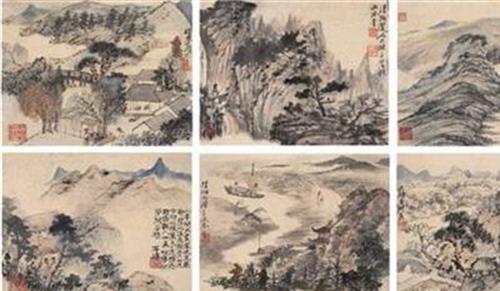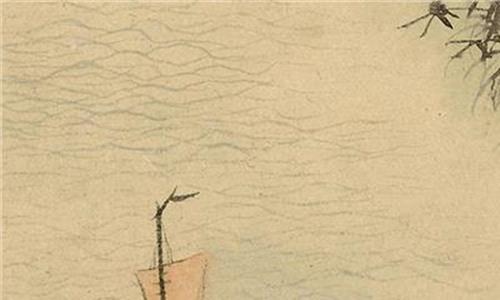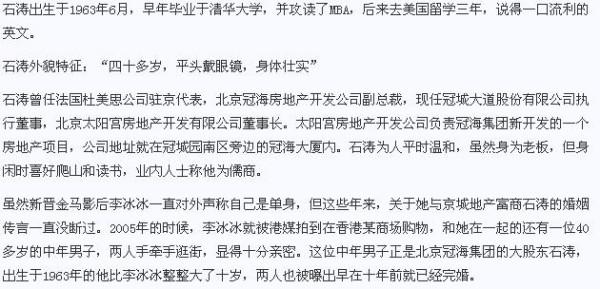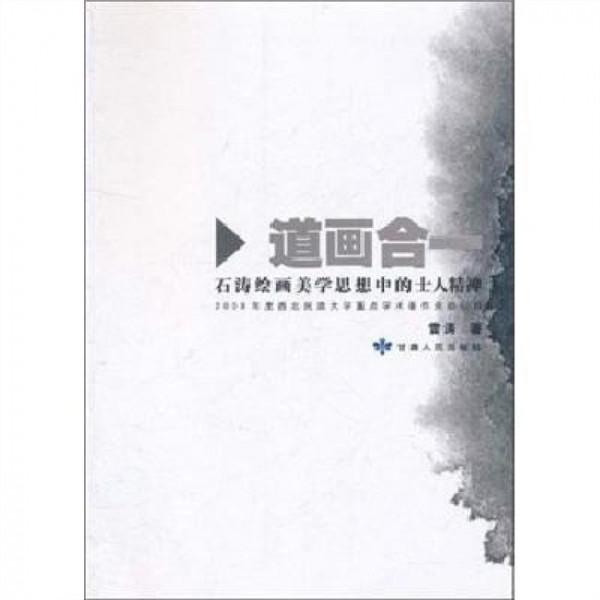石涛的画学思想 石涛和尚《画语录》的学佛思想
石涛和尚(1630—1707)①是中国画坛上的一位奇才,是中国画“黄山派”的创始人;因自幼出家为僧,对禅有极深的研究;他在文学、诗词等各方面也都有很高的造诣。
在禅学思想的影响下,他的画风独树一帜,笔墨恣肆纵横,超凡脱俗,不拘一格,意境苍莽新奇,为中国画的发展开创了一派新的意境。他的《画语录》极富佛学思想,“笔墨当随时代”、“我自用我法”的见解,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师法自然”建成就
石涛,明宗室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僧人,俗姓朱,名若极,法名超济,号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等。石涛起初“好聚古书,然不知读”。(清·李膦《大涤子传》)后经人指点,渐渐钻研藏书,并练习书法和绘画,包括山水、花卉、人物、翎毛。
1662年,石涛在松江拜名僧旅庵法师为师。旅庵法师为禅宗临济宗三十五代传人,精通禅理,擅诗、画。石涛耳濡目染,禅理与诗画均得以提高。
1666年(即康熙五年),石涛来到宣城。他以禅会友,以诗画会友,其中梅清、梅庚等新安派几个画家对石涛画艺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石涛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古代书画,并留下了一些师法古人画法的作品。1667年,石涛作《十六阿罗应真图卷》,这幅画据说画了一年才完成,是其进入禅门后的精心之作。
“(石涛)由越中之宣城。施愚山、吴晴岩、梅渊公、耦长诸名士一见奇之。时宣城有书画社,招人相与唱和。辟黄檗道场于敬亭之广教寺丽居焉。每自称为小乘客。是时年三十矣。”(清·李膦《大涤子传》)
应南京勤上人之邀,1680年石涛抵居南京,期间结识了戴本孝、程邃、王概、柳堉等画家。其中,戴本孝对石涛有较大影响。当时活跃在南京的是“金陵八家”,其中以他的成就为最。龚贤等人的某些技法或多或少都对石涛产生了影响。
1684年11月,清圣祖玄烨南巡,圣驾驻跸南京,曾至名刹长干寺巡幸。当时石涛正挂锡该寺,欣逢其会,即与长干寺僧众—-起恭迎接驾。5年后,康熙28年(1689),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康熙帝居然还当众呼出石涛之名。这两次召见,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后意气风发的情感。
1687年,石涛即作北上京师之行。期间,他曾几次往返于京津两地,结识了一些权贵、豪富人物,也结识了一些绘画上的知音。另外,当时统治整个画坛的正统派代表人物王原祁,对石涛的画也是认可的。他还在石涛为博尔都所绘的墨竹图中补上了坡石。而且多年后,王原祁赞誉石涛为江南画坛之翘楚,认为他自己和都不及石涛。
但是,石涛的绘画却被京师上层艺术界批评为“纵横习气”,生性耿直的石涛实在难以接受。于是,频频创作出他一生中的代表作品,如《搜尽奇峰图》卷、《古木垂阴图》轴,更在题识中发表了自己的绘画见解,指斥当时盛行于京师的仿古派画家。
石涛在遭到满清最高统治者和京师画坛的冷遇的同时,在出入达官贵戚府第之时,也见到了他们大量的书画收藏,临摹了古代画迹,受益匪浅。
石涛晚年,以卖画为生,作品相当丰富。《苦瓜和尚画语录》,则是其一生实践与求索的理论结晶。1707年7月,石涛画了《设色山水册》(书画十二帧),自此之后石涛画迹不再出现、
从石涛的一生来看,他曾经一度出家为僧,深研禅理,俨然一位禅师;从他的艺术成就来看,更是中国画史上一位不叮多得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表现手法富于变化,义能独特、和谐统一为自己的风格特色。他一生游历过广西、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自然界的山水赋予他深厚的绘画素养,在大自然的体验和探索中,加以对前人技法融会,因而他提出“师法自然”,把绘画创作和审美体系构成为“借笔墨以写天地而陶泳乎我也。
”研其画风,蕴含一种超凡脱俗的禅意。无疑,“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石涛绘画艺术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画语录》的佛学思想
《画语录》,又名《石涛画语录》、《苦瓜和尚画语录》,是石涛的画论专著;是以禅学思想为内核,提出的具有指导性的艺术见解的论著。通观全篇,贯穿了禅学思想。
石涛师从禅宗大师旅庵披剃出家,还曾以禅师的身份开堂说法,可见其参禅悟道之深。从石涛的大量传世作品和《画语录》中,大量佛学用语和参禅诗句的使用,可以看出他把禅意和艺术创作、本心自性和艺术内涵,做到了恰如其分的融合。
比如“一画之法”的提出,就是以佛法融通画法的具体运用,是文以载道的躬身实践和理论总结。“石涛画语录篇章不多,却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置之于历史长河,更是世界美术发展史上一颗冠顶明珠。”(吴贯中《我读石涛画语录》)下面就《画语录》的内容探讨石涛的佛学思想。
《画语录》共十八章。“一画章第一”云:“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
石涛所提出的“一画”,取自佛教的“佛性即一”、“不二之法”、“一真法界”,“佛性”即“本心自性”,“一画”即对其隐称,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是觉悟,悟道,即洞明意识之根源,“—”画之法”即以本心白性从事绘画艺术之法。石涛的师父旅庵本月禅师与玉琳通璘的一段对话。《五灯全书》卷七十三《本月传》记载道:
玉琳通璘曾问本师:“一字不加画,是什么字?”本月答曰:“文彩已彰。”璘颔之。
玉琳通璘的疑问是,当“一”字只在概念上存在而还没有出现形象的时候,它是什么字呢?旅庵本月的回答是,既然概念先于形象而存在,那么,即使形象没有出现,也要算做是“文彩已彰”了。它来源于《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七:
太尉举南阳唤侍者事,赵州云:“如空中书字,虽然不成,而文彩已彰。”
石涛所提出的“一画”,概受师尊的影响,从而运用到绘画之中。
“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这是立法的原则,从文中大义可知,“一画”指的应该不是一幅作品,按禅理来解释,应是明心见性。因为一切法不离心法,心能生万法。《法华经》云:“一法藏万法,万法藏于一法,万法即一法,一法通万法,万法在一法中、”经中所说的一,指的就是心。
所以石涛提出“一画之法”巾的——指的应是心。人若达到明心见性,即可达到一,其万法就在其中。然而达到心法的根本又在于缘起,缘起性空,方可见性。人若能达到见性,想得到石涛所说的“一画之法”那实在太容易了。因为此时的这个一,是随心所欲的一,此时这个法,是大智慧的法,所以在石涛的文中才引出“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的结论。
在“子法章第二”中,文说:“规矩者方圆之极则也,天地者规矩之运行也。”这里谈的是法,无规矩不成方圆,是事物存在的道理。这个理同宇宙之理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天地运行,是宇宙内在所具有的必然规律,这是宇宙的特性,也是的真理。
世上万物的存在与变化,都离不开宇宙的真理,若违背其理,则走向反面。人之役法于蒙,虽攘先天后天之法,终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为法障之也。”人因为不明白“法”所产生的道理,虽然立了法,却不明白此法所具有的本质,故很容易产生偏见,并执着于所知之法,反而使法成了障碍,无从改变,佛及禅理称之 。
尤在“氤氲章第七”中,石涛说:“画之理,笔之法,不过天地之质与饰也。“绘画的道理,用笔的方法,皆与宇宙的真理有关。故,质与饰的本质也都包含着天地之道理。“山川脱胎于予也,子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
唯识宗主张“心境相依”,这也是因为人具八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此八识,在唯识宗称之为心王。它们各自都能独立去缘境界,如,眼可观色,耳可听声,鼻可闻香等,故此心王为能缘,所缘境为所缘。
所缘之境与能缘之心息息相关,故,有心则有境,有境则有心。如此“心不孤起,托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显。”(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这就是心与境的关牙 石涛言:“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是以佛学唯识宗的理论阐明心与境的关系。
从石涛的文中可以得知,山川即是境,予即是“我心”,脱即是“缘起”。因此“山川脱胎于予”是境中有心,“予脱胎于山川”则为心中有境。所谓“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是“一画之法”的神来之笔的具体表现,即彻见本性之心,而达到心境交融之意境,故此方可终归于大涤,也就是归于“一心”,终将客境化为禅之意境。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石涛所用的“大”字是指得到大我之意,所用的“涤”字是“洗”之含义。
但是,他为何以此“涤”字代替“心”呢?这正是石涛用宇之玄妙,即,以此字表示一个经过洗涤,除掉妄念的无我之心。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同样是以心之能缘生境之所缘,或由境之所缘生心之能缘,而产生的对心与境的深层次的认识,否则就不可能见到石涛所指的,那些真正的心境相依的奇峰。
“脱俗章第十六”云:“遇者与俗同讥,愚不蒙则智,俗不贱则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今不能不达,不能不明。达则变,明则化。受事则无形,治形则无迹。运墨如已成,操墨如无为。”石涛认为愚与俗没有区别,愚即俗,俗即愚。
《六祖坛经》中有:“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作画可以师法前人,但仅仅是临摹还远远不够,还要有创新,有超越的思想。通达禅法,明觉“一画之法”即可达到变化。
若能以禅之大智慧,观看所要描绘的景物,这时已经不再是未开悟之前所看到的样子及感受了,如此下笔作画一定会改变其画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随之用墨也会产生变化,如同达到无我无为的境界。
“资任章第十八”云:“古之人寄与于笔墨,假道于山川,不化而应化,无为而有为。”古人作画只论笔与墨,将一切想要表现的形象,都寄托于笔与墨的运用。而不以禅悟之心求“一画之法”的理论宋研究艺术的表现。因此不得不受景或物的约束,即山是什么形象就画什么样,这样又怎能将其意境表现得深邃,故曰“假道于山川”。
执著于物体的表面,不深入理解物体存在着“质”的内在变化,以无变化之笔墨,描绘千变万化之山川,即“不化而应化”。以禅理来认识,以上均称“有为”之法,而不是“无为”之法,因而无法达到超凡的境界。
石涛《画语录》全文共计十八章,以上仅选了其中部分章节,并以佛学与禅学思想作了一些通俗的解析。
三、石涛与“杨州八怪”
自隋唐以来,扬州就以经济繁荣著称,虽经历代兵祸破坏,但由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总是很快恢复繁荣。进入清代,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呈繁荣景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重要贸易中心。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尤其以盐业兴盛,富甲东南。经济的繁荣,也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当时,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在艺术创作上,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无法而法”,宛如空谷足音,震动画坛。国画大师潘天寿评价清初几位大画家时说:“石溪开金陵,八大开江西,石涛开扬州。”是说石溪、八大、石涛分别是金陵画派、西江画派、扬州画派的奠基人和开创者。齐白石也高度评价石涛:“下笔谁教泣鬼神,二千余载只斯僧”。
清代以前,扬州虽然也属人文荟萃之邦,但在绘画方面,在华夏并无区域中心地位,但自石涛时代起,逐渐形成八怪新兴画派。他们不拘成法,将陈陈相因的陷人形式主义泥坑的传统文人画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扬州八怪”诸家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八大)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问”,不死守临摹古法。石涛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
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人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八怪”以石涛独抒胸臆、排募纵恣、不拘传统成法、敢于突破古人绳墨矩度的大无畏精神为师,在“四王”山水、南田花卉之外独树一帜,开出一块新的天地。
实际上,“八怪”中唯高翔与石涛有直接的接触。石涛比高翔年长48岁,但高翔在青少年之际就结识了这位“大江以南当推第一”的大画家。他们亦师亦友,情谊深厚。高翔绘画中所受石涛的影响,正如张庚《画征续录》中所称:“参以石涛之纵姿”。史载,石涛逝后高翔每年必扫其墓。
“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长于画兰竹菊石,偶亦写梅,笔法直接取法石涛。剪裁构图崇尚简洁,笔情纵逸,随意挥洒,苍劲豪迈。在其题画诗中曾多次提到画学石涛。如他在《兰竹石图》中题到:“近世陈古白、吾家所南先生,始以画兰称,又不工于竹。
惟清湘大涤子山水、花卉、人物、翎毛无不擅长,而兰竹尤绝妙冠时。清湘之意,深得兰竹情理,余故仿佛其意。”他在题跋中曾说:“石涛和尚客吾扬十年,见其兰幅极多,亦极妙。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
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慨叹“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一方面又说“不必全也”,这就叫用石涛的态度学习石涛,恰得石涛艺术态度之真髓。“八怪”诸人中,李鳏是相当高傲的一个。他曾经说:“八大山人长于用笔,而墨不及石涛。清湘大涤子用墨最佳,笔次之。笔与墨合作生动,妙在用水。余长于用水,而用墨用笔又不及二公,甚矣笔墨之难也。”。可见对石涛倍加推崇。
除了上述高翔、郑燮、李鳏外,其余各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石涛绘画风格的影响,如:汪士慎早年致力于山水,谓其“用笔傅色,似与石涛仿佛”;李坤工山水花卉;而喜作意笔人物的黄慎,则被人称为“笔意纵横排奡”;善于画鬼的罗聘,则被人称为“尤奇而不诡于正”;至于李方膺,《国朝画征录》的作者则干脆认为他的画作是“纵横排界,不守矩蠖”,其遣词用语,与对石涛的评价几无二致。
可见,“扬州八怪”诸家的出现,是在石涛艺术思想的影响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画家群体。他们建立的独特画风,石涛实际起了先导作用,可以说,没有石涛奠定的基础,扬州就不会产生扬州八怪,在艺术上、理论上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飞跃。
康熙四十六年,石涛阖然长逝,葬于蜀冈隆庆寺后,墓建在蜀冈平山堂后。石涛生前曾自画《墓门图》,并题“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广陵诗事》(清·阮元)载:“石涛和尚自画墓门图—一—诗人高西唐翔独敦友谊,年年为之扫墓酹酒。
闵廉风华有《题石涛墓门图》诗,云:‘可怜一石春前酒,剩有诗人过墓门’。”据旧志记载,墓有石碑。直到清末,当地文人清明时节尚有前来祭扫者。旅居台湾的扬州耆旧杜负翁先生在之石涛与扬州》一文中对此也有描述:
负翁于某年冬祭墓归时,乃从溪之小径,登临蜀冈。岂知石涛之墓,即在此处。墓前有一石碑,为泥土沾污,已不能辨识。高只二尺,甚狭小。经拂拭后,见其文曰:石涛上人之墓。此地在平山堂后围墙之外,地邻蜀冈中峰之背,虽在峰上,已近边缘。墓碑可能毁于民国年间。
1953年,大明寺建石涛和尚纪念塔于“谷林堂”后,包契常题写“石涛和尚纪念塔”。塔阴由李梅阁题文:“石涛和尚画,为清初大家,墓在乎山堂后,今已无考。爱补此塔,以志景仰。”“文化大革命”期间,纪念塔被毁。1993年,大明寺立石涛墓塔于栖灵塔侧,同时,立莲溪和尚、能勤法师、瑞祥法师墓塔于其附近。
秋雨连绵,在乎山堂后散步,但见秋草萧瑟,坟茔已不可寻。漫步在栖灵塔下,瞻仰石涛和尚的墓塔,仿佛感受到散落在周围的氤氲之气。生发之机,充斥天地,循环流动,如雾如烟。正是这股氤氲之气,孕育了后来的“八怪”,书写了一段“大写”的历史。
注:①石涛的生卒年代,傅抱石先生《石涛上人年谱》认定为1630—1707;郑拙庐先生《石涛系年》认定为1636—1707;《文物》1979年12期专文认定为1642—1707。新版《辞海》从《文物》说,列为1642一约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