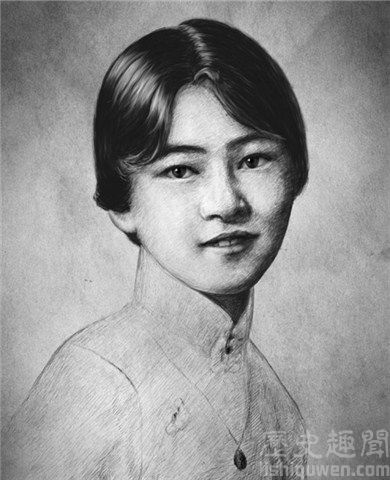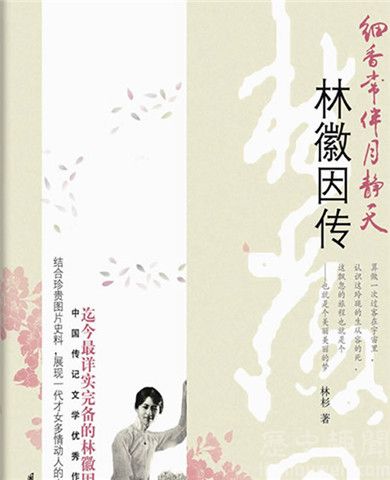林徽因:国徽的红色中也有我的一小滴血
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向北看,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庄严肃穆,照耀着国家的未来;向南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底座伫立在广场中心,托举着民族解放的历史。每天,数以万计的行人、车辆在它们的注视下川流而过。
这两件作品,都凝聚了林徽因的心血。
现在的文艺青年和影视作品热衷于把林徽因演绎成柔弱的美女、多情的才女,描述为“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干得好的‘五好女性’”,并津津乐道她的感情经历,好像她不曾经历国难家愁。
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她生于1904年,卒于1955年。短短51年间,祖国大地上外敌入侵、百姓流离、政局动乱,而她,始终与国人家人同甘苦、共患难。在战火中,她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潜心治学;在病痛中,她仍殚精竭虑培养人才;在任何危局中,她都坚守祖国。
这才是真正的林徽因:一位建筑师,一位坚忍忠诚的知识分子。
2014年是林徽因诞辰110周年。我们在她女儿、学生、亲友的讲述中,探寻林徽因真实的精神世界。
1937年夏天,山西五台山区荒凉、崎岖的路上,出现了几驾步履迟缓、颠簸不已的“骡轿”,上面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妻,33岁的林徽因和36岁的梁思成,还有他们的同事——“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的成员们。
这是林徽因第三次山西之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她曾在1924—1928年赴美学习美术和建筑学,24岁回国后与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27岁加入营造学社。他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时发现:框架式木结构是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形式,于是下决心要找到一处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然而,经过上千年的朝代更迭与战火,当时学者们了解的唐建筑实物只有砖塔结构,没有木结构。日本建筑学界甚至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这深深刺激了这对年轻夫妇。
他们从敦煌壁画中得到启示:唐代佛光寺或存在于五台山地区,于是便兴致勃勃地出发了。一路上,林徽因带着少女般的欢愉,心情激动,不时与丈夫热烈讨论。
尽管过去5年的野外考察不乏这样的经历——千辛万苦地跑了几百里路,结果只见到一片废墟,或是明清以后仿建的赝品,但这一次,他们依然充满期待。
走了两天崎岖山路和陡峻山崖后,他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一个名叫豆村的小山村。夕阳西下,他们惊喜地发现,前方一处殿宇沐浴着晚霞的余辉,气度恢弘,屹立于荒凉空寂的苍山中。佛光寺!它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林徽因、梁思成的眼前。
一行人的兴奋难以言表。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生前回忆说:“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与臭虫堆中摸索测量。”林徽因凭着一双远视眼,发现大梁下有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
“为了求得题字的全文,他们在梁下支起高架,清洗梁底尘垢,看出了一行‘功德主故左军中尉王’的字样,字体均是唐风。
字的意思表明:修建大殿的施主是一位宦官,官衔是左军中尉(由宦官出任,执掌唐代的中央禁军),姓王。”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张德沛回忆说,林徽因在佛光寺测绘时,与当地老百姓和教书先生相处极为融洽,“他们主动帮她拉皮尺、拓碑文”。
面对大殿角落中“女弟子宁公遇”庄严美丽的雕像,林徽因更生出一种崇敬的心情。“母亲说,她恨不得也为自己雕一尊像,让自己陪着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盘腿再坐上一千年!”梁从诫说。
测绘结束后,林徽因、梁思成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然而就在此时,数百里外的北平,卢沟桥上响起了枪声。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军队向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蓄谋已久的挑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和民族到了救亡图存的时刻,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考察不得不戛然而止,这次山西之行成为林徽因夫妇考察事业的最后一个高峰。
“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
匆匆赶回北平的梁氏夫妇,面对华北当局战和不定的暧昧态度,于7月16日和北平高校的26位教授、文化名人,联名致电正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军政要员。他们一致主张守土抗战,“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
当时,他们的女儿梁再冰正在北戴河同姑姑们一起度假,林徽因给她写了一封信:“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在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日军分三路进城。街头冷落了,胡同寂静了,政府部门开始撤离、疏散。林徽因和梁思成为防不测,连日清点、整理营造学社的研究资料。后来,为防止这些珍贵的资料落入日本人之手,他们将其存进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两人一面联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尽快收拾行李。他们被迫离开北平,但坚信自己必将回来。
当时,匆忙逃难的林徽因不会想到,1937年就这样成为一个分水岭,将她的人生截然分开。1937年之前的林徽因,是传说中的林徽因:出身名门、事业顺利、婚姻美满、儿女双全,可谓幸福生活的范本。1937年之后的林徽因,人生是不断的失去:疾病夺走了她的健康,战争让她流离失所、事业中断、失去至亲。但1937年之后的林徽因,才是真正的林徽因。
林徽因、梁思成和他们的朋友决定南下昆明,这段路程格外艰难。如今,许多当年的“南渡者”去世了,梁再冰已是一位85岁的老人。作为唯一健在的亲历者,她选择母亲生日当天——2014年6月10日,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了一家人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林徽因、梁思成带着5岁的梁从诫和林徽因的母亲何氏,赶到天津与8岁的梁再冰会合。此后两人扶老携幼,先从天津坐海轮到青岛,再坐火车经济南、徐州、郑州到汉口,靠摆渡船过长江到武昌,又坐火车去长沙。林徽因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
……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到长沙后不久,日本敌机的轰炸就来了。“有一次,事先没有警报,日本轰炸机就到了头顶上。爹爹以为是中国飞机,直到炮弹爆炸才急忙跑回房间把我抱起来。妈妈也立即抱起小弟,搀扶着外婆往楼下跑。当时整个楼房震动,到处都是碎玻璃。
当我们跑到楼梯拐角时,又一批炸弹落下,抱着孩子的妈妈在刹那间被震到了院子当中。后来我们跑到街上,听到飞机再次俯冲,那时毫无战争经验,竟然不知道卧倒,全家人都站在那里,幸好这批炸弹没有爆炸。”
长沙不能久留,从1937年11月下旬开始,一家人再次踏上旅程,取道贵阳去昆明,这是一段最艰苦的路。“湘黔一带都是高山峻岭,我们乘坐破旧的长途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妈妈、外婆、弟弟和我都晕车。”此时,梁再冰印象最深的是父母在困难的旅行中配合默契、应付自如。
“譬如打行李,两人合作,动作敏捷熟练,很快就能把一大包被褥枕头打成一个结实的铺盖卷,用油布包好防潮;在外吃饭准备好一小铁盒的酒精棉,将碗筷消毒后再吃。这显然是他们过去到野外考察古建筑时‘练’出来的本事。”
走到湖南和贵州交界处的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时,林徽因病倒了。感冒多日的她,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休息并发了肺炎,高烧至40度。“那时还没有抗生素类药物,肺炎是很难治的病症。”幸好同车人中有一位女医生,为林徽因开了中药方,林徽因服用后缓慢退烧,两周后烧才退尽。经过这场大病,林徽因的身体虚弱了许多,也为她后半生缠绵病榻埋下了祸根。
1938年初,一家人终于到达昆明。“父亲在昆明市郊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夯土墙盖了三间小屋。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虽然他们只住了半年。”梁从诫生前说。
有了立锥之地,林徽因显得愉悦起来,在写给美国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说:“这儿的阳光总是异常的明媚,天空昼夜湛蓝,云朵自在惬意地飘动。”据梁从诫回忆:“昆明这高原春城绮丽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
记得她曾写过几首诗来吟咏那‘荒唐的好风景’,一首题为《三月昆明》,可惜诗稿已经找不到了。还有两首:《茶铺》和《小楼》。”在昆明的3年,整个家庭得到短暂休整,梁思成也有机会在此前从未到过的四川和西康(民国时期旧省,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展开古建筑考察。
“日本真打进来,家门口就是扬子江 ”
1939年9月,希特勒在欧洲发动“闪电战”,不久就占领了大半个欧洲。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与希特勒结盟的日本很快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半岛”(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北部,轰炸中国西南变得容易了。
同营造学社关系密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等单位为了保护珍贵的资料和文物,决定迁往腹地四川。由于研究古建筑需要这些单位的资料支持,营造学社决定一起搬迁。
林徽因一家随之迁徙到四川宜宾的李庄,一个他们从未听说的长江南岸的小镇。这里气候阴冷潮湿,对患过肺病的人很不利。“我们到达李庄是在1940年的12月。1941年春节前,妈妈的肺结核症复发了。她的病症来得极为凶猛:连续几个星期高烧到40度不退,夜间盗汗不止。
当时爹爹正在重庆请求政府教育部资助营造学社的经费。李庄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也没有医院,没有体检的条件。当时没有肺病特效药,妈妈身边也没有任何医护人员,可怜的妈妈只能独自一人苦苦挣扎。我早上起床时,常看到她床前挂着十几条被汗浸湿了的毛巾。看到她病得一天比一天厉害,我那时真怕会失去妈妈。”梁再冰回忆说。
1941年4月,梁思成回到李庄。他没能给病重的林徽因带来药品,相反,他带来了噩耗——林徽因的三弟、空军飞行员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阵亡了。林徽因听闻这个消息,伤心欲绝。
除了亲弟弟以外,林徽因在抗日战争中还失去了其他飞行员“弟弟”。林徽因和梁思成曾在晃县邂逅一批前往昆明的空军航校学员,他们住在同一家旅馆。后来,他们把林徽因当作长姐,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到昆明后,林徽因和梁思成成了这些学员的“名义家长”。在李庄,林徽因陆续听到他们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梁从诫曾说:“不到两年,昆明那批空军朋友中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也是母亲最喜欢的一个,又在衡阳战役中被击落后失踪了。
他们的死在母亲精神上的反响,已不限于对亡故亲人和挚友的怀念感伤。她的悼亡诗《哭三弟恒》可以说不是只给三舅一个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的。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林徽因在这首诗中写道:“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1944年,12岁的梁从诫同林徽因谈起日军占领贵州都匀、直逼陪都重庆的危局,问母亲:“如果日本人真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林徽因答道:“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亲握着梁从诫的手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
”这是第一次,梁从诫觉得,自己温柔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别人”。
在李庄,一家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居住的房间以木板和竹篾抹泥为墙,梁柱被烟熏得漆黑,房顶上有竹制顶篷,老鼠和蛇常常出没其间,木床上的臭虫成群结队。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拿到钱后必须立即购买柴米油盐,否则便会“缩水”。
面对战时大后方的艰苦,梁思成、林徽因从未有丝毫彷徨。梁从诫曾回忆,“母亲这时爱读杜甫、陆游后期的诗词,这并非偶然”,她从中汲取着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爱国情操。
“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
在李庄的4年多时间,虽然生活困顿,重病缠身,但林徽因对未来始终保持着一种坚韧的信心:相信抗战必会胜利,相信中国建筑研究事业会继续。这种信念极大地帮助了她。在病床上,她开始读书。
“妈妈开始很认真地阅读《史记》与《汉书》等古籍并做笔记,为营造学社研究汉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建筑做文献准备,这是后来爹爹主持《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不可或缺的。”梁再冰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妈妈关注各个时代的建筑物和‘人’的关系,同时也进入了各种历史人物的世界”。
这一时期对营造学社而言,是苦苦挣扎却硕果累累的时期。梁再冰说:“在李庄如豆的灯光下,爹爹和妈妈整理出了他们多年古建筑研究的资料,后来成为中英文版本的《图像中国建筑史》,那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换来的。”
林徽因还付出极大的心血,同营造学社成员一起,协助梁思成恢复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两期汇刊出版过程十分艰苦,从石印刻版到印刷全是他们手工操作,装订的时候连外婆都参与了。”
1944年,梁思成在《汇刊》第七卷第一期发表了《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
类似的观点,林徽因早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时也公开表达过:“荷兰的砖瓦匠与英国的管道工,正在损害着中国的城市,充斥各个城市的是那些他们称之为新的时髦式住宅的滑稽而令人讨厌的范例。比如一座中国住宅被添上法国式的窗子,美国殖民地式的门廊和大量并不必要的英国式、德国式、意大利和西班牙式的装饰细部,这是对东方艺术的亵渎。”
正是对中国建筑的赤子之心,支撑着他们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说:“战后我们曾经在中国的西南重逢,他们都已经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我为我的朋友们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早就抛弃书本,另谋生存之道。”
“怎么写的没有你们看见的那么好”
抗战后期,他们就开始考虑战后人才培养的问题。1945年3月9日,梁思成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复员后的清华大学成立建筑系,梅贻琦接受了这个建议。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大西南。当时,梁思成和梁从诫在重庆,林徽因和女儿、母亲在李庄。一家人分隔两地,和亿万同胞共享这等待了8年的胜利喜悦。
一年后,1946年7月,一家人乘坐西南联合大学的包机,回到了北平这座受尽蹂躏的古都。梁从诫曾回忆:“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9年。当时他们都还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在北平复校的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建筑系,聘梁思成为系主任。
不久,梁思成应邀赴美讲学和考察。创办建筑系的工作实际上落在了系里聘请的第一位教师吴良镛以及林徽因身上。如果说战时,林徽因写出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把目光投向民宅修建,已经表现出对未来的前瞻,那么战后,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更是一件薪火相传的事。她躺在病床上,全力支持吴良镛的工作,从桌椅板凳的行政琐事,到排课授课的学术问题,事无巨细,出谋划策,确保9月份开学后建筑系第一班学生能正常上课。
清华大学教授朱自煊,是建筑系第一班学生,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林先生从1947年1月开始授课,讲住宅设计、装饰等。当时的建筑系设在水利馆二楼,台阶很高,生病的林先生根本上不去,我们就到她家里听她讲课。她不在系里挂名,完全是义务讲课。”
住宅设计在当时属于新课题,相关资料很少,林徽因对学生要求很严。学生茹竟华、王其明调查圆明园附近的营房,回来后向林徽因绘声绘色地描述:“在干涸的黄土地上零乱的村舍间,忽然出现一片绿树丛,穿过树丛,透过倒塌的围墙,看到一排排的四合院,进入里面,又有办公事的厅、小庙、水井、仓库、学校等设施。
那些突然出现的意外景象真有《桃花源记》中叙说的感受……”可两人写成论文初稿时,林徽因问:“怎么写的没有你们看见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