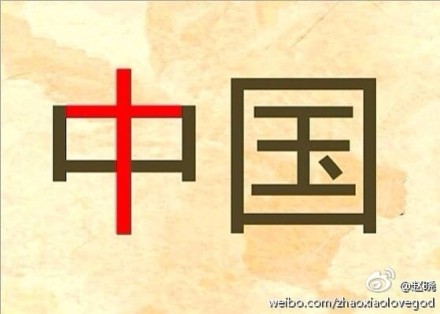赵林基督教 赵林:论基督教信仰之根基的内在化转变
近代科学理性对于传统基督教信仰的最沉重的打击在于,它摧毁了后者赖以建立的神迹基础,使得基督教教义和信条中的所有违背理性精神的东西都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如果说,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根据《圣经》的神圣性来重新解释基督教的教义和教仪,那么,18,世纪启蒙运动则根据理性原则对《圣经》本身的神圣性表示了怀疑,并且对基督教信仰赖以建立的神迹基础和形而上学理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但是拆除了基督教的神迹基础并不意味着消除了基督教本身,因为这个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悠久历史传统的宗教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根须重新置于人性的基础之中,这种人性的基础就是人的道德良知和情感需要。
因此,经历了启蒙运动之浩劫的基督教在日益强大的科学理性面前采取了回避退让和忍辱负重的姿态,它把自然界和知识论的领域留给了科学理性,而把人的道德世界和情感世界当作自己的最后避难所,从而实现了基督教信仰之根基从外在的神迹启示和形而上学知识论向内在的道德良知和情感体验的转化过程。
在这个信仰内在化的转变过程中,卢梭,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等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卢梭和康德对道德神学的确立
当义愤填膺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上帝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时,沉静而忧郁的卢梭却挺身而出,站在道德良心的立场上为上帝进行了辩护。卢梭虽然也属于启蒙思想家之列,也对专制制度的暴虐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伪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是他对待宗教基本问题的态度却与当时所有的启蒙思想家大相径庭。
这种宗教态度上的差异以及在一些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使得卢梭最终与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启蒙思想家分道扬镳,并且一直到死都与他们处于紧张而尖锐的对立之中。
卢梭在其坎坷一生中虽然因环境所迫而屡屡改变教派归属,但是在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上却是始终如一的,这些基本态度就是:承认上帝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信仰的根源是内心的虔诚,宗教生活的基础是道德和情感,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教派之间应该彼此宽容,等等。
卢梭倡导一种自然宗教,这种宗教既不同于自然神论和无神论,也不同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它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良知和自由心情之上的。卢梭既反对用天主教的天启、也反对用自然神论的理性来达到对上帝的认识,而强调以真挚的情感和向善之心来实现与上帝的沟通。
这种贬抑科学理性,崇尚道德情感的宗教思想,与当时法国知识精英中盛行的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是格格不入的,它构成了从英法的理性神学向德国的道德神学和浪漫主义神学过渡的重要契机。
1755,年葡萄牙的里斯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成千上万的人在地震中丧生。这件事对欧洲人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关于"我们的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信念以及英国诗人蒲伯在《人论》中所宣称的箴言"凡事皆属正义",遭到了普遍的怀疑。
伏尔泰就此发表了一首关于自然法则的诗篇,对上帝统辖世界和保卫人类的传统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在诗中暗含着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的思想。这首诗大大地激怒了卢梭,成为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正式决裂和反目成仇的导火索。
在1756年8月18,日针对此事而写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卢梭指责伏尔泰表面上信奉上帝,实际上却信仰魔鬼。他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位养尊处优的大哲学家企图借用这场灾难来扼杀人类的希望,"此种论调的荒谬尤其令人作呕"。
伏尔泰把一切事物都说成是邪恶的,并且斥责宗教观念,这种做法犹如在伤口上洒盐,只能使人痛上加痛。卢梭认为,关于上帝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是不能从理性的推理或形而上学的思辨中得出的,它植根于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
面对着伏尔泰所煽动起来的怀疑主义氛围,卢梭坚定不移地表达了自己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的信念:"形而上学的种种诡谲,片刻也无法诱使我怀疑自己灵魂的永存和精神的上帝;我感受它、坚信它,我向往它、期待它,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捍卫它。"[1]
宗教生活的根基在于道德良心和内在情感,而不在于知识理性,这是卢梭关于宗教的最基本的思想。这种宗教思想在卢梭的《爱弥儿》第四卷,信仰自白--一个萨瓦省的牧师述,(该文也是卢梭本人的"信仰宣言")中明确地得以阐发。
卢梭力图说明,信仰是完全奠立于个人真实的内心体验之中的,神学无非就是道德神学,"一颗正直的心,就是上帝的真正殿堂。"任何宗教教义和信念,都建立在人的道德良知之上;人与上帝的交往不是在外在性的宗教仪式中,甚至也不是在对《圣经》文字的理解中,而是在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中。
"一个人应去寻求上帝法度的地方,不是几页零散的纸张,而是人的心,在人心里,上帝的手屈尊写道:'人啊,不论你是什么人,都请你进入你自身之中,学会求教于你的良心和你的自然本能,这样你将会公正,善良而具有美德,你将在你的主人面前低首,并在永恒的福祉里分享他的天国。'"[2]
与艾克哈特等神秘主义者一样,卢梭始终坚信宗教生活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生活。一个有着真正的宗教信仰的人,应该因上帝爱善而诚心向善,因相信上帝的公正而毫无怨言地忍受痛苦。他在坎坷的命运中应该始终以欢乐的心情面对上帝,用真实的情感而不是理性的论证来领悟上帝的存在,通过对上帝所创造的秩序和自然法则的热爱来达到对上帝的体认。
卢梭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论证上帝存在时所使用的那套烦琐的形式逻辑,在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说明中具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
在《爱弥儿》中,卢梭强调,上帝就存在于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中,就存在于信者的心中。当我们执意要寻找上帝的确定形象时,当我们要追问上帝在什么地方或上帝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时候,上帝就避开了我们,但是他同时却在一切生命的和非生命的存在物中向我们显示他那无限的睿智,使我们坚定地相信他的存在。卢梭写道:
这个实体是存在着的,你看见它存在在什么地方?,你这样问我,不仅存在于旋转的天上,而且还存在在照射我们的太阳中,不仅在我自己的身上存在,而且在那只吃草的羊的身上,在那只飞翔的鸟儿的身上,在那块掉落的石头上,在风刮走的那片树叶上,都存在着。[3]
与伏尔泰等人的随机应变的自然神论不同,卢梭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坚定,明朗的态度,他的教派归属虽然游移不定,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过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的朋友圣朗拜尔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卢梭愤然地威胁要离席而去,他高声叫道:"Moi,Monsieur,je crois en Dieu!
(我吗,先生,我是信上帝的!),这信仰在他心中从来没有真正动摇过。上帝对于卢梭来说就是灵感的源泉,道德的砥柱,在他的长期的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中,上帝就像一个忠实的伴侣一样须臾不离地守护在他身边,鼓舞起他在逆境中孤军奋战的顽强意志和不泯希望。他在给一位贵妇人所写的信中说道:
啊,夫人!有时候我独处书斋,双手紧扣住眼睛,或是在夜色昏暗当中,我认为并没有上帝,但是望一望那边,太阳在升起,冲开笼罩大地的薄雾,显露出大自然的绚烂惊人的景色,这一霎时也从我的灵魂中驱散全部疑云,我重新找到我的信念我的上帝,和我对他的信仰,我赞美他,崇拜他,我在他面前匍匐低头。[4]
在卢梭看来,上帝是智慧,仁慈和美的化身,上帝的善良就体现在对秩序的爱中,他正是通过秩序来维持一切存在的。我们关于上帝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良知的直觉"从自然这本大书中获得的,从这本宏伟的著作中我们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
这种知识的获得既不需要矫揉造作的理性,也不需要超自然的天启。卢梭的这种自然宗教无疑是受了泛神论的影响,但是与泛神论把知识,理解当作信仰的基础的做法不同。卢梭始终把情感,良心当作信仰的首要条件,把宗教看作是属于心情的事情。
这种强调道德良知和真实情感的宗教观点对于西方近现代神学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康德在神学领域中所进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颠倒信仰与道德的传统关系,把道德确立为信仰的基础,从以神学来说明道德转向了以道德来说明神学,从以神来说明人转向了以人来说明神),以及施莱尔马赫把个人的心情,体验和感受确立为宗教信仰的基础,从而实现了宗教观从形而上学向心灵哲学的转化,这些变革活动都是在卢梭宗教思想的启发下进行的。
如果说卢梭在他的自然宗教中首先将宗教信仰的基础从外在的神迹启示转向了内在的道德情感,那么自认为是卢梭的忠实信徒的康德则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谨的思辨论证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前提,从而建立起一套精美的道德神学体系。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对自在之物与现象的划分,将自在之物或本体界驱逐出了认识的领域,使自然科学可以专注于经验世界而不受宗教神学的干扰,从而完成了自然神论的历史使命--将上帝(以及灵魂不死,意志自由等宗教主题)从自然界中彻底消除掉。
然而,这种现象与本体的二元论划分并没有把康德引向无神论,而是使他像卢梭一样将上帝存在的基础由外在的必然性世界转向了内在的自由世界,由自然领域转向了道德领域。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上帝作为本体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一副毫无内容的空皮囊,这个垂死挣扎的上帝被无情地抛弃到自然界的彼岸,如同荒冢中的磷火一般忽闪忽灭。
然而康德把上帝从自然领域中驱逐出去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彻底剥夺上帝的权威,而是为了把这种权威在更加牢靠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他在自然领域中一棍子把上帝打死,只是为了让上帝在精神领域中复活。
《纯粹理性批判》的最终宗旨并非摒除信仰,而是限制认识。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必须否定认识,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因此,当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完成了对认识范围的限制之后,他立即开始在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中重建信仰的基础,这个崭新的基础就是实践理性(即道德)。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从理论理性(认识)方面对以往各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进行了反驳;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又从实践理性(道德)方面说明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康德把上帝的存在当作实践理性的一个基本要求,宗教信仰是"对道德律之承诺的信任",这种承诺就是实践理性对"至善"的追求。
在现实世界中,道德与幸福处于彼此脱离的状态,二者的统一即"至善"--它是理性在实践方面的全部对象和最终目的--只有在彼岸世界中才可能达到,因此必须设置灵魂不死,意志自由和上帝存在作为"至善的可能性的必然条件"。关于上帝存在的道德根据,康德论证道:
只有在我们假设一个无上的自然原因具有与道德意向相契应的原因性的范围以内,然后世界上才会有至善存在。但是一个能够依照法则表象而行事的存在者就是一个灵物(Intelligenz)(有理性的存在者),而且这样一个存在者依这种法则表象而有的原因性就是他的意志。
因此,自然的无上原因,就其必须作为至善的先设条件而言,乃是凭着理智和意志而为自然之原因(因而也为其创造者),即神明的一个存在者。因此,我们一悬设了最高派生的善(极善世界)的可能性,同时也就悬设了一个最高原始的善(即神的存在)的现实性……因为这个至善是只有在神的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所以它就把有关这种存在的假设与义务不可分地结合起来,那就是说,假设神的存在,在道德上乃是必要的。
[5]
这样一来,上帝就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复活了,成为人类道德理想(至善)的最终保证。一个人可以在科学认识领域中对上帝漠不关心,但是在道德实践活动中他却不得不面对着上帝,上帝成为道德良心自我观照的一面明亮的镜鉴。这上帝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他的,而是他的道德本性的自觉要求。从而就使上帝从一种外在强制性的束缚,惩罚力量变成了一种内在自觉性的鞭策,激励力量,实际上已经将上帝等同于人的向善本性或道德良知。
从使宗教生活发生人性化和内在化转变的角度而言,康德堪称为18世纪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使人与上帝在信仰中合二为一,康德则使人与上帝在道德中合二为一。但是当我们把康德与马丁·路德相提并论时,切不可忘记康德的直接先驱是卢梭。
二、浪漫主义思潮与基督教信仰的情感根基
如果说康德使人与上帝在理性(实践理性)的道德生活中达到了统一,那么浪漫主义则使人与上帝在神秘的情感生活中达到了统一,而这股风靡欧洲的思想狂飙同样源于卢梭。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时代思潮,并不仅限于文学领域(尽管它主要表现在文学领域中),而是深深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这个概念的外延极其宽泛,它实际上包含了一切对现实状况怀有仇恨的思想倾向和行为方式。
浪漫主义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现实恨,而在,18,19,世纪这种现实恨首先就表现为理性恨。
因此浪漫主义在价值取向上或憧憬未来,或眷恋往昔,唯独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怨恨和愤懑;在表现形式上则以天真质朴的自然情感与日趋僵化和暴虐的启蒙理性相抗衡。
18世纪末叶的社会大动荡(法国大革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恋旧心理,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和拿破仑的强权政治迫使陷入失意和绝望状态中的人们在情感上纷纷转向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并且将朦胧追忆中的中世纪生活景象夸大为一种具有田园诗般恬美情调的理想境界。
夏多勃里安,斯太尔夫人等法国贵族流亡者和施莱格尔兄弟等德国浪漫派更是给逐渐远遁的中世纪生活增添了几分令人神往的美感,并且将这种理想化了的中世纪梦幻与南美洲原始粗犷的蛮荒莽林,德意志神秘莫测的古堡幽灵和传说中罗曼谛克的骑士遗风结合在一起,引发了人们无限的好奇心。
这种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而引发的恋旧情绪,再加上从卢梭那里沿袭下来的对纯净的大自然和真挚情感--它们恰恰构成了对污浊的社会现实和矫揉造作的古典主义的强烈反照--的赞美之情,以及一些思想超前者对科学理性的冷漠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弊端的敏锐感受和乌托邦式的(或"后现代"式的)批判,这一切滞后的和超前的反现实冲动和反理性倾向共同凝聚成了一股时代性的思想巨澜,这就是浪漫主义。
因此,在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既有"反动的"或保守的方面,也有"革命的"或激进的方面,既有夏多勃里安、施莱格尔兄弟这样忧郁多情的文化思乡者,也有拜伦、雨果这样桀傲不逊的传统反叛者,然而无论是保守的恋旧者,还是激进的超越者,双方所针对的目标都是同一个现实;它们的理想目标和价值取向尽管互不相同甚至背道而驰,但是它们所抨击的对象却是同样的,而且它们在形式上都具有明显的情绪化色彩。
因此,这场风靡欧洲的时代思潮可以形象地称之为一场反现实,反理性的情感运动。
任何一场剧烈的社会革命,在爆发之初往往都会以不可抗拒的情绪感染力使绝大多数人暂时地丧失理智,陷入疯狂般的热情漩涡中。然而当它在人们心中所点燃的激情的火焰燃烧殆尽之后,人们就会迅速地堕入一种百无聊赖的厌倦感中。
在1800年,从大革命时期的狂热情绪中冷却下来的法国人就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在政治热情骤减的情况下,宗教热情往往就会趁虚而入,使得对超现实世界的信仰成为经历了现实的磨难、遭受了现实的嘲弄从而对现实世界本身失去了信心的人们的唯一可靠的精神依托。
夏多勃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抒发了这种澈心透骨的厌倦情绪,他写道:"我除了宗教什么也不相信,要是我是一个牧羊人或是国君,我拿着牧羊棍或节杖会怎么办呢?我会对荣誉和天才工作和休息、幸运或不幸同样感到厌倦。
一切都使我厌烦。我整天痛苦地拖着疲乏的身子,打着呵欠把一生度过。"[6]这种由于政治理想的挫折而导致的对整个现实生活的厌倦心理,如同,17,世纪以来的一切时髦风气一样,从文雅的法兰西迅速地蔓延到整个欧洲,使得一切对现实状况不满的有教养的人们在思想上结成了一个庞大而松散的同盟。
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水平落后的德国,这种深切的现实恨更是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引起了具有深邃思想和忧郁气质的哲学家与诗人们的普遍响应。
近代的德国人虽然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不自由,但是却在精神中享有自由(这一点要归功于马丁·路德通过宗教改革而给德国人带来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尽管他们在实践领域里是一些怯懦的侏儒,但是在思想领域中却是顶天立地的巨人。
这种片面的精神自由使得德国成为近代唯心主义的滋生地和茁壮成长的沃土,而且使一切现实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一股形而上学的晦涩气息和唯灵主义的理想色彩。
因此,当法国人的带着忧郁的厌倦情绪的浪漫主义一传入德国,它就立即被深刻的德国人改造成为一种深沉的宗教理想,从而产生了德国式的基督教浪漫主义。这种德国式的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把对现实社会的深刻仇恨与对中世纪梦幻的痴迷眷恋交织在一起,将法国人的忧悒而漫不经心的孤独情绪,粗犷而炽烈的原始情感(这种情感典型地表现在夏多勃里安的小说《阿达拉》中)转变为对"中世纪月光朦胧的魔夜"的神秘领悟,转变为一种灵魂出窍的沉思、一种静穆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幽冥意境和一种崇高得令人热泪盈眶的宗教虔诚。
海涅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实质一语道破:
可是德国的浪漫派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7]
然而在浪漫主义温床中复苏的基督教信仰不再像以往那样奠基于抽象玄奥的神学和繁缛琐碎的仪文,而是置根于人的神秘直观和真实情感中。在把真切的情感体验确立为宗教信仰的基础这一点上,德国浪漫主义神学的思想巨擘施莱尔马赫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功绩。
这位浪漫主义阵营中最富于哲学思考的思想家,在他的《论宗教:对有教养的蔑视宗教者的讲话》一书中把宗教信仰建立在一种与旧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和康德神学的道德论全然不同的基础之上,这个新基础就是心灵对无限者的直接感受。
在他看来,以往关于上帝存在和性质的各种争论仅仅只涉及到宗教教义,而没有深入到宗教本身。施莱尔马赫认为人的精神生活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知觉,行动和感受。知觉导致认识,行动导致道德活动,感受则是宗教的独特根据。
他反复强调,宗教的本质只有在真切的神秘感受中才能领悟,与知识学无关。知识的量并不能增加虔诚的质,信仰的意义也不在于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虔诚不可能是对一大堆形而上学的和伦理学的残渣碎屑的本能渴求"。
宗教既不属于理论理性的范围,也不属于实践理性的范围,它的独特功能只是感受和直观。宗教生活的实质并非去进行那些冷冰冰的逻辑证明或做出种种形式化的善功,而是在对上帝的直观中实现灵魂的虔敬和升华,从而使"整个灵魂都消融在对无限者与永恒者的直接感受之中"。
施莱尔马赫进一步把"虔敬之自我同一的本质"定义为人对上帝的"绝对依赖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产生于个人的真实感受,而非产生于神学知识和道德规范。
针对谨守教义教规、奉《圣经》文字为宗教圭臬的新教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施莱尔马赫像马丁·路德一样再次把个人的心情、体验和感受确立为宗教信仰的基础。在他看来,宗教是属于心情的事情,真实的心情和体验一旦凝固为圣书和圣事的"纯粹的陵墓",宗教就丧失了自由灵感,不再是活生生的主观感受,而成为历史中的客观而僵化的纪念碑。
宗教的全部内容都活生生地流溢于个人的内在而神秘的直观感受和自由心情之中:
一个有宗教气质的人必然是一个沉思的人,他的感觉必然不断地在思索着自身。由于他整个的身心充满了最深奥最深沉的思想,他同时也放弃了一切外部的事物不论是有形的东西还是理智上的东西……因此十分自然的是,从古迄今,一切真正具有宗教性的人物都有一种神秘的气质……而且,一切富有想象力的性质,至少都有某些激发虔敬之情的东西。[8]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浪漫主义的激越奔放的想象力、神秘幽邃的冥思遐想与宗教的虔诚信仰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内在联系。
如果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用知识理性在自然领域中杀死了上帝、而康德又为死去了的上帝在人类道德领域中的复活提供了理论上的假设,那么施莱尔马赫则使这个上帝在个人的情感领域中获得了新生,成为自由心情的一个活生生的直观对象。
从此以后宗教真正成为个人的事情,成为自由心灵的真实感受。宗教信仰被归结于心理学,这种建立在切身体验和直观感受之上的主观主义宗教观成为基督教现代神学的重要基础。这种宗教观点认为,每个具有虔诚信仰的人只须对自己的活生生的心情负责,而无须服从种种外在性的权威和内在性的刻板律令。
对上帝的神秘体验和绝对依赖感成为宗教的唯一可靠的根基,心灵成为人与上帝交往的唯一场所。宗教不再关注形而上学和道德实践,上帝直接把充满爱情的目光投向人们内心的希望与失望、欢欣与郁悒、安恬与恐惧。
利文斯顿指出:自从施莱尔马赫把个人的内在体验确立为整个神学的出发点以后,"神学就不再感到必须在科学法庭或者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法庭之上为自己辩护了。
现在神学有了一种新的感觉,它可以在体验之中进行自我证明。……正是由于浪漫主义者们重新发现了上帝在自然界和历史中的内在性,才使得人们有可能再次对上帝产生一种更为深刻的切身体验。上帝不再被排斥在世界之外,遥远而不可企及,而是被体验为就呈现在日常生活的最为普通而平凡的事情中。"[9]这个直接呈现于个人的切身体验和日常生活中的上帝,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上帝。
当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现代性的内在基础被确立之后,它就真正地由一种外在强制性的思想枷锁变成了纯粹个人性的精神自由。从此之后,被道德神学和浪漫主义神学所复活了的上帝不再干预世俗事务,他只关怀人的灵魂归属。基督教在演完了它的漫长的历史悲喜剧之后重新回到了它的最初原则,从而使信仰再度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生活。
【注释】
[1]参见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5页。
[2]《卢梭通信全集》第3卷,第490封,转引自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3]卢梭《爱弥儿》下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91-392页。
[4]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33页。
[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8-129页。
[6]参见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7]亨利希·海涅《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8]施莱尔马赫《论宗教:对有教养的蔑视宗教者的讲话》纽约1958年版,第132-133页。
[9]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