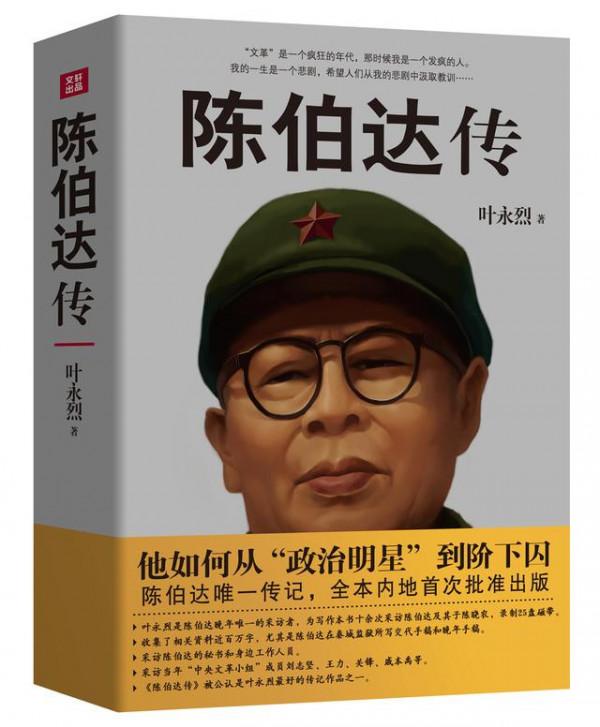父亲束星北的真情(上)
2005年,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一书在全国,尤其是在科技界和教育界引起了广泛关注。2007年10月1日是父亲束星北百年诞辰,国家海洋局联合父亲生前工作过的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举办了纪念大会,并出版了纪念文集——《胡杨之魂》、《束星北学术论文选集》,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先生题名的纪念光盘——《一个正直、勇敢、热爱祖国的科学家—— 束星北》。
纪念大会上,国内外学者踊跃发言。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先生将父亲的人格比作“胡杨”:“胡杨一样百折不屈的铮铮傲骨,一样永不言败的顽强精神,一样万劫不叹的人格韧性。
”展现了父亲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以及强国之梦,也表达着父亲的友人、学生和晚辈们对他深切的怀念、不尽的哀思和由衷的景仰。
在参与《纪念文集》和《论文选集》资料的搜集过程中,我曾分别到上海、北京等地,拜访过99岁的中科院院士谈家桢先生和104岁的贝时璋先生。尽管他们年事已高,但头脑清醒。当谈到父亲,特别谈到抗战期间在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湄潭与父亲相处的日子时,他们显得格外兴奋和激动。
更可贵的是谈老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父亲的纪念文集题词:“傲骨一身 求是精神”,并委托友人在父亲的纪念大会上发言。我在搜集父亲论文的过程中发现,父亲论文发表的时间非常集中,一个时间段是1931年至1934年父亲在国外工作期间;一个时间段是1945年至1946年即浙江大学西迁湄潭时,这是父亲一生中工作分量最重的,其中包括在国际一流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的两篇论文;另一个时间段是解放后1951年至1955年有关气象等方面的文章。
之后二十多年没有见父亲的论文。再以后则是父亲晚年复出步入海洋领域后了。而1956年肃反运动后高教部和科学出版社分别与父亲约的稿《电磁学》和《狭义相对论》,都是父亲在被批斗与劳动之余完成,故当时无法出版。
《狭义相对论》则是在父亲去世多年以后才出版。当我读了1979年父亲写的一首诗后,则完全能理解这个情况了:“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态龙钟始于春,愿得中华民族振,敢辞羸弱握黄昏。
”从年少时期漫长的出国求学之路,到“九一八”事变后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辞职回国,抗日战争期间随浙江大学一路西迁;胜利后返回杭州时,父亲已年过不惑,可谓半生流浪。
解放后父亲被戴上“反革命”、“极右”两顶帽子,缘由分别是因为1944年抗战期间被国民党军令部借调并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雷达,以及反右运动时“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的宣言。
这虽使他吃尽苦头,至今却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应该更准确说这两顶帽子应是父亲人生的两大亮点。而父亲的所有学术成果,则是在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夹缝中产生的。在参加“上海浙江大学校友会纪念束星北诞辰100周年大会”时,原副会长杨竹亭先生对我讲,束星北代表着他们心中知识分子应有的形象:是既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忠、孝、义”,又渗透着“民主法制”精神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搜集资料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父亲的过程。
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们基本上都已八十岁以上,有的人在写完稿件不久便离开人世,有的人则是在住院抢救后写下的稿件,篇篇文字都表达着他们对历史与科学的尊重。本着这种精神,我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出,以便后人对这一代老科学家们的理想和品质有更深层的理解,给中国的科学史和教育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资料,也算是有一种使命吧!
父亲的家世 我手头有一张摄于1924年的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搜集到的父亲最早的照片。摄影师是著名的电影演员赵丹的父亲,为庆贺我父亲的祖母束曹氏90岁生日而拍的。
右起第八人穿西服的高个子为父亲,那年他17岁,刚考入杭州之江大学。 我的祖父束曰璐,江南陆师学校优等毕业。清末曾任参领,辛亥后引退,民国任全国水利局主事,后为张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在南通也有自己的企业。
祖父有两房太太,我的祖母郭氏为大,她身材高大,性格豪爽,嗓门大脾气急。生有两子。父亲为长,叔叔束佺保。 我的祖父为人非常豪爽、热心,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
表伯父严仲简(原上海纺织工学院的教授)在世时曾对我讲,在他九岁时,他们的母亲(我祖父的亲姐姐)便去世了,祖父便一直抚养着他们弟兄两人,送他们上了南通纺织学校(据说是中国第一个纺织学校),以后又送他们弟兄出国留学。
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第一代纺织人才。所以严伯伯经常教育他的子女说,要永远感谢我祖父。因祖母的陪嫁田产均在江都,她常年带着两个儿子住江都大桥老宅,管理祖产滩地水田。
祖母的田全部佃给农民。她常到田头看庄稼,发现有人不尽责,从不留情,当面责骂,但若是碰到灾年,她不但减租,而且捐资募化,赈济衣食。农户们对祖母是既惧畏又敬重。父亲曾给我讲过,他小时候非常顽皮,因此几乎每天都要挨祖母的打。
祖母常对他说:“你要有那一天不挨打,我就给你搭台戏。”有一天从早上开始,父亲便小心翼翼地表现,终于熬到晚上没有挨打,于是他死缠着祖母,非要让她给自己搭台戏。祖母说以后再给他搭,他死活不干,最后还是以挨了一顿打而告终。
父亲非常孝顺我祖父母,尤其是对祖母。1941年我祖父母相继去世,父亲曾两次从时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返回上海奔丧,并将他两个尚未成年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带回贵州我家,与我们兄弟姐妹同吃住,担当起责任。
我叔叔日后曾流着泪对我们说起:“讲起我们是兄弟,其实我们像父子。” 我们生活中的父亲 我们弟兄姐妹共七人,我最小,上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据三哥和四哥讲,抗战胜利后我们家从重庆返回杭州,他们俩一个8岁上小学三年级,一个6岁上二年级,因语言不通,一年下来杭州话不会讲几句,功课也听不懂,但骂人话却学了不少。
这天因为要留级,不敢告诉父母,但回到家后听说母亲生了个妹妹,看到父亲开心大笑的样子,于是他们两人一下子冲进了家门,一个人抱住父亲的一条腿,说:“爸爸,我们留级了!
”。父亲大度地说:“留就留吧!再上一年就是了!”也就是在父母亲40岁时,有了我这个小女儿。
当我有记忆后的第一件事,在我五岁时的一天,(正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听父亲说厦门大学卢嘉锡先生和山东大学的华岗校长同时都邀请他去。他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让他往南走,不要往北走,说往北走祸大于福。
但父亲笑着对我们说:“我听算命先生的话,但朝着他说的相反的方向走。”于是父亲便到了山东大学。后来又有一个自称会拆字的人对父亲说,你不该到山东来,山东的“东”字(指繁体字)是在你姓“束”的“束”字心里横插了一把刀。
父亲却仍然不以为然。结果在山东他蒙冤受屈二十余年。 仍在山东,党和人民最终又还给他了公正。1952年我们家从杭州到青岛时,父母起先只将我们最小的三个孩子带来了。大哥那时已参军到锦州当飞行员去了,姐姐和二哥、三哥仍留在杭州上中学。
母亲说,我们家离开杭州时,只是人来了,其他什么都没带,连冰箱也撂在了杭州,父亲都不要了。也许因为多年的战乱逃难太多,习惯于抬腿就走。在来青岛的火车上,我和小哥兴奋地满车厢乱跑。
突然,不知为何我腰以下的半个身子一下子漏到车厢底下。低头一看,下面是飞驰的火车轮子和轨道,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正巧旁边一个列车员,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将我拉了上来。原来是车厢门口楼梯上的铁盖不知为何一踩跷起来了。
当列车员将我送到父母身边时,父亲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一再说:“太谢谢你了,你救了我女儿的命就等于救了我的命啊!”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炽烈的亲情。事后父亲开玩笑地说,这是他“往北走”给他的第一个“下马威”。
其实所谓的“往北走”或“往南走”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种巧合而已。据父亲的研究生、老地下党员、原浙江大学副校长李文铸先生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谈到,刚解放在浙江大学时,就曾有人以父亲在国民党军令部工作过为由,将父亲列入镇反名单。
但在浙江大学里有一批了解父亲的共产党员学生们,由于他们的据理力争,才使父亲能够得到保护。 在家中对待我们兄妹的教育问题上,父亲的态度向来是非常宽松的。
很少过问我们的学习,从不强求我们要考多少分数。偶尔我们向父亲讨教不解的功课,总感到父亲二三句的解答,就全明白了。父亲常对我说,学习要多动脑子想。一看就会的作业,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做,要做似会不会的,或干脆不会的。
所以我在青岛二中上学期间经常不完成作业。一开始老师还批评我,后来发现我的成绩很不错,也就不管我了。 1966年高中毕业时遇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在山东聊城三线工厂当了近十年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报了名,父亲听说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只有两行字:“既然你决定了要高考,就考吧。记住,会做的题先做,不会做的最后做。” 困境中的岁月 父亲心境豁达,虽常处逆境,也从未放弃过对国家的爱和对真理执着的追求。
1955年10月13日父亲曾给青岛市委写过信: “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员会: 我曾于7月28号、8月6号两次奉上材料,请予参考。自8月13号山大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束星北’大会已有两个月。
我向学校借的图书已被全部收回,我主持的气象研究室已被封锁,一切科学研究工作全部被迫停顿…… 对我个人来讲,我薪水照拿,而且我深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迟早总要去掉的,我并不着急,不过因此耽误了科学研究的进行实是一件不易补偿的损失,尤其气象研究室职员全停顿下来,无事可做对国家也是损失……” 我曾采访了当年同我父亲一起在气象研究室工作的王彬华教授,尽管他年已95岁高龄,但一提起气象研究室,他就精神抖擞地说,1954年在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有气象研究室,而且是在竺可桢先生和涂长望先生的直接支持和领导下的。
以父亲的数理功底,再加上王先生他们夫妇二人丰富的实践经验,那段时期,父亲几乎是一月一篇论文,他们的合作是他们三人气象研究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可惜研究室只持续了一年多就中断了,我父亲的论文也就中断了。 文革前父亲总觉得自己没有错,他坚信自己是爱国、爱人民的,即使给党提意见也是出于本性,是为了党好。
用他自己的原话说:“你让人提意见,如果认为不对,不听就是了。”所以后来的检查,几乎是在大哥的强迫下才写的。因此好多年我甚至都有点恨我大哥当时的做法。大哥复员回家前,尽管父亲已经挨斗了,但我们家的气氛从来都很温暖。
自他回来后,家中经常有他和父亲的吵架声。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便对大哥说:“我恨你,你回来后整天同爸爸吵架。”结果大哥的一番话,把我说得愣住了。他说:“如果我不强迫爸爸写检查,他再犟下去,恐怕要被逮捕,弄不好还会被打死的。
”我一想也是啊,如果不是父亲的“犟”,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打成反革命极右分子。1957年,他在山东省委宣传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后,用母亲的气话说,是他“逼”得人家把他打成反革命极右分子的。
因为这次发言所造成的影响太大了,据载,发言中曾二十多次被掌声打断,因此事后也使得一大批人受牵连。例如老红军、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明也是因为对别人宣传:“看,束星北的发言讲得多好啊!
”这也成为他反右中的一条罪状,其实他和父亲根本没有任何私人交往。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看到那么多的开国元勋都受到了冲击,尤其是看到罗瑞卿跳楼后摔断了腿,仍被用筐抬出来批斗时,大为感慨地说,比起他们,我那点委屈又算什么。
记得有一天,我看见他剪了一个平头回家了,就问他原因。他指着脑袋说:“明天批斗张立文(当时青岛医学院的党委书记),让我陪斗,这样他们(指造反派)就揪不住我的头发了。
”第二天,他一回到家,我和妈妈非常关心地围上去安慰,谁知,他却非常轻松地对我们说:“批斗时,我在台上‘坐飞机’,都差一点要睡着了!”还有一次,看见他回家时身上挂了一块“反革命极右分子束星北”的大牌子时,我的眼泪马上掉下来了。
谁知,父亲却安慰我说:“哭什么,认识我的人反正知道我是束星北,不认识我的人,反正不知道束星北是谁。”在青医刷厕所时,有一天他很神秘地对我说:“我发现,刷厕所是一个好活。
”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刷完厕所后,躲在里面看书,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扰你!” 1971年底,父亲跟随青岛医学院到了山东的北镇,因我即将分娩,母亲就到聊城来照顾我。但我们都非常不放心父亲独自在北镇,因那时他毕竟已经64岁了,而且又有哮喘。
但每次父亲来信总是说:“北镇如何如何的好”,“什么黄河刀鱼是多么的便宜”(因父亲是江苏人,特别喜欢吃两合水的鱼)。还经常来信说:“北镇的羊真便宜,7元钱就能买一只,天天可以吃大米。
”总之,他来信总是让我们放心,即使在最困难时,他往往也是用一两句调侃的话让我们开怀大笑,使全家沉重的心情一下子变轻松起来。自从1931年父亲回国结婚后,我的母亲就一直默默地陪伴在他的身旁,尤其是在父亲最艰难困苦时,是母亲给了他最大的安慰和支撑。
充实而俭朴的晚年 1978年,父亲调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他已完全顾不上考虑个人的冤案平反问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来不及了!
”他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已71岁高龄的他,他个人即使再拼命努力,要想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他刚到海洋一所就给自己定位为“作人梯”,他把“追赶”的希望寄托于后人。在海洋一所领导的支持下,他成立了28人的“物理海洋进修班”,分秒必争地投身于他所热爱的科学教育工作。
他经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是:“你们趁我身体好时,多学点东西,不要分心,不要以后后悔。”经常对我讲的一句话也是:“可惜我的脑子里的知识不能遗传给你,把它们带进坟墓去见马克思,就太可惜了。
” 记得1980年左右,一天在半山坡学习班的教室里,他的一个学生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太满意,正在发牢骚,父亲走进来听见后就说:“你们不要动不动就发牢骚,而且发牢骚也是没有用的。
邓小平能把一个走下坡的中国扭转过来开始走上坡了,就非常不容易了,让你当主席,你该怎么办?你能一下子把中国变富吗?”那个学生回答说:“让我当主席,我就请卡特来当总理。
”父亲听后非常生气,说:“我不要你这样的学生”,说完就离开了教室。当时我在场,回家后就对父亲说:“他说的是不对,爸爸你事后怎么批评他都不要紧,但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幸亏现在不搞运动了,否则他的前程可能从此就完蛋了。
爸爸你不也就因为几句话,而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吗?”听后父亲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感叹地说:“你们年轻人没有在国外呆过,光感觉国外好,但你们不了解,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大,国人是多么受气啊!
当年在美国,有一个黑人见了我都骂‘黄狗’,他骂我,我可以和他对打。但是有一次,到一个饭馆里去吃饭,桌上坐了一个白人,我在他旁边坐下后,他抬起屁股就走了,表现出不屑于和你中国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那时受到的屈辱,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超过白种人,为中国人争光!”这就是父亲为什么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默默作为他一生座右铭的缘故。 父亲一生中,不管是在顺境或逆境中,他对生活上的要求是极其简单的,平时吃饭,只要一荤一素。
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你做多了菜,我也分不出味道来,只要营养够就行了,不要浪费了。”穿衣服,只要保暖,从不求样式。到海洋一所后,我找人替他做了一件呢子中山装,总觉得他有时出席正式场合,别穿的太随便。
谁知,他一点不买账,对我说:“你这叫花钱出力不讨好,我这是花钱受罪别人看!”让我哭笑不得。直到有一天,突然刮大风,降温了,父亲感到有点冷,这时,我便拿出了那件呢中山装来,给他套上了。
他才说了一句:“哦,看来它还挺挡风的啊!” 如果一个不认识父亲的人在马路上碰见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同一个科学家联系在一起。父亲有个习惯,只要是天气好,常拿着个小马扎,到研究所旁的小山坡上坐坐,考虑问题。
有一天,一个老大爷在山上碰见父亲,兴致勃勃地同父亲聊天,谈起他儿子是部队雷达连连长时,老大爷充满了自豪。父亲在一旁微笑着很虔诚地听。近一个小时后,大爷突然打住,问了父亲一声:“大爷,你识字吧?”父亲赶紧地点了点头,真诚地回答说:“多少识两个吧!
”1982年所里给父亲买了一台“PC-1500”微型计算机,比书本略大一点,可用Basic语言编程,也可打印和画图。
父亲爱不释手,立即着手看说明书学习,两三天他就会用了。因为计算速度较慢,算题时间很长,所以睡觉时就把它放在枕头边,父亲说,听到它打印的声音心里就高兴。编程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有时就问我。
一次我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一个大教授来问我这么个小助工,不掉架吗?”父亲一本正经地说:“掉什么架?不懂不掉架,不懂装懂才掉架。” 父亲晚年从不存钱,月底一看工资还有节余,他总要让我们陪他出去买东西。
然后送给这个,送给那个。有时我不理解,就问他:“你不会存一些下来吗?”他说,他不会留给子女任何财产的。并说正因为他的父亲太有钱了,所以他的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除去老九束炎南外都没大出息,而他的堂兄束剑南(南通张謇的亲外孙)更是:“少时靠父母,老来靠儿女。”父亲又给我们举例,讲正因为以色列的自然资源最贫乏,所以以色列人才开发了人类最大的资源—— 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