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随笔 林贤治《人文随笔》民间立场
林贤治选择了散文与随笔体裁,而谢绝了论文体裁,这也意味着,他选择了批判精神而非专业精神,选择了民间立场而非学院立场。由此,正可见林贤治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期许:他不愿是知识界中人,而愿是精神界中人;他不做专业的知识分子,而要做不专业的知识分子。
民间立场与批判精神
鲁迅将杂文打造成批判现实的武器,林贤治则将散文编排为自由精神的舞蹈。
林贤治在《世界散文丛编·总序》中说:“散文并非王国,乃颇类联邦共和国;在每一块疆土之上,弥漫着同一种共和的空气:人类的自由精神。”
这一观念,不仅表现在他的个人写作方面,也贯穿在他的图书编辑方面。与邵燕祥合作主编《散文与人》(三联书店),自己主编的《读书之旅》(广东教育出版社),与筱敏最新合作主编《人文随笔》(花城出版社),林贤治其道一以贯之:以散文或随笔为体裁,以人与自由为主题,有思想的批判,有人文的关怀,回溯历史,指向当下。
此外,他主编的丛书“流亡者译丛”(花城出版社)、“曼陀罗译丛”及“曼陀罗文丛”(作家出版社),也属同一种文化思路。
人文关怀《人文随笔》已刊三辑,第一辑“春之卷”可能准备更充分,内容似更为可观。以下仅据个人视角,对第一辑内容评点二三事,略见其编辑旨趣之一斑。
狄马的《乞丐、垃圾以及多数人的暴政》是很有现实批判力度的一篇。
作者以美国法律个案为参照,质问西安市“清理乞丐”行动的合法性,并借用“多数暴政”的政治学理念,对相关报道中“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的现象作出阐释:“如果以我们刚刚过去的世纪为例,那么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几乎每一场血腥的‘运动’到来时,人民群众都会‘拍手称快’……可后来为‘胡风分子’平反,为‘右派’平反,为‘刘、邓’等‘走资派’平反时他们还是‘拍手称快’……因而可以说,人民,从来都是刽子手和行刑队的啦啦队员,他们的最大愿望不是在阳光下消除暴力,而是在行刑的现场蘸拾人血馒头,至少要听到一两声悦耳的‘嚓!
嚓!’声,这使得暴力失去了起码的见证。”这个历史总结可谓鞭辟入里。不过,为何我们的执法者和旁观者都潜意识地不将乞丐视做合法公民?作者将此归因于传统,也即归罪于古典的中国文化,我则以为未免舍近求远、厚诬古人了。——试看陶渊明将佣工转给儿子时,给儿子去函道:“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别把佣人不当人,这不明明是爱无等差的胸襟吗?谁说古代中国就没有平等博爱呢?
钱满素的《纳粹女人的献身精神》,则从群众心理学立场,剖析“纳粹女人”大义凛然地为法西斯殉葬的行为:“……在伟大高尚的名义下——不管是奉献给‘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女人,还是在‘圣战’号召下争做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他们做出可怕的事,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名垂千古。
”由此得出最浅显也最深刻的结论:“献身精神本身不足以成为一种美德,为什么献身才是要义。”这个思辨,跟苏珊·桑塔格关于法西斯主义“对勇气盲目推崇”的批判正相一致(见同书所收《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也跟朱利安·班达对近代政治道德“鼓励把人直面死亡的能力树立为最高的价值”的辩驳不约而同(见《知识分子的背叛》第三章)。
我本对何满子的文字毫无兴趣,但他为吕荧立传的《六亿一人》,却是不可无的掷地有声之作:“七位数的知识分子与六亿人口中,只有吕荧一人,仅此一人,没有第二个,敢于在1955年5月25日召开的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面对大会对‘胡风反革命’气焰高涨的声讨,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英雄般地站出来,为后来事实所证明了的诬陷声辩:”胡风不是反革命!
‘“可幸的是,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苍黄中,吕荧式的人物,其实不仅仅是”六亿一人“:往前,在1953年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梁漱溟为农民请命,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并因此在大庭广众下顶撞毛泽东;往后,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持者要求全体举手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唯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不举手,紧闭双目以示反对。
敢于公开跟毛泽东争执,敢于公开为胡风辩护,敢于公开对刘少奇表示同情,当时都是仅此一人,没有第二个。但就因为有此一人,有了梁漱溟,有了吕荧,有了陈少敏,则中国人终于没有彻底丧失一士谔谔的精神,知识分子也因此挽回了最后一丝颜面。
鲁迅曾慨叹中国“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但尽管少有,却幸未绝迹。总而言之,《人文随笔》是一本林贤治风格的文摘集,文章水准虽有参差,但编者的精神始终贯注其中。书很薄很轻,思考却很厚很重。
民间姿态林贤治选择了散文与随笔体裁,而谢绝了论文体裁,这也意味着,他选择了批判精神而非专业精神,选择了民间立场而非学院立场。由此,正可见林贤治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期许:他不愿是知识界中人,而愿是精神界中人;他不做专业的知识分子,而要做不专业的知识分子。
在朱利安·班达的时代,知识分子卷入政治、迎合世俗,使得其思想和学术成为民族主义激情的牺牲品,班达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却似乎陷入另一种“背叛”——他们不再卷入政治,相反却逃避政治,以专业之名,行犬儒之实,仅仅将学术当做职业的敲门砖,当做生活的通行证。知识分子多已丧失了自由性格和批判精神,他们固然不复以政治激进主义作为他们的鸦片,却又以世俗消费主义作为他们新的鸦片。
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时候,像林贤治这样,拒绝学院知识分子的庙堂身份,维系民间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就愈显其独立不迁、横而不流。
在我个人看来,或许林贤治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他激扬自由精神,我深表认同;但他守护革命激情,我保持疑虑。他捍卫鲁迅,我可以理解;但他讥刺胡适,我只能存异。也许,理想主义终不免会带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书生意气吧。
尽管如此,任何时代到底都不应缺少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本是理想主义的守夜人,如果连知识分子都完全没有了理想主义,那么也就意味着,全社会的理想主义都已荡然无存,整个时代也将因此而丧魂失魄了。
林贤治:“随”是一种境界
记者:《人文随笔》丛书已经出到了第三卷。你做这套书最早的想法是什么?
林贤治:就是觉得国内思想类的刊物很少,屈指可数,所以想补充那么一点。
记者:那如果和《读书》这样的刊物相比呢?
林贤治:《读书》基本上是知识型、观念型的刊物,其中的文体也以论文和介绍性的文字为主。而《人文随笔》采用的随笔是属于文学的一种,它借助文学固有的功能,使思想观念带上审美性。可以这么概括,《人文随笔》的文章既是思想的载体,又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是思想、生活、审美三位一体的东西。
记者:这样的东西在国内杂志当中是很少的,那你在选择文章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
林贤治:首要的标准就是人文化的倾向。我选的文章大抵带有着对社会的关怀,关注人的生存、人的精神、人的命运,也就是人从物质状况到精神状况的方方面面。
记者:从书中选录的篇目来看,既有说理性的文章,又有非常朴实的“口述实录”式的文字,感觉风格上似乎比较多样。
林贤治: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里的“罗马”就是人的生存。而这些“大路”有的偏议论说理,有的偏叙事记录,还有的偏抒情。我对文字的要求是非常挑剔和苛刻的。像夏之卷里几篇讲西部农村教育的,是小学老师自己的叙述;秋之卷里有记者采访沙兰镇100多个孩子意外死亡事件的手记。这些文章可能比较直白,相对不那么有文采,但那也是一种朴素的美。
我所看重的一点是,作者必须怀有对人类生存的关爱之心。从上述几篇文章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亲历者内心的强烈躁动、忧虑、纷乱,对社会正义和人类幸福的希冀。
记者:那么说这是一个跟现实关系非常紧密的书。
林贤治:应该是的,在这本书里是找不到闲适,找不到传统文人玩赏式的文字的。那是我最反感的东西。也没有幽默。我觉得这个时代离幽默很远。
记者:你预想的读者是什么样的?
林贤治:当然我希望范围大一些,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人,从青年到老年。但能够掏钱买这本书的人,我想应该是对思想有追求、对文字的美也有追求的人。
记者:采用随笔这种文体的好处在哪里?
林贤治:好处就在“随”。不要小看“随”。随随便便,普普通通,这里有一种自由意识、平民意识在里面。这随便可以打掉很多学者的架子。能写高头讲章的人,不一定能写随笔。“随”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它要求作者要做一个普通的人,不带优越感,心态正常。
很多名人已经做不到这个了。我觉得随笔天然地适合承载思想。因为它既能表达思想,又带有审美价值。其实思想本身是有活力的,与我们的生活关系密切,它不是那么呆板僵化,永远让我们感觉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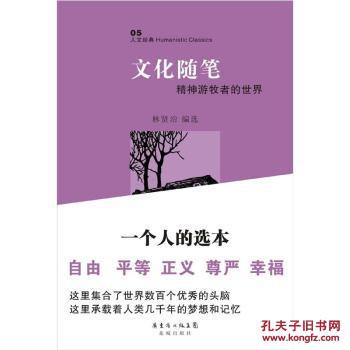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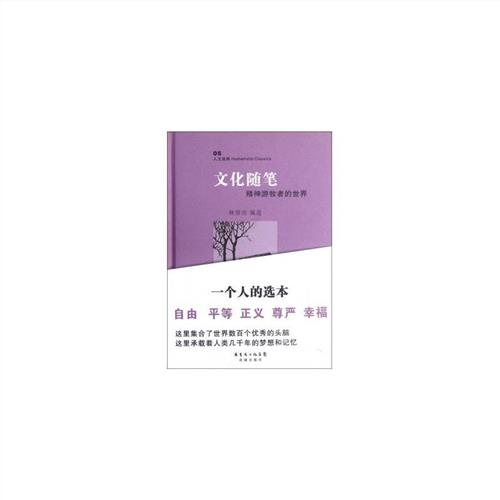




![安徽薛荣年 [股市360]薛荣年收拢平安保代会师华林 著名曾年生当总裁](https://pic.bilezu.com/upload/e/4f/e4f29cb3940539151e0384e28ab639ce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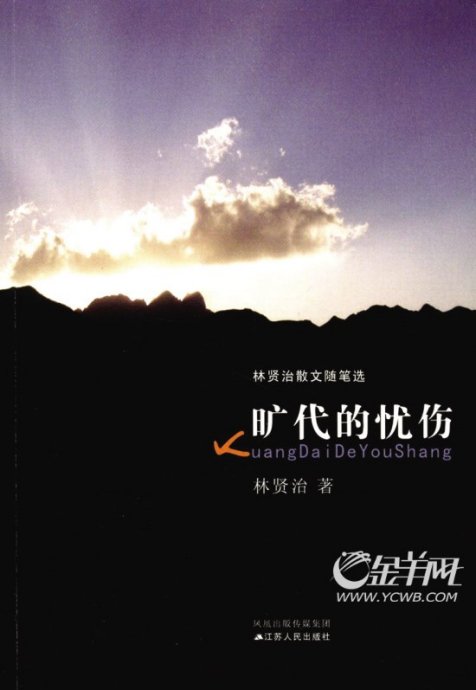






![>薛荣年保释 [股市360]薛荣年收拢平安保代会师华林 著名曾年生当总裁](https://pic.bilezu.com/upload/4/b6/4b645b238126d5b4cebf8a4a9429a3c4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