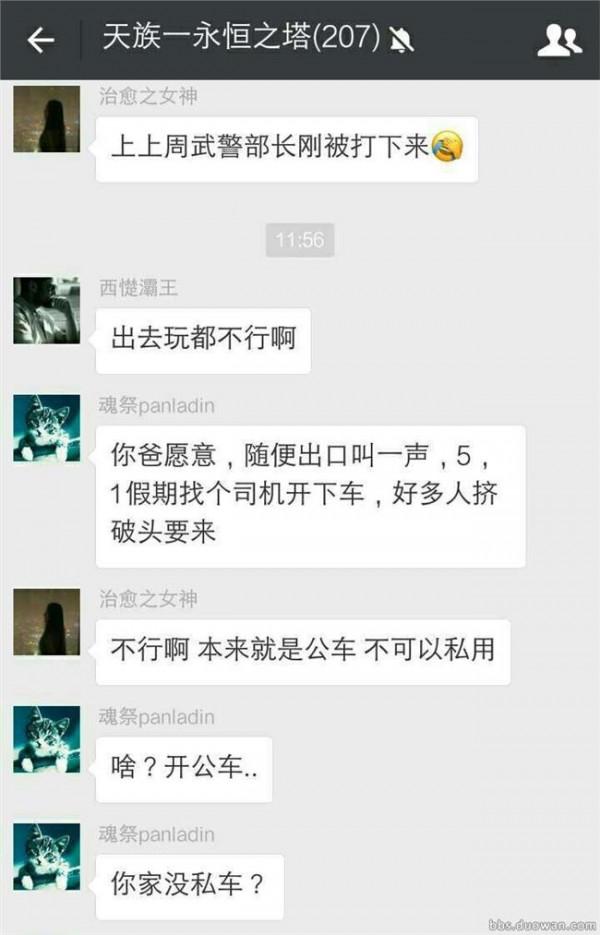周小舟子女 【高干子女】看看那时的高干子弟
不全的“全家福”,摄于1958年,大哥缺席。后排左起为老鬼、大姐徐然、二姐小胖,前排左起为母亲杨沫、父亲马建民(图片由老鬼提供)
因为出身干部子弟,孩子们对父母的级别本能地注意,对平民子弟,潜意识里就有点瞧不起。 还记得一个高年级同学,不知道叫什么,总穿着双褐色皮鞋,即使是旧的,在一九五九年,全校一千多同学中能穿上皮鞋的也寥寥无几。
他还敢穿着皮鞋往水里踩,毫不在乎。最叫我敬畏的是他能背出一百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字。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的名单,他了如指掌,像是中央组织部长。本校同学中谁父亲是什么职务他也能滔滔不绝地给你讲一大串儿。
聊天时,他还能说出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及众多指挥员姓名、籍贯、职务以及打过什么仗、授了什么军衔、夫人叫什么、孩子在哪个学校上学……我却啥都不知道,根本插不上嘴,一下子就感到人家才像干部子弟,自己却无知透顶,一点也不像干部子弟。
为了像一个干部子弟,我也开始背中央委员名单,并注意搜集部长、副部长名单,只要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人是什么官儿,就抄在小本子上背,记了满满一本儿。很快,我就背熟了一大串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名字,上将的名字也能记住二十多个……特自豪。
好像知道了吕正操是铁道兵司令、赵尔陆是一机部部长、王平、肖克、郭天民、杨成武、李志民是上将……自己就不是小市民了。可惜五十七位上将的名字总是搜集不全,我一直耿耿于怀,我很希望能把所有上将的名字都叫出来,以为这才更像干部子弟。
妈妈曾很好奇地看我往小本子上抄大官儿的名字,好多人她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尽管我们不怎么公开议论同学的父亲,但内心深处都知道班里同学谁的爸爸官儿大、谁的爸爸官儿小。
比较而言,父亲官儿大的同学就更有威信一些。我们班长姬军是外交部副部长、老红军姬鹏飞的儿子。姬军瘦高个儿,爱踢足球,很守纪律,功课好,谦和有礼,从没和同学闹过别扭。
他穿得很干净,但也就是蓝布裤子,古铜色的旧条绒夹克,每星期六都乘公共汽车回家。 毛主席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的儿子范苗长得像个大娃娃。他大手、大脚、大脑袋,说话口齿不清,总爱摇头晃脑,曾动手术将六个手指、脚趾割去一个。
他虽然功课不大好,却憨头憨脑的,非常可爱。同学们隐隐约约知道他父亲跟彭德怀一起犯了错误,被降了级,对他充满了同情。 建材部部长赖际发的小孩儿赖小危和我打过架,以后就关系疏远了。
主要是他很壮,我也不弱,谁也不服谁。直到毕业前夕,我们也不大来往。但事实上,他很朴素,穿的衣服比平民小孩儿还旧,从不搞什么特殊,周末也从没见家里用小车来接过他。 何孟雄烈士的侄女何小珍也跟我同班。
何小珍的父亲何健础是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与毛主席认识。何孟雄系中共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一年的最早党员,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是何小珍父亲的堂弟。何孟雄曾三次上书中共中央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后遭到错误处分,一九三一年被捕不久牺牲于上海龙华。
何小珍大眼睛大鼻子,乐观爽朗,咋咋呼呼,从没向我们提过她叔叔。直到陶承的《我的一家》出版后轰动一时,才有人透露她叔叔是陶承的儿子欧阳立安的入党介绍人。
何小珍常常嘲笑我的一些行为举动,但没有恶意。 凌土儿的父亲是凌云,公安部副部长,为人善良随和,很少跟同学争吵,也爱踢足球,是姬军的好朋友,我们班的中队旗手,两道杠。 方辛辛的父亲方复生当时任天津市政府外事处处长,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干部。
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经萧楚女介绍,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四期。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共党员。毕业后在叶挺部任连长、参谋等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又赴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
难怪方辛辛长得有点像俄罗斯人,眼睛发蓝,翘翘鼻子,我能感觉出她对我很友好,但我待她很冷淡。当时,我哪里知道她父亲的资格这么老,还以为她父亲的官儿不大呢。 还有,周正华的父亲韦明是周总理的秘书,跟我同住在复兴门外的国务院宿舍。
我父母与她父亲的关系很好。 我对小官儿的孩子,确实有一种轻视。如一位本校老师的女儿,很是天真泼辣,我却看不起她,把她的泼辣视为俗气、爱穿新衣服视为臭美。还有一个男生叫张柯,是新转来的,喜欢唱京戏。
我感到他父亲官儿不很大,戏称他为"张科长",老善意地挖苦他。 我的父亲是九级干部,在同学中不属最高,也不是最低。但自己心中还是暗暗嫌父亲官儿小,一九三〇年入党的,怎么才混个九级?当有同学问我父亲多少级时,我曾说过八级。
因为照实说了,我总觉得不如一个中将、上将硬气。在育才这种干部子弟的环境下,潜移默化中我已经懂得虚荣了,以父亲官儿小为耻。但由于说瞎话很累,必须总得记住,不能前后矛盾,让人戳穿了就更丢脸,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老实承认父亲是九级。
我曾特地问过哥哥,爸爸的级别合军队上的几级,够不够得上将军?哥哥告诉我,爸爸的级别大校是绝对够了,少将也差不多够。
因为八、九、十级都属于军级干部,军队就有九级的少将,我知道后特别高兴。 有的同学总爱往高了说自己父亲的官儿,明明是个科长却说成处长;明明是处长却说是局长;明明是局长却说是部长。我对这类吹自己老爸官儿大的家伙恨之入骨,虽然自己也偶尔吹过。
许老师对高干孩子和平民孩子绝对不一样,比如,她从来就没有碰过姬军一下,因为报纸上经常出现姬鹏飞的名字。开家长会时更明显。对领导或领导秘书,她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但对普通家长,就不那么鸡啄米一样地点头。
她老喜欢挖苦嘲讽桑桂兰像个家庭妇女,暗示桑桂兰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她受了她母亲的影响。其实桑桂兰的父亲是个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同志,可能职务不高;她母亲是为了支持她父亲搞革命才失掉了工作的。
那时候,很多高干的孩子根本看不出什么特殊来,穿得破破烂烂。比我大几届的育才校友戍大燕,是他们班上穿得最差的孩子。春游时,天气已经很热,他还光着膀子穿件棉袄,连件衬衣也没有。
他的一双布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跟乞丐一样。老师批评他:"你怎么搞的,这么邋遢,你的家长是怎么当的,一点儿不负责任,星期六你让他来找我。"星期六接孩子的时候,戍大燕领着一个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黑棉袄,活脱脱的一个老农民来见老师。
这人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对老师说:"我是戍子和,大燕的爸爸,孩子卫生不好,我有责任。"老师愣住了,他知道戍子和是薄一波的助手,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呀!竟然俭朴得像个老农民。
我潜意识里常常幻想父亲是一个将军,那多威风!很为他只混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头头难为情。母亲写的《青春之歌》里有个小资产阶级主人公林道静让我感到羞耻,母亲的妹妹白杨是个著名的电影演员也让我感到不光彩,因为电影明星等同于资产阶级。
谁要在我面前提林道静或白杨,我就气得要命,立刻翻脸。我私下觉得文艺界资产阶级味儿浓,跟她们沾上关系,不如跟红军、八路军沾上关系光荣。 我多么羡慕那些出身于革命军人的小孩儿啊!有一次,母亲带我上街,可能是在阜成门外,碰见了一个育才的同学。
我感到特不好意思,赶忙与母亲拉开距离,因为觉得母亲穿着太洋气,跟上海资本家的阔太太一样。她还把头发弄个大疙瘩系在脑后,像个羊尾巴,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大街上,极少见。
父亲原来在国务院二办工作,顶头上司是张际春。可不知为何,却又被调到了北师大当代理书记、副校长,以后是副书记,名次越来越靠后,我真替他憋气。 我和父亲之间虽然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我还是希望他的官儿能再大一点。
父亲从不带我出去串门,似乎是怕我这没礼貌的农村土孩儿丢他的人。父亲能和姐姐小胖长时间地又说又笑、亲亲热热,又上街、又陪客人、又看电影,任凭小胖撒娇,跟他争吵,却很少跟我说过话。
记得一个星期天,我爬上一棵海棠树,被洋剌子蛰了,疼得像火烧一样,又哭又喊。父亲在屋里全无反应,结果还是姐姐和老太太跑过来,帮我上了药。父亲对哥哥也很冷淡,哥哥回到家就干活,穿得又破,以至于被邻居认为是父亲的勤务员。
此时,我已不是农村来的小土孩儿了。在育才学校的干部子弟圈子中,我懂得了等级,知道了自己的父母属于司局级干部,父亲坐的车是别克,有时,不知怎的,也能坐上吉姆。当我坐上父亲的吉姆车时,心里非常兴奋,特希望能碰见同学,显一显。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我看见父亲的请柬是鲜红色的,烫着金,比过去的请柬高级,就以为父亲升官儿了,回学校马上向同学询问,是否副部级的官儿才能拿鲜红色的请柬。
答案是肯定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很想把这请柬给偷了拿给同学们看看,美一美,无奈父亲保管得很严格,无法下手。 父亲平时很注意不让我有什么特殊化的观念。他认识的大官儿很多,却从不跟我提一下。比如聂荣臻、吕正操、林铁、肖新槐、周彪、周小舟、旷伏兆、罗玉川、刘秉彦等都曾是他晋察冀的老领导。
哥哥透露给我,姐姐上华北军区文工团是爸爸给聂荣臻写了信,这让我特激动。啊,爸爸还有这等面子!他自己却从来不说。
每逢过年过节,回学校后听姬军、赖小危等人议论起他们陪父亲一起参加欢庆活动时,我发现父亲却没有参加,又让我痛心父亲官儿还不够大,感觉特沮丧。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我的个子长高了,胳膊变粗了,走路越发沉稳有力。
姑姑从老家捎来的土布衣服我再也不穿了,嫌它太寒酸、太土气。我对待保姆的态度也横了起来。虽然父母一再教育我要尊重保姆、尊重劳动人民,我还是很恶毒地把那个照顾我的老太太给骂走了。原因忘了,反正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和她争辩起来,她把我说得没了词儿,我却不服气,觉得她不过是一个做饭的,连一个大将的名字都不知道,连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就气急败坏地骂:"去你的,滚蛋,你滚蛋!
" 自从我们家搬到国务院宿舍后,就住在四楼。
父母感到老太太岁数大了,又是一双小脚,天天买菜上下楼不方便,已有辞退之意。所以我这次骂老保姆没有挨父母的说。老奶奶伤心之极,默默流泪,当天晚上就向母亲告辞走了。 我自以为是堂堂的干部子弟,对底层人产生了居高临下的心理。
三十多年过去,这位老奶奶肯定早已不在人世,但她给我洗脸、喂饭、擦屁股、扇扇子、擦鼻涕……我都还依稀记得。尤其那次着火母亲打我,她跑过来拉住了母亲,把我从鸡毛掸子下解救了出来,晚上还轻轻抚摩着我的伤痕,哄我睡觉。
哎呀,我却仗着自己会背一大串中央首长名单,仗着父亲能到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就瞧不起了老奶奶,生生地把她骂走了。 写到这儿,我不得不忏悔两句:这位默默无闻的老奶奶呀,您的姓名,我已经永远不可能知道--只有父母可能会记得,但他们也都已经谢世。
如果有天堂的话,我愿意到天堂上找到您,向您深鞠躬、深低头,抚摩着您的老手,当面赔礼道歉。我干了坏事,对不起您。 (节选自老鬼《血与铁》,标题是本博另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