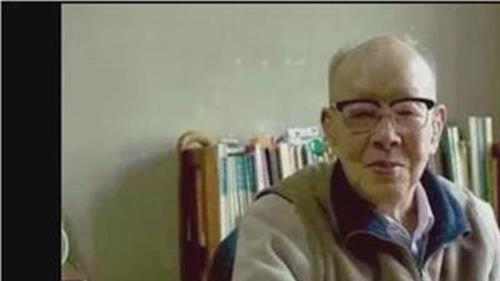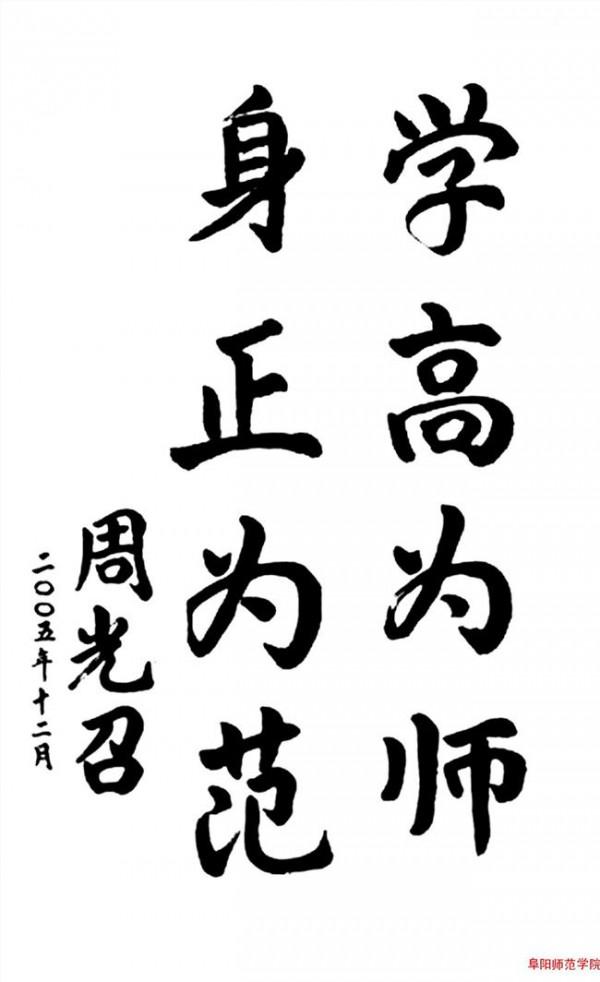周有光近况 走近周有光老人:至化无方至德有光
工作很久,才知道周老居然就住在离自己办公室两分钟就能走到的地方,也直到《静思录——周有光106岁自选集》出版,送样书、送稿费,才和老人有了更多的交往。每次老人都说“见到你很高兴”,初时以为客套,后来我发现老人谈兴真的很浓,慢慢就养成了去聊天的习惯。
周老聊天的开场白通常是:“好了,你现在可以说话了。”因为要先戴上助听器。除了耳朵,身体无大碍,读书写字,谈话会客,一如常人,对一百多岁的人来说,真是难得。周老却很谦虚,说:“不行了,老糊涂了,一百岁以后的事情,大部分都记不得了。”嗨,世上有几人能熬到说这话的资格呢?周老年轻时患肺疾,曾有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35岁。
老人最喜欢讲故事,尤其喜讲下面这个,连我都陪各路人马听过好几遍:实行配给制后,周老家因有两位保姆,粮票不够。有旁人指点:周老夫妇可去政协食堂吃饭,省下粮票给保姆。周老无奈,依计前往,问题果然解决。每次吃饭,均见一老先生亦来吃饭。仔细一看,原来是溥仪。每次讲到这里,周老都会率先笑起来:“哈哈,皇上家也没粮票啊。”
某年有关部门通知周老出国访问。周老说:我不去,我的西服都破了,没有衣服穿。有关部门说:马上做新的。周老很高兴,遂新装出访。回国后才知道,新衣服按规定要上缴,只好接着穿旧的。这事每次提起也是开心得不行。有一次,周老晚辈查阅国外资料,发现周老上世纪40年代曾和爱因斯坦见过两次面。遂吃惊发问: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过?周老答:“我没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言语之间掩不住孩子般的得意。
周老曾参与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这也是周老津津乐道的:“你看,小保姆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我的拼音。老伴90岁学电脑,也要先学拼音。”我趁机问了一个自己困惑多年的问题:“ü是我最喜欢的字母,一条小鱼两个泡泡,太可爱了。可是jqx小淘气见了鱼眼就挖去,为什么挖啊?留着多合适。”周老说:“为了写着方便。”也是,十几亿人学拼音,省下的小点点,就是恒河沙数。
我说:“我觉得字母比表意文字高级。”周老马上开始显摆自己的《世界文字发展史》,很得意地说:“这本书我写了40年。”我说:“搁现在,照您这种写法,副教授都评不上就该退休了。”翻着书里的鸟篆虫书,我问:“这些您都认识吗?”周老说:“写书的时候当然都认识,但现在,全忘了!
”又说,“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情。玛雅文,我早就认出来了,也发表了文章。可是中华世纪坛前些年举办玛雅文化展,那么大的展览,就只把原文展出来,没有中文解释。我早就认出来了啊,他们不知道。哈哈!”然后就翻书,一个一个指给我看。好在玛雅文的常用词只有几百个,半小时也就看完了。嗯,以后可以吹牛,我也是学过玛雅文的人了。
某天忽然接到周老公子晓平先生电话,言近日流传周老若干言论,有些是老人说的,有些不是。老人无意成为问题人物,亦不主张暴力。媒体为求轰动效应,不惮乱写,可能会给出版者带来一些麻烦,特表歉意。我回答:多谢,目前尚无妨。周老言论无端遭人增饰,犹不忘体恤顾及出版者之处境,蔼然仁者之怀,令人感念。
周老的太太张允和于2002年8月去世,享年93岁。当时,我已经在他家楼前的办公室里坐班两年,近在咫尺,却无知无闻,缘悭一面。直到着手做周老的书,才逐渐接近。一天,周晓平先生随手送我一本书,说∶“这是妈妈的。”装帧设计都很精致的《曲终人不散》。说来惭愧,这还是我第一次全面阅读张先生的文字。果然闺秀,文笔和周老迥然不是一路。尤其《小丑》一篇,老人淡淡叙来,间以插科打诨,却看得我难过至极。
文章写某年的某个下午,家里忽然来了不速之客,搞外调。因为老太太对来客所询答以“不知道”,小将勒令∶“不许坐,站起来!”“给你五分钟,考虑考虑!”老太太只好从命,站立考虑。这样的情形,想来很多人的记忆里还都有残影……接下去老太太这样写道: “随后是抄家。
外调人员走后,围观的半大孩子们一拥而入,打开小孙女的玩具橱,各取所需,一哄而散。踩倒了丝瓜架,踩坏了碧纱窗。忽然想起聂绀弩,他《题林冲题壁寄巴人》中有一联名句: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一字一顿,字字千钧。”
张允和出身世家,年轻时曾伴周老环游世界。聂绀弩的人生经历更是风云变幻、云谲波诡。有这样阅历和眼界的老人,一金刚怒目,一菩萨低眉,在面对种种“又向荒唐演大荒”的闹剧时,却不约而同,不由自主,穿越时空,一笑莫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笑”!
上面的感想曾被我写成小文发表,发表后,也曾拿去向周老献宝。记得当时,还带了一摞要求签名的书。本来不忍心劳动老先生,晓平先生说:“没关系,签吧,正好活动活动手指。最高纪录有一次一连签了40本呢。”所以每次去,我都会给老先生带点小零活儿。
坐定以后,周老看了眼稿子,说:“先签字,好把书拿走,省得堆在桌子上。”签完,开始看稿。等他看完,我说:“我觉得张允和先生的文字,比您写得好看。”周老侧着耳朵听清楚以后,忽然开始大笑,说:“她写的是文学性的,好看。
我的不是。”话锋一转,“你喜欢语言学吗?我可以把我的书送你。”然后打铃叫人送一本书进来,认认真真签好字,给了我。我赶紧接过来收好,我可不想告诉他,这已经是他送我的第三本一模一样的书了。一篇小稿,忽然就打开了周老的话匣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搞经济吗?因为当时我的老师说,你周围的人全是搞文学的。搞得好的不得了。你再搞也超不过他们了,你不要搞文学了。文学搞得再好,也救不了中国。不能让中国富起来。一个国家,要是人人都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国家就完了……你学经济吧。后来我去了美国。一看果然。美国的大学,要求学生,不能只读一个方向的书,文学书籍应该占多少比例,非文学书籍应该占多少……”
周老早年读书、留学日本,专业都是经济金融,然后一直在银行工作,曾派驻纽约、伦敦。他搞经济搞到一半,1955年忽然改行,去做文字改革、汉语拼音。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周老喜欢说一句话:“温故知新。”他温的那个“故”,比别人的“新”,都不知要长多少。
忽然想,如果夕阳西下时分,周老偶尔回忆往事,首先会想起哪一段呢?30年代?50年代?70年代?周老还有句名言:“人生是场马拉松,不必在乎一时之长短。”让我非常信服,而且受益匪浅。不过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首先,如何才能把自己的人生变成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古人言:“至化无方,至德有光。”就在这些随随便便的聊天里,我已如坐春风受益良多。曾有一位朋友问周老:您的名字是源于《圣经》的创世纪吗?周老答:“不是,中国古人也有叫这个名字的,比如归有光。”虽曾求学日本,任职美国,怀抱种种欧风美雨,但我经常会想,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2014年元旦前后,老人感冒住院,逐渐减少会客。今年元旦后,已经110岁的周老,身体依然康健,足以令人欣慰。1月下旬,却忽然传来周老哲嗣晓平辞世的消息,真是令人难过。经晓平先生之手,我与周老签过好几份出版合同,但由于我的磨蹭,至今仍有两种未见样书。
曲未终,人已散。因为经常去周老家,遇到晓平先生的次数很多。每个周末,当时已届八十高龄的晓平先生,都要坐地铁,从中关村赶到朝阳门附近,来看父亲。有一次,周老指着晓平先生说:“他当我的儿子,真是倒霉啊。
别人八十岁已经是老人了,可因为我还活着,他只能当孩子。大家也都拿他当孩子。”举座大笑。我当时签了周老一本书,张允和先生一本书,转头跟晓平先生说:“您也给我们写点东西吧。”晓平先生大笑,说:“我不会呀!”至今思之,如在目前。
(作者:廉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周有光《静思录》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