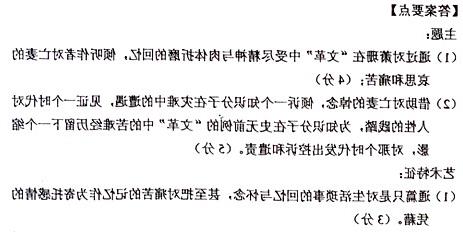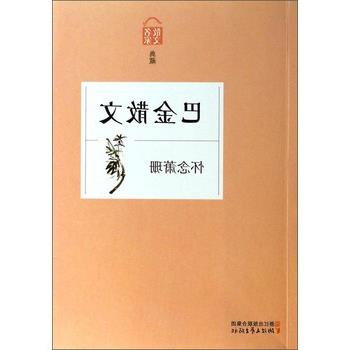巴金两篇动人心弦的思念老婆萧珊
巴金(1904 2005年),我国现、今世闻名作家,无党派人士。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还有佩竿、余一、王文慧等,本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及《憩园》、《寒夜》,散文漫笔集《随想录》、《真话集》等,还有很多译作。
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心的有前进思维的作家,在寥寥无几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2003年国务院颁发其“公民作家”荣誉称谓。
曾获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苏联“公民友谊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声誉院士称谓等。首倡树立我国现代文学馆,主张树立“文革”博物馆。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描绘前史剧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也许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没有郭沫若的渊博学养,没有徐志摩、朱自清的瑰丽文采,也没有沈从文、老舍的明显个性;但他激烈的热心、激烈的对于芳华冲力的巴望,却让他变成“五四”芳华精力的最佳标志。
他在言外之意焚烧的情感,点亮了多少人魂灵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的行走,叩响了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射中的热心、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书中永久闪烁灿烂的光芒。
萧珊(1918 1972年),巴金的得力助手和恩爱情侣。原名陈蕴珍,奶名长春(因女友叫她“小三”而谐音为“萧珊”),结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上海人,父亲是一位商人。他们1936年知道,1944年成婚,在一同日子了调和、甜美、高兴的28年,两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萧珊逝世后,晚年的巴金写了《思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漂亮的双眼》等文章留念她,真实是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思念萧珊》写于1978年:“今日是萧珊逝世的6周年留念日。6年前的光景还十分明显地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全部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自个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留念她的文章。
在50年前我就有了这么一种习气:有豪情无处倾诉时我常常求助于纸笔。但是1972年8月里那几天,我天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 我甘愿让(萧珊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依然和我在一同。”
《再忆萧珊》写于1984年,那是又一个6年曩昔了(引文见文首)。
有人说,巴金既专注又多情。作家萧乾则说他“写爱情,但不谈爱情”。巴金的终身有一个不变的主题:爱。爱祖国,爱公民,也爱他的老婆、孩子和兄弟。女作家冰心评估道:“巴金最可敬服的地方,即是他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厉和专注。
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厉、真诚而专注的,这是他最可钦之一。巴金终身的爱情,只和一个叫萧珊的女人有关。”他们的爱情是如此忠贞和火热。28年的婚姻日子,他们一向相亲相爱,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
他们相识于1936年的大上海。那时,年仅32岁的巴金,已在文学创造和翻译两方面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青一代对夸姣爱情和夸姣日子的寻求。所以巴金收到了很多函件,不少是寻求他的女人写来的。
一天他又拆开了一封信,里边一个女孩子的相片掉了出来。他很诧异地捡起相片看了看,这女孩剪着一头短发,戴着花边草帽,有着和蔼的笑脸。他下意识地翻过反面,上面写着“给我爱戴的先生留个留念”。巴金微笑了一下,阅览了那封信。
本来,这个女孩的来信一向最多,笔迹清秀,言词不多,落款老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的信给巴金留下了格外的形象。他们通讯了大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她即是萧珊。最终仍是萧珊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调和,为啥就不能面谈呢?期望李先生能容许我的恳求 ”巴金深感这是位开畅、仔细的女中学生,由于信中不只约好了时间、地址,还夹着她的一张相片。明显她是怕巴金认错了人。
依照信中的约好,巴金来到新亚饭馆。一瞬间,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人呈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神来,她就像熟人相同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说着请萧珊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萧珊望着巴金,快活地笑道:“李先生,您比我幻想的可年青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一瞬间少了很多拘谨,高兴地说道:“你比我幻想的还像个娃娃呢!”萧珊笑着说:“我可不肯李先生也把我当小孩看哟!”
看着萧珊稚气的姿态,巴金觉得很风趣,便诘问她:“哦,还有人和我观点相同?”巴金这么一问,萧珊一股脑儿托出了这次找他的真实缘由来:“我恨我父亲,他老说我小,一向不允许我参与爱国学生运动。正本我是校园有名的干将。我不光常常演前进话剧,如《雷雨》中的四凤,还结识了上海很多从事话剧的前进人士,常常参与他们的活动。”
巴金说:“我信任。你父亲是干啥的?家里还有些啥人?”萧珊叹了口气:“我父亲是上海泰康食物厂的股东,还在南市城隍庙开了家咖啡馆。他老是处处约束我,尽管妈妈有常识、懂文学艺术、倾向 五四 新潮,弟弟也与我情投意合,但仍是抗不过父亲。
李先生,我真想脱离这个死板的家庭,去闯荡江湖。”巴金一听,忙说:“千万不要这么,我前段时间还写信劝过一个17岁的女孩子不要逃离家庭。像你这么的少年,仍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激动行事。你现在应当多读书、多考虑,再举动啊。”巴金苦口婆心的言语,打消了萧珊离家的想法。一位高文家和一位少女的心逐渐拉近了间隔。
这次碰头今后,他们彼此留下了极好的形象。萧珊更多地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心肠在信中说:“我永久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她为“小友”。萧珊常到巴金作业的出书社去找他,以求思维上得到更多的启蒙。巴金一向防止把萧珊当作“另一半”的幻想。
1936年末,巴金的兄弟要去桂林半年,家里无人照料,便请他去协助照看居所。所以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端关怀他的起居日子。萧珊的来访和关怀,使从成都出走十几年很少与女人触摸的巴金感遭到了日子五光十色、布满画中有诗的另一面。
他们的豪情交流和对日子的知道、方案逐渐老练。1937年他们正式订亲,爱情又得到了新的提高。1938年7月,萧珊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书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同就餐。巴金作业时,萧珊则照料杂事,彼此尊敬,十分调和,像兄弟相同。
不久巴金应邀去武汉,她也随同前往。10月日军攻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出书社同行,匆促包船去桂林。途中换船等船、防敌机、躲警报,总共9天。后来,巴金依据这段流离失所的日子写下了《从广州出来》等一系列文章:“这些通讯写了我爱情日子中一段阅历,没有润饰,也没有诗意,咱们即是那样日子,没有半点虚伪。”
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巴金又投入到了忘我的写作当中。1939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两人约好第二年再相见。今后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秋》。1940年夏,巴金跑到昆明和萧珊碰头,她仍是那么生动开畅、丰姿绰约、光彩照人。巴金的心境十分欢愉。暑假日间,他们天天都在一同,一同玩耍,一同招待亲朋好友。黑夜巴金送萧珊去女人宿舍,自个回到住处伏案写作。
3个月后巴金去了重庆,一住即是一年。1941年暑假,他去昆明看望萧珊后回到桂林。萧珊十分牵挂巴金,怕他只管忘我地作业,不管就餐和歇息。她一封接一封地给他写信,关怀他的身体和日子。巴金每次收到萧珊的信,都是一读再读,感动之余,也及时回信彼此鼓舞,增进情感。
1942年,因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搭档连续脱离了桂林。他顿感悲寂,手足无措。无微不至的萧珊深深惦念着他,不等大学结业就来到他身边,并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悲伤,我不会脱离你,我永久在你身边。”巴金的双眼湿润了,他颤抖地说:“萧珊,我不知道如何谢谢你,再等我一年,好吗?”萧珊没有提出任何贰言。
她了解地知道,巴金有一咱们子人,原由三哥承当的日子费用,现在只能靠他了。所以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挣了些钱,侄儿、侄女的膏火没疑问了,自个成婚成家的费用也有了。
1944年5月,萧珊和巴金决议成婚。此刻巴金现已40岁了,而萧珊只要26岁。从相识到成婚,他们的恋曲进行了8年。这8年中,他们在烽火连天中几度离散、几度团聚,天涯海角,两情依依。同甘共苦的年月,早已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同。
现在总算要成婚了,萧珊明澈的大双眼里盛满了对将来的神往和巴望。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兄弟一间屋做新房,没有增加一丝一绵、一凳一桌,只要他4岁时与妈妈的合影作为家传家产。也没啥可组织的,只托付弟弟以两头家长的名义,向亲朋印发了一张游览成婚的“告诉”。
一个星期后,巴金和萧珊去贵阳城外风景如画的花溪度蜜月。是夜,两人偎依在一把长长的藤椅上,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曩昔的作业和将来的日子。萧珊转动着一双明如秋水的大双眼,兴味盎然地谈着,用温顺的目光凝视着她的如意郎君。她对他仅有的恳求即是:“从今日起我是您的老婆了,再不许叫我小女子了。”
新我国树立后,巴金在文学界有了较高的方位和较多的作业,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十分繁忙,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家里的全部都由萧珊照料,夫人是他们家真实的“顶梁柱”。好在他们在此之前就曾有过几年聚少离多的日子,两人早已习气了温馨的笔谈。
1960年冬,全国正陷于严峻的饥馑危机,上海家中全赖萧珊照料组织。她既要照料儿女又要服侍婆母,自个还在杂志社上班。由于粮食严峻,家中三餐已改为二稀一干,稍后又被逼改为一天三稀。每人天天只能吃到2分钱的菜,给孩子们订的牛奶只能3天供给一次。
孩子患病想吃挂面,还非得有医师证实才干买到。煤也缺少,限量供给。萧珊尽量节约用煤,生怕到急需时供不上。巴金其时在成都,饮食尚可。当他联想到家中瞪大双眼的儿女、不堪仰慕的爱妻,他们快要“三月不知肉味了”,乃至处在半饥饿状况,心中有说不出的悲伤和苦楚。
他在给萧珊的信中屡次说道:“我每顿饭都想到你们,我要是能分一半给你们就好了。对于你来不来的事,我有时也对立,格外是在就餐的时分期望你来共享 盛馔 ,在黄昏时分,期望有你对坐谈谈 ”
“文革”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秘了多少次自个所遭受的待遇,而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罪。在巴金遭批斗的那些年,作为他的老婆,萧珊也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纸牌,并被派去扫大街,遭到周围不明事理的人谩骂和糟蹋。
为维护巴金,她还被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打过。不过萧珊一向静静忍耐,即是为了不让巴金悲伤。她常常一大早便陪着巴金从家里走到车站,从后边将他推上公共轿车,尽力不让他摔下来;还要不断叮咛他,不要忘了将小红书带在身边。这时巴金便十分自责,以为恰是自个的写作害苦了老婆。
1972年6月,巴金从干校回来休假。萧珊卧床不起已有好些日子了,见老公回来,她发灰的脸上露出了笑脸。巴金见老婆的病越来越重,有时烧到摄氏39度以上,屡次看医师都弄不清究竟是啥病,便恳求延伸假日,留在家里照料她,但没有得到“工宣队”的同意。
7月中旬,家人托兄弟想了不少方法,给萧珊拍了两次X光片,才查出她患的是肠癌。后来,在亲属的协助下,萧珊才住进了医院,这时大夫发现她的癌细胞已分散到了肝部。在这种状况下,巴金方获准留家照料萧珊。他天天去医院陪老婆大半响。
8月8日,萧珊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前,她生平仅有一次对巴金说:“看来咱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悄悄捂住她的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彼此交融,肝胆欲碎。
手术后,巴金静静地守在萧珊的床榻前。到悲极时,他简直想大声大喊:“全部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萧珊尽力克制住自个的苦楚,不叫不喊;除了模糊中几回恳求开床边的氧气筒,和担忧输血太多付不起医药费外,她从不诉苦啥。她含泪望着形容瘦弱的老公说:“我不肯丢开你。没有我,谁来照料你啊?!”望着老婆那双很大、很美、很亮的双眼,巴金心中布满了酸楚,专注的期望即是她能赶快康复健康。
8月13日正午,巴金在家刚端起饭碗,俄然接到传呼电话说萧珊逝世了。真是平地风波!全家人当即赶到医院。萧珊的尸身已用白床罩包好,停在太平间的担架上。巴金弯下身子,隔着白布拍着她的遗体,无声地哭喊:“蕴珍,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心中涌出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萧珊临终前一向牵挂着“叫 医师 来”,她其时习气称巴金为“医师”。巴金懊悔老婆临终时没有守在她身旁,懊悔没有听到她留下遗言,懊悔有很多话没有向她倾诉。
后来,巴金回想到这段阅历时写道:“她十分安静,但并未昏睡,一向睁大着两只双眼。我望着、望着,如同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双眼永久亮下去,我多么惧怕她脱离我 ”
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向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床头则放着她的译作。
友人考虑到巴金的日子和写作,以为他应当有个伴侣来照料他,便悠扬地向他表明了这个意思。巴金给了他最简练明快的答复:“不想找老伴,没有兴致和劲头。”巴金心中的那个方位永久交给了萧珊,没有任何人再能占有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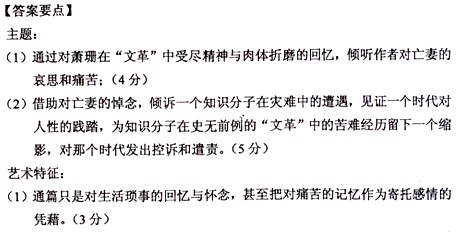

![>怀念萧珊 巴金两篇感人肺腑的怀念妻子萧珊[中国历代名人情感解读系列]](https://pic.bilezu.com/upload/e/b7/eb758965e771f5c3d0900d83ae732dd3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