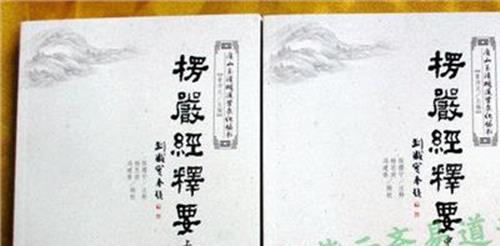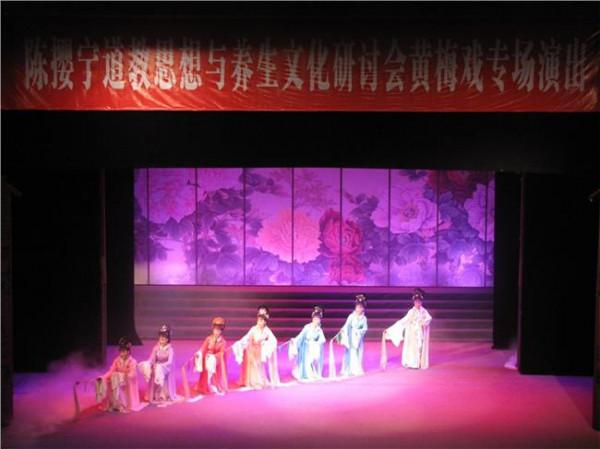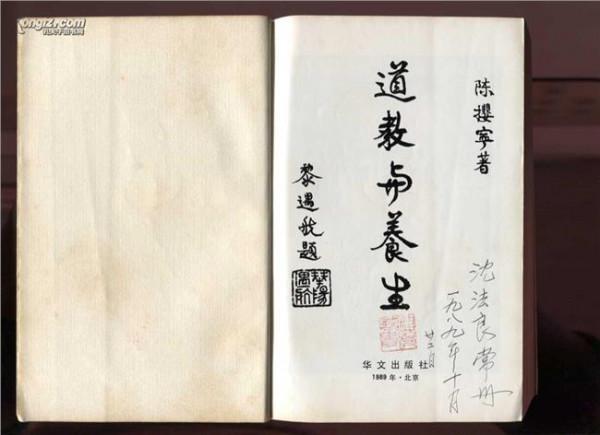葛洪哲学书 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与黄老学的关系
《抱朴子》内、外篇是葛洪的重要着作,其中内篇集中反映了他的神仙道教思想。对于内、外篇的思想倾向,《外篇·自叙》说:“《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这里所说的《内篇》“属道家”之“道家”,很大程度上指的是“黄老学”。其实,即使他所说的“属儒家”的《外篇》,也有多处称颂、赞美“黄帝”、“老子”抑或“黄老”的字眼,故无论《内篇》、《外篇》都渗润着一种“黄老”情结,只不过《内篇》的“黄老”情结要比《外篇》浓重得多罢了。
对此,其《内篇》说:“夫体道以匠物,宝德以长生者,黄老是也。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减周孔也。” “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
黄帝先治世而后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黄老之德,固无量矣,而莫之克识,谓为妄诞之言,可叹者也。”而《外篇》则说:“徒疲劳于述作,岂蝉蜕之有期也?独苦身以为名,乃黄、老所嗤也。”内、外篇对黄老学的这些崇信、赞颂,有的从“道”、“德”能使人长生着眼,有的从黄帝既能治世又能得道成仙立论,还有的是从老子既能兼综礼教又能长生久视提出的。
不管从哪个视角去信奉、推崇黄帝、老子,都说明《内篇》“属道家”的“道家”,已与老庄原始道家有很大不同,而在精神实质上则与“黄老学”有着相通性。
学界皆知,“黄老”作为黄帝与老子的合称,它是指从老子道家分化出来的那个假托黄帝以自重的道家支流。其产生于战国中期前后,分别以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齐国为主要活动中心,到西汉初,南北这两支黄老学整合在一起,并臻于极盛。
根据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黄老学是围绕着“道”与治国、治身的问题展开的。“道”是治国、治身的究竟,治国、治身则是“道”在形下层面的逻辑延展和降落,黄老学所关注的就是“道”与治国、治身怎样协调一致的问题。
在对待先秦百家之学问题上,它不再像老庄道家那样持拒斥的态度,而是主张以“道”为统领,兼取各家学说之长。依据上述黄老学的思想内涵,葛洪的道教思想中之所以渗润着黄老情结,其原因就在于他在不少方面援用了黄老学的若干资料。
(一)对道论的援用
黄老学作为从老子道家分化出来的一个道家支派,无论是反映战国黄老学的《黄老帛书》、《鹖冠子》、《管子·心术》四篇,抑或是反映秦汉黄老学的《文子》、《淮南子》、严遵《老子指归》、《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以下简称《河上公章句》)等,都继承了原始道家的传统,仍然把“道”作为最高哲学范畴。
葛洪《抱朴子》同原始道家和黄老学一样,也把“道”作为建构其神仙道教思想体系的哲学根据。它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
隶首不能计其多少,离朱不能察其仿佛,吴札晋野竭聪,不能寻其音声乎窈冥之内……”这里的“道”是从“本无名”立论的,即道既不是绝对的无,也不是绝对的有,而是一个不可穷尽的有、无共存,成为不可分割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整体。
由于“道”具有如此之特性,所以《抱朴子》又引进道家所常用的“玄”和“一”以深入论述它。内篇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乎其深也,故称微焉。
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又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谓也。”“玄”、“一”作为哲学范畴,均见于《老子》,其后的黄老学也几乎皆用“一”表征“道”。
至于“玄”,在黄老学中虽不多见,但葛洪“此所谓玄,原自汉代杨雄之《太玄》,非魏晋玄学之玄”。不过,杨雄《太玄》的气化论的宇宙生成图式,“基本上是《淮南子》的说法”,故“玄”在其流变过程中亦与黄老学有缘。
其实,从哲学特点上来看,《抱朴子》援用“道”、“玄”、“一”的偏重点不在于发挥老庄道家的抽象思辨性,而是与两汉的黄老学相接近。两汉黄老学的突出哲学特点:一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老子关于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坚持用自然主义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
如《文子》卷八专门以“自然”作篇名,而《老子指归》则云:“道德无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时行。凡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验也。”二是它在继承稷下黄老学“道”即“精气”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道释为“气”,并用道、气一元论充实两汉的气化论的宇宙生成理论。
如《淮南子·天文训》云:“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所谓“虚廓”、“宇宙”、“气”几个阶段,其共同特点都是指浑一无形象的不可见之气。
而葛洪《抱朴子》在对“道”、“玄”、“一”的具体运用上,则与上述黄老学两个特点有着相通性。对于天道自然无为,葛洪说:“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
”又说:“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他还指出,诸如水火在天而取之诸燧,铅性白而赤之以为丹等物类变化现象,“皆自然之感致,非穷理尽性者,不能知其指归,非原始见终者,不能得其情状也”。
而对以道、气阐释宇宙的生成,内篇《明本》说:“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塞难》则说:“浑茫剖判,清浊以陈,或升而动,或降而静,彼天地犹不知所以然也。万物感气,并亦自然,与彼天地,各为一物,但成有先后,体有巨细耳。
”甚至,《地真》还认为那个“浑茫剖判”的宇宙未分化的状态,也就是“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并强调“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
葛洪对宇宙生成的这些论述,在总的倾向上并没有脱离汉代黄老学的致思方式,特别是他的“道起于一”,基本上承袭了《淮南子·天文训》关于“道始于一”的说法,而他的“浑茫剖判”为天地万物的思想,亦与黄老学的一气(即“道”)化为阴阳而分为天地的说法相一致。故连同他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一起加以审视,葛洪的道教思想中的确援用了黄老学之道论的若干资料。
然而,葛洪对黄老学之道论的若干资料的这种援用,其理论价值不可低估。他所以对“河洛图纬,一视便止”,以及“不喜星书及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符之属”,甚至认为“天道邈远,鬼神难明”,从而表现出怀疑鬼神和反对祭祷鬼神的各种迷信活动的倾向等,与他援用并认同了黄老学关于天道自然无为及道、气论的宇宙生成论有密切关涉。
不仅如此,就连他的道教思想中何以存在着自然论与神秘论、理性主义与宗教信仰的矛盾,亦可从其转承了黄老学的若干积极成分而得到解释。
(二)对兼综百家之学的援用
在对待先秦百家之学的问题上,葛洪基本上采取了黄老学所主张的以道为主兼综百家的立场和思维。他同样先把“道”作为最高统领,认为在百家之学中,老子和老子的“道”为最高。他说:“得道之高,莫过伯阳”,“老子,得道之圣也”。
老子的“道”所以为最高,是由于“道者,万殊之源也”,“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损之不可减也”。所谓“万殊之源”,是说“道”是各种具体存在对象的本原,所谓“不可益”、“不可加”,是说“道”作为宇宙本原是无限永恒的存在。
这些说法,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抽象性、玄思性,未超出老子对“道”的规定。但是,老子道论的一个重要缺憾就是道作为万物的根源,其与自己的派生物之间是对立、隔绝的。像老子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以及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就有把“道”悬置起来的倾向。
而对原始道家的道论之弊作出纠偏的是黄老学,像它主张以道为主而兼综百家之学,就意味着作为各种具体对象产生的根源之道与其派生物不是对立、隔绝的,而是统一的。
葛洪《抱朴子》虽然崇信老子的“道”,但是并没有把“道”与各种具体存在相分离,而是着重将两者作了沟通。如《明本》说:“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今世之举有道者,盖博通乎古今,能仰观俯察,历变涉微,达兴亡之运,明治乱之体,心无所惑,问无不对者,何必修长生之法,慕松乔之武者哉?”葛洪认为“道”涵具天地、阴阳、柔刚、仁义乃至兴衰治乱之道,这就意味着原始道家的那个形而上的抽象之道已向经验层面的社会生活降落,从而为其接纳百家之学作了理论铺垫。
基于此种思维路向,《明本》则对“道”与百家之学的关系作了近乎《论六家要旨》式的评判。即谓:“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夫)以为阴阳之术,众于忌讳,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遍循;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
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
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可谓总结黄老学的纲要性文献。葛洪的这段论述虽然未必完全合乎《要旨》之旧,但他主张“动合无形”、兼综儒墨名法,却同《要旨》取得了一致,并表明他在处理“道”与百家之学的关系上确实选择了黄老学的立场和思维。
由此,葛洪一方面宣扬“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另方面,他又反对学者专守一业”,而主张博取百家之言。他强调百家之言,“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故而,葛洪对百家之学的优劣试图作具体分析,如认为:老子虽“不失人理之欢”,但却“泛论较略”;儒家虽重名利、爱势利,但其谈仁义,“制礼律以肃风教,皆大明之所为”,等等。
这些分析都是从社会和人生的需要着眼,因而与黄老学对待百家之学的理性态度相一致。
(三)对治国与治身思想的援用
在治国与治身的问题上,葛洪从其道论出发,也认为道具有治身与治国的功能。他说:“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道”所以具有治身与治国的功能,是因为“道”能使身、国达致自然无为。它体现在治国方面,即“干戈不用,不议而当,不约而信,不结而固,不谋而成,不赏而劝,不罚而肃,不求而得……令未施而俗易,此盖道之治世也。
”它体现在治身方面,即“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葛洪还从这种清静无为的治身思想引出了他的养生术,强调“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食不过饱……饮不过多”。
表面看来,这种以“道”治国、治身的思想,与老子的主张并无二致,然而在内涵上却与黄老学相接近。首先,从其主张以清静无为治国来看,这主要是从以“道”固“本”立论的。而在具体治国方略方面,葛洪更主张将“道之治”与仁礼刑结合起来使用。
他说:“仁者养物之器,刑者惩非之具”;“考名责实……匠之以六艺,轨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齐之以礼刑”。这种说法,既与其以道为主而兼综百家之学的学术精神相一致,又切近黄老学的治国思想。
其次,从其清静无为的治身思想和养生术来看,这不仅滥觞于原始道家,并且更被黄老学所继承和发挥。像《管子·心术》四篇、《文子》、《淮南子》,以及《老子指归》、《河上公章句》等,都无不张扬这种思想。同时,葛洪并没有把治身的问题仅仅归结于恬淡无欲和养生,而更强调治身也是一个积善修德的过程。
即谓:“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种思想,与《淮南子》等两汉黄老学着作关于以道家的修身术保持生命之真,而以儒家的仁义修养达致生命之善的主张,可谓同声同调。
既然治国与治身皆以自然无为为本,那么就势必得出治身与治国同理的结论。故内篇《地真》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
”其实,葛洪的这种说法并不是他本人的独创,早在《管子·心术上》中就有“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的君臣同体而分治的深刻论述。后来的黄老着作对此也多有推阐,如《淮南子·诠言训》引詹何的话说:“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
”《河上公章句》也说:“国身同也”;“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黄老学的这种身国同治、治身与治国同理的思想,乃至被《太平经》所接纳和系统化,提出:“端神靖身,乃治之本也,寿之征也。
无为之事,从是兴也。”幻想把无为治身推广到无为治国、治天下。可见,无论从哪方面说,葛洪《抱朴子》的治身与治国思想,都是与黄老学的主张有密切关联的。
二、对葛洪援用黄老学的宗教追问
葛洪在《抱朴子》中虽然援用了黄老学的若干资料,但是他并没有沿着黄老学的世俗学术走下去,最终倒是成了东晋的一位着名道教学者。《抱朴子·内篇》的中心思想,是以成仙为最高信仰目标,以修仙术、炼丹术、养生术为证成,其主旨则教人如何成仙。
以此为圭臬对葛洪援用的黄老学资料进行宗教追问,他的这种援用适成其道教神仙思想形成的一剂酵母,并在某些环节上为其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作了理论铺垫。换言之,葛洪正是以神仙信仰为观照,并在这种观照下对其所援用的黄老学资料加以裁剪、改铸和整合,才充实起其神仙道教体系的。
(一)“气”、“玄”、“一”的宗教归宿
如前所述,葛洪在道论方面确实接受了黄老学的道气一元论和天道自然无为的一些思想。但是,当他以“道”阐释人之成仙的可能性、成仙之要方,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时,所使用最多的范畴则是“气”,并赋予“气”以精神或神灵的属性。因此,尽管葛洪在对道、气的理解上曾保留了黄老学的某些理性特征,但他在构建其神仙道教体系的过程中,却使“气”流为一个宗教性的本体。
例如,人何以能成仙,一直是道教产生以来所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葛洪要确立其神仙不死的目标,就必须重新阐释这个难题。对此,葛洪的回答是:“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认为人生受气若正好遇到仙宿,他就会生来相信仙道,再加上肯刻苦修炼成仙之方,就能登道成仙。
这种阐释在内篇《辨问》中得到了相同表述,他借援引《玉钤经》之意说:“按仙经以为诸得仙者,皆其受命遇值神仙之气,自然所禀。”葛洪以“气禀”之不同来阐释人有没有成仙的可能性,这不仅把“气”纳入了有灵论,而且也把“自然”流为偶然、命定论的代名词。
再如,在如何成仙问题上,葛洪把“宝精行气”作为修仙之要。即所谓:“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炁,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
”又谓:“九丹金液,最是仙主。……宝精爱炁,最其急也。”葛洪“宝精行炁”的理论根据是“炁”构成人和天地万物,即:“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
”他以此解释生命的奥妙,认为人“受气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若乃精灵困于烦扰,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天和,劳逸过度”,即使祭祀鬼神也难保真长寿。这些说法,并没有脱离黄老学自然论的范畴,并含有某些中医养生学的科学因素。
但是黄老学的养生理论偏重于“养神”、“爱气”,直到东汉末早期道教的另一部着作《老子想尔注》才正式提出“食气”、“宝精”的修炼方法,主张“宝精勿费”。大概正是沿循《想尔注》的这种修炼方法,葛洪在内篇《至理》诸篇中,认为宝精行气不仅可以“内以养身”,而且还可以“外以却恶”。
像他列举的那些“行气”可以“禳天灾也”、“禁鬼神也”,可以“举形轻飞,白日升天”的故事传说,都表明他的“道”或“气”在此时已神格化了,并最终转化成神仙信仰的道教范畴。
又如,在以“气”解释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葛洪也常常把它作为一种能赏善罚恶的精神力量来看待。亦即:“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
”他说山川草木等皆由“精气”所构成,这是坚持了黄老学的元气自然论,但他把精气与精神混为—谈并赋予其赏善罚恶的功能,这就把“气”、“精气”神秘化了。故而,可以说葛洪对道、气的援用,其出发点是黄老学的,而其归宿则是道教的。
不仅如此,即使葛洪援用的“玄”、“一”,其归宿也与“道”、“气”相同。他援用“玄”、“一”的目的不在于如何深化“玄”、“道”的范畴体系,而是将其神格化,使之成为论证成仙的哲学根据。他说:“一在北极大渊之中,前有明堂,后有绛宫;巍巍华盖,金楼穹窿;左罡右魁……龙虎列卫,神人在旁。
”又说:“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
”这里的“一”显然是有形象有人格的最高神灵性存在。既然如此,那么得道成仙的秘诀就是如何“向一”、“思一”、“守一”,故葛洪将“一”分为“真一”和“玄一”。所谓“真一”,就是祛祸消灾的神秘功能。
即:“守一存真,乃能通神……陆辟恶兽,水却蛟龙;不畏魍魉,挟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葛洪认为,“守真一”与服食金丹同等重要。因为服食金丹虽然能使身体保持健康而达于长生不老,但如果不守“真一”而消灾免祸,那就会外患扰体、不能“守形”,于是无法达致长生不老。
所谓“玄一”,就是神秘的分身术。即:“守玄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
”故欲成为神仙,就必须通过“守玄一”的分身术,使人之三魂七魄与天灵地祗、山川之神相感通。按照葛洪的神仙修炼理论,服金丹是外养,守“真一”、“玄一”是内修。由于他把“一”转化为神这个最高本体,所以这不仅将以道为本体的道家(包括“黄老学”)与以“一”(即“神”)为本体的道教区别开来了,而且也协调了服金丹与“守真一”、“守玄一”的修炼术之间的关系,这应是他对其以前道教理论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对兼综百家之学的宗教运用
从世俗学术的视野看,葛洪在对待百家之学的态度上同黄老学确有相通之处。但是,葛洪赞同黄老学兼综百家之学的动机,不啻在于吸取诸子百家的思想,而且更在于从中提取一种思维方式,超拔道教的容纳汇合精神,以为论证神仙信仰体系提供一种方法。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正是在这一包容、开放思维方式的观照下,葛洪虽然独信金丹,以为“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长生可知也”,但他认为修炼之方是多种多样的,故欲敷演金丹大法,就要善于把各种各样的法术吸收过来,加以去粗取精,择善而用,切不可只知一端,而走片面。
他说:“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由此,葛洪批评当时信道者只执一术的错误做法,指出:“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长。
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矣;学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他明确表示在学道问题上,偏颇任何一术都是徒劳的。足见,葛洪倡导的是一种兼容开放、博采众长的修炼方法。
根据《抱朴子·内篇》,他的包容一切、博采众长的修炼术有行气、房中、辟谷、导引、药物养生等,并在《释滞》、《对俗》诸文中专门作了论述和辨别。特别是对于行气,他认为“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并指出胎息的原理和机制是根据龟鹤的导引食气以达长寿总结出来的。
葛洪对胎息的这种理解,对后世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道藏》中大凡讲胎息者多引用此说。除此之外,葛洪还记录了各种方技、符箓,如佩符、风水等,认为这些方术在避邪、治病、防身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作用。
而对于民间的养生技巧,如坚齿之道、聪耳之道、目明之道、登涉之道等也兼采并用,不加排斥。可见,黄老学的兼收并蓄的学术特点经葛洪的剪裁、转手和整合,不仅在内容上得到了宗教性的拓展,而且它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也适成了充实葛氏神仙理论和修炼之术的工具。
(三)从治国向治身的倾斜
葛洪和黄老学虽然都主张协调道与治身和治国的关系,但在治身与治国孰轻孰重的问题上,黄老学主张以治国为主而次及治身,葛洪则偏重于治身而兼及治国。诚然他在《抱朴子》中也谈到了治国与治身同理的问题,但其倾向却是重治身而轻治国,最终以养生、长生为归宿。
他说:“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长生”所以为“道之至”,是因为“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故人欲长生成仙,就必须善于内修、外养,从养生做起以防患于未然。
“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民难养而易危也,气难清而易浊也。故审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欲所以固血气。然后真一存焉,三七(即三魂七魄——引者)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
”这里的“审威德所以保社稷”,只是一种借喻,其要旨在于教人如何通内修外养的养生之道而获致“年命延”。既是这样,那么“道”主要观照的就不是治国,而是养生问题。所谓“死王乐为生鼠”,以及“道与世事不并兴,若不废人间之务,何得修如此之志乎”,都表明葛洪已把养生、修道的治身作为高于一切的要务。
当然,葛洪在倡导治身的过程中,曾屡次运用过“穷理尽性”、“理尽事穷”、“穷道尽真”、“尽物理耳”等哲学命题或术语。但这些命题或术语经他运用,绝没有任何伦理道德的意味,而是在于探索生命的幽隐之秘,并潜含着宋明道教关于性命双修的某种因子。
至于《抱朴子·外篇》在“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的过程中所谈论的如何采用仁义礼刑进行治国与处世的问题,把它与《内篇》的根本思想联系起来看待的话,这恰恰体现了中国道教其外为救人济世的精神,而其内则为治身长生以追求肉体飞升或不死成仙的信仰,这是不可震撼和移易的。
葛洪由治国向治身倾斜,这与黄老学的演化有密切关涉。西汉中期以前,黄老学的确把以道治国作为其理论探讨的重点,但在西汉中期后,特别是到东汉时期,其所探讨的重点与以前有很大不同,怎样颐养性情、延年益寿,怎样离世遁居、独善其身等,则成为它关注的焦点。
一些人或好黄老,清静寡欲,不慕荣华;或学黄老,庶几以松、乔之术而达长生不死。此时的黄老学几乎成了治气养性的养生学的代名词,其原有的那种关注现实政治的责任感、进取心和所迸发出来的理性精神,已被淹没在追求长生不死的仙国中。
这种情况,不仅《后汉书·光武纪》载有太子劝光武帝以黄老学的“养性之福”保养其身心之事,在《后汉书》的列传中也还载有任隗、樊瑞、淳于恭、樊融、高恹、矫慎等一大批信奉黄老养生成仙说的官吏或逸民,足见当时的养生风气之兴盛。
尽管东汉的这种崇尚黄老养生以成仙的风气曾在魏晋时期受到玄学的冲击,此时的玄学内部仍有人在阐发黄老的养生思想,像嵇康的“养生得理”的养生观念,就是在对黄老食气之学研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葛洪的重治身而轻治国,大概就是沿循黄老学的这种学术重心的转移发展下来的。他所以援用黄老学的思想资料来构建其神仙不死的信仰体系,大概就因为黄老学曾经是道教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而葛洪所处东晋时代的文化走向是玄学与佛学的合流,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他援用黄老学来构筑其神仙道教思想体系,足见他是一位具有本土文化情怀的道教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