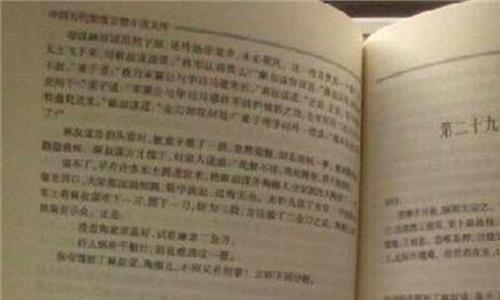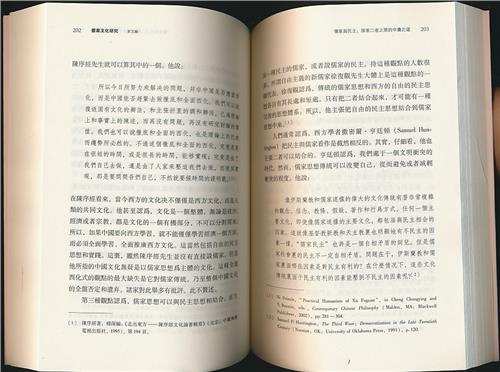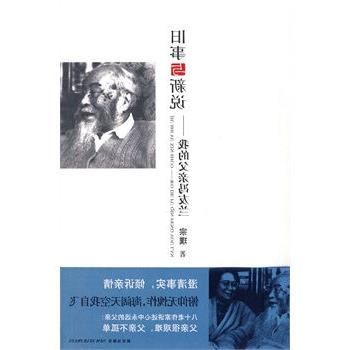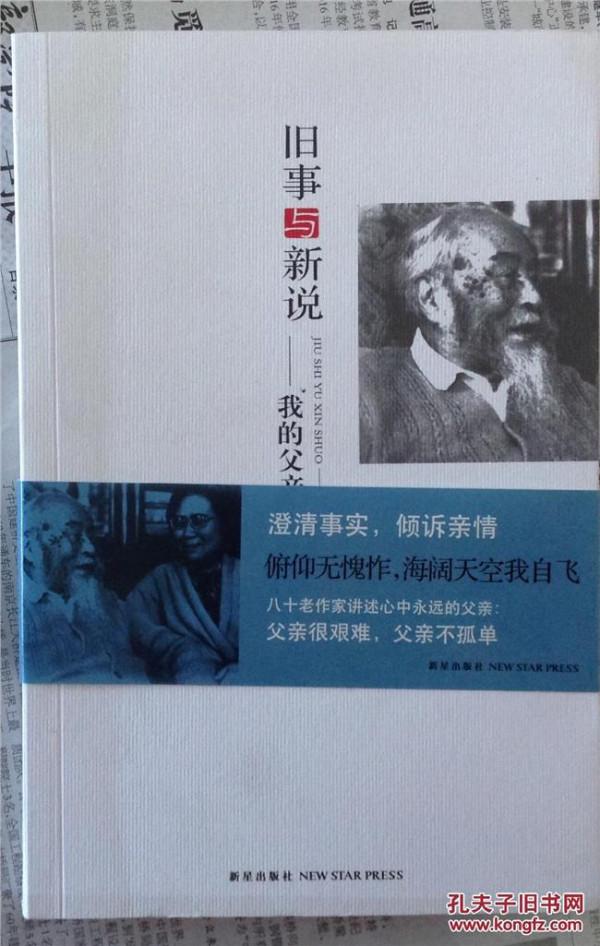陈来评价冯友兰 余敦康:怎样客观公正评价冯友兰的哲学业绩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的同龄人,经历了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文革”动乱直到开放改革新时期的全过程。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虽然冯先生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多次变化,但是变中自有不变者在,这就是始终不渝地联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中国文化的前途,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坚持不懈地上下求索,试图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转化之路。
冯先生曾说:“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
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能适应。”(《三松堂自序·明志》)这段话不仅表述了冯先生个人的心声,同时也具有普遍的意义,代表了生活在现代的一大批中国哲学家的共同的心声。
关于中西古今文化的矛盾冲突是时代的主题,所有站在时代前列从事思考的哲学家,莫不为这个主题所困扰,普遍抱着“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心态,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决思路,创建了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哲学再现了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那样的辉煌,营造了一种如同《易大传》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那样的格局。
如果单就“殊途”、“百虑”的一面而言,各家之间相互攻驳,争论不休,一部现代中国哲学史可以说是由一系列的论战所构成的斗争史。
冯先生的新理学的体系,由于个性鲜明,思路独特,往往被卷入到斗争的中心,褒贬不一,赞扬者有之,谴责者亦有之,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哲学家。
但是,如果我们撇开由历史的偶然因素所形成的学派偏见,站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复杂进路和坎坷历程的宏观角度,着眼于其“一致”和“同归”的一面,就可以看出,冯先生和其他各位同时代的哲学大师一样,他们所探索的主题以及所研究的对象是共同的,所以虽“百虑”而“一致”;他们都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无限关怀祖国的命运和文化的重建,所追求的目标是相通的,所以虽“殊途”而“同归”。
据此而言,一部现代中国哲学史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各种学派和各种思潮互争雄长的斗争史,而应该看成是围绕着共同的时代主题进行探索的历史,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互动互补、和而不同的丰富多彩、仪态万千的面貌。
冯先生的哲学体系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因而也就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和不可取代的地位。当我们立足于这种宏观的历史背景来重新研究冯先生的哲学著作,可以发现,冯先生毕生辛勤的探索从来没有脱离时代的主题,其所凝结的探索成果贯穿了一条独特的一以贯之的思路,显示了理性的洞见和深邃的智慧,直到今天仍未丧失现实的意义,给后人以启迪。
一、“贞下起元”、“旧邦新命”——冯先生哲学探索的根本关怀
在《新原人·自序》中,冯先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全,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四部书后来加上《新原道》、《新知言》,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先生解释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
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这种发自肺腑的真诚的表白,说明冯先生的哲学探索,并非是躲在象牙塔里从事概念的游戏,为了建构一种玄虚的纯哲学体系以自娱,而是服务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崇高目标,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广阔的胸怀。
当时冯先生以清醒的理性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指出日本是工业国,中国是农业国,日本业已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化,中国则仍然处于前现代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日本成为东亚的城里人,中国成为东亚的乡下人,为了压制中国,叫中国永远当乡下人,所以日本必须派大量军队来侵略中国,这就是中日冲突的根本原因,而冲突的性质也就是工业国与农业国、现代与前现代之争。
冯先生认为,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唯一可行的路就是摆脱落后的状态,迅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行现代化的建设。
这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必过的关。知其是必过的关,则即非往前闯不可。闯过也要闯,闯不过也要闯。因此,冯先生提出了“且战且走”的口号,主张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弘扬中国文化与“斗争的精神”异曲同工的“无逸”的精神。
冯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四千年的生存,就是靠这种精神维持的,以这种精神作为强大的精神力和道德力,再加上现代的知识、技术和工业的补充,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也一定会复兴。
在《新事论·赞中华》中,冯先生满怀信心地指出:“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这种完全以国家民族为念的根本关怀和坚定乐观的信念,是推动冯先生从事哲学探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构成了《贞元之际所著书》的总的基调。
50年代以后,经历了“文革”前的批判和“文革”中的折腾,到了晚年,冯先生仍然是未改初衷,矢志不移,抱着这种根本关怀和乐观信念从事《新编》的写作。在《三松堂自序·明志》中,冯先生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
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坚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冯先生哲学思想的评论,多半侧重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纯哲学理论的逻辑分析,不大重视冯先生的根本关怀所在,模糊淡化冯先生“贞下起元”、“旧邦新命”的哲学抱负,这就免不了会产生许多不尽不实的误解。
为了对冯先生所创造的哲学业绩求得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对冯先生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进程中作出合理的定位,有必要特别强调冯先生毕生追求的目标和探索的重点。这是我们重新研究冯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二、《贞元六书》——一个理事兼备、体用一源的完整体系
冯先生的新理学体系,形成于抗日战争的40年代,由《贞元六书》所构成。冯先生指出:“这六部,实际上只是一部书,分为六个章节。这一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凡是反思,总是在生活中遇见什么困难,受到什么阻碍,感到什么痛苦,才会有的。
如同一条河,在平坦的地区,它只会慢慢地流下去。总是碰到崖石或者暗礁,它才会激起浪花。或者遇到了狂风,它才能涌起波涛。”(《三松堂自序》,第245页)所有这些困难、阻碍和痛苦,都是由中国社会没有完成向现代转型所引起的,在经济上缺乏一个产业革命的变革,在文化上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各国,落后就要挨打,因而中国人遇到了“一个空前底挫折,一个空前底耻辱”。
这种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在冯先生的内心深处引起了轩然大波,促使他进行反思。
由此可以看出,《贞元六书》所反思的问题并不是与人生日用毫无关联的纯哲学的问题,也并非是引进西方的新实在论接着程朱理学讲,仅仅着眼于中西哲学的结合;实际上,其所反思的问题虽然涉及到方方面面,就总体而言,全部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探索如何使之克服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阻碍和痛苦,由一个传统的旧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以平等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换句话说,《贞元六书》是一部忧患之书,是一部中华民族在那个面临着“空前底挫折”和“空前底耻辱”的时代寻找如何脱困的出路之书。
关于这六部书的内在结构及其在新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冯先生本人在前后不同时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1940年写成的《新世训》的自序中,冯先生说:“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曰《新事论》,谈社会文化问题。
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是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王之道’也。合名曰《贞元三书》。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铄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
1946年写成《新知言》,冯先生在自序中又提出了另一个说法:“《新原道》述中国哲学之主流,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此书论新理学之方法,由其方法,亦可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之地位”;“新理学之纯哲学底系统,将以《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及此书,为其骨干。
”50年代以后,冯先生的纯哲学系统受到猛烈的批判,他的哲学抱负被视为狂妄,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被迫无奈,有时为《新原人》辩护,有时为《新原道》辩护,似乎是以为其他的四部书都可以否定,唯独这两部书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阐明中国哲学的特点多少有一点价值。
冯先生前前后后的这三种说法,语境不同,强调的重点很不一样,这对我们准确地把握六书的内部关系,如实地理解新理学体系的性质,确实是增加了不少困难。
应当承认,冯先生对自己的纯哲学系统是十分钟爱的。《新理学》是这个系统的总纲,着重讨论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冯先生认为,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中西哲学共同的问题,中国哲学从公孙龙一直讨论到程朱理学,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一直讨论到新实在论,但是这种讨论在中国哲学中却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和特殊的方法。
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涉及到真际与实际、道与器、理与事、体与用、天与人、内圣与外王诸多方面的关系。就其所用的方法而言,主要是一种负的方法,直觉的方法,至于西方所惯用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则非其所长。
新理学融贯中西,接着程朱理学继续讨论,建立了一个名之曰“新统”的纯哲学系统,作出了很大的创新,解决了存留于中西哲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冯先生着眼于纯哲学系统的成功的建构,把《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说成是这个系统的骨干,自有充分的理由,如同当年张载在完成了自己的体系时所说的,“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谦,所言皆实事”。
但是,纯哲学系统所讨论的问题,有真际而不着实际,极高明而不道中庸,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个层面,不进一步讨论实际的文化社会问题,用中国哲学的标准来衡量,就叫做有体而无用,有虚而无实,明于理而暗于事,蔽于天而不知人,内圣与外王不相贯通。
这是中国哲学的大忌,冯先生当然不会满足于只做一个专门从事抽象思辨的纯哲学家,他反复引用“横渠四句”以自勉,追求此二者的结合,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使自己的哲学服务于贞下起元振兴中华的大业,所以他不能不走出纯哲学的领域,去讨论许多实际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新事论》和《新世训》这两部书在新理学体系中就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值得认真研究。
冯先生晚年并不把《新事论》看得很重。关于《新世训》,冯先生说:“现在看起来,这部所讲的主要是一种处世术,说不上有什么哲学意义,境界也不高,不过是功利境界中人的一种成功之路,也无可值得回忆的了。”(《三松堂自序》,第260页)这种有意的忽视和贬抑是在晚年经过自我否定后的特殊语境下说的,当他早年刚刚写成了《贞元三书》之时,却是充满着一种无限欣喜的和自豪自诩的心态,作了很高的评价:“书虽三分,义则一贯。
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王’之道也。”如今时过境迁,历史的偶然因素不复存在,我们可以不必拘泥于冯先生本人晚年过分的贬抑,而应该以早年的说法为据,重新恢复这两部书本来应有的地位。
照冯先生看来,新理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业已由《贞元三书》所完成,《新理学》是这个体系的纯哲学的依据,着重于讲理,《新事论》是纯哲学的实际运用,着重于讲事,《新世训》讨论功利境界中人的成功之路,也是讲事的,这三部书合起来看,就是一个明体达用、理事无碍的完整的体系。
因此,他对《贞元三书》作了很高的评价,意思是他的新理学的体系已经完整体现在这三部书之中了。但是,就纯哲学的系统而言,意犹未尽,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讨论到,所以又接着写了另外三部书,即《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作为“新理学之纯哲学底系统”的补充。
从冯先生纯哲学系统的几部著作问世之日起,就引来了许多批判,认为这是一种玄虚的哲学,背离了中国哲学传统的精神,体用殊绝,理事割裂,无实事求是之意。
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到《新事论》、《新世训》这两部书来看,这种批判完全是一种误解,不仅误解了新理学的根本性质,而且也误解了冯先生在贞元之际所探索的时代主题。
实际上,《新事论》的宗旨是“中国到自由之路”,《新世训》的宗旨是“生活方法新论”,其中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当时国家民族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十分实际的问题,丝毫没有玄虚的味道。《新事论》以“别共殊”开篇, 《新世训》以“尊理性”开篇,说明这种讨论是以纯哲学系统中所讨论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为依据,追求理与事的结合,因而新理学的体系是由纯哲学系统和实际应用的哲学系统共同构成。
如果我们只关注它的纯哲学系统,不重视对《新事论》和《新世训》的研究,那就是歪曲了它的本来面貌,把一个完整的体系变成一个跛脚的体系了。
三、“别共殊”——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新模式
自“五四”以来,围绕着中国如何摆脱落后挨打的地位,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两个堡垒分明针锋相对的思想派别,一个是“全盘西化”派,另一个是“本位文化”派。这两派争论的焦点是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
“全盘西化”派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当时所有一切消极的东西,都是由传统遗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因袭的重担,为了向现代转型,必须与传统彻底决裂,全盘西化。“本位文化”派则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看法。
他们援引许多历史事例,证明中国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进路,只是在物质文明的层面暂时落后于西方,主张“中体西用”。这两个思想派别,前一派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带有激进的倾向。
后一派以梁漱溟、杜亚泉为代表,带有保守倾向。这两派的争论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关于中西文化优劣之争,属于文化史观的范畴,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关于中国走向现代化应该选择何种道路,采取何种模式的一种紧张的探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
冯先生一直是关注这两派的争论,并且站在哲学的高度,把他们所争论的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如何明确地区别共相与殊相的问题,一方面肯定了他们探索的成果,同时也指出其片面性的失误,从而独树一帜,提出了自己所设想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的蓝图。
在《新事论》中,冯先生运用这种“别共殊”的思路,分古今,辨城乡,说家国,原忠孝,谈儿女,阐教化,评艺文,讨论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既有思想的广度,又有思想的深度,实质上是对现代化模式的一种全面的思考,与“全盘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所设想的模式鼎立而三,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进程中的一大景观。
在当时那个三派鼎立的时代, “全盘西化”派的激进主张属于左翼,“本位文化”派的保守主张属于右翼,冯先生的“别共殊”的主张并非激进,也不保守,属于中间派。中间派是不好当的,常常会受到来自左翼和来自右翼两方面的攻击,而且也处于少数的地位,不易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但是,唯其如此,也正好显示出冯先生所倡导的这种“别共殊”的现代化模式的独特的个性,及其超越于其他两派之上的综合创新的精神。
冯先生指出,一般人所说的东西之分,不过是古今之异,所谓古今之异,其实就是社会各种类型的不同。我们近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西方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
中古的文化是农业文化,其社会类型是以“家”为本位。近代或现代的文化是工业文化,其社会类型是以“社会”为本位。某一种社会类型是共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是殊相。
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是某一类型的社会,而在另外一个时期可以转化或发展成为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这就是共相寓于殊相之中。因此,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只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即由农业文化转入工业文化,由中古类型转入现代类型,并不是将我们的一个特殊的文化,改变为另一个特殊的文化。
当这种转变成功,从共相的角度看,中国就进入到世界上先进国家的行列,中国文化也就成为现代化的类型,但从殊相的角度看,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国文化仍然保留着自己所特有的个性。
冯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最合理的选择,“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主张之所以说不通,行不通,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别共殊”,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思想混乱,只把文化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而不知其类型。
在《新事论》的“别共殊”篇中,冯先生对这两派都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所谓西洋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则所谓全盘西化者必须将中国文化之一特殊底文化完全变为西洋文化之一特殊底文化。如果如此,则必须中国人俱说洋话,俱穿洋服,俱信天主教或基督教等等,此是说不通,亦行不通底。
”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认为全盘西化,则中国失其所以为中国。虽然他们也认为中国文化有当存者,有当去者,西洋文化中亦有中国所当取者,但是由于不识共相,不明类型,难以确定取舍的标准,总体上表现了一种保守的倾向。
比如“有人说,中国的文言文,是当存者。有人说,中国的旧道德,是当存者。但无论如何说,如果以所谓中国文化为一特殊底文化而观之,其说总是武断底。”
冯先生根据这种“别共殊”的观点,提出了自己具体的主张。他说:“所谓西洋文化是代表工业文化之类型的,则其中分子凡与工业文化有关者,都是相干的,其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我们要学,则所要学者是工业化,不是西洋化。
如耶稣教,我们就看出他是与工业化无干的,即不必要学的。我在朋友中间,他们一有说到‘西洋化’,我总是要说‘工业化’。……照我们的说法,我们要‘工业化’,即与工业化有关者皆要,否则不要,则主张‘全盘西化’与‘部分西化’者大约都可满意了。
而主张‘中国本位’者也该满意了,以中国为本位,与‘工业化’冲突者去之,不冲突者则存之。”(《三松堂学术文集》,第392页)关于中国的当务之急,冯先生指出:“中国现在最大底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
这是一个基本。至于政治上应该实行底主义是跟着经济方面底变动而来的。有许多所谓教育文化方面底事,都是这样底”;“生产社会化的开端,始于工业”;“所谓民主政治,即是政治的社会化。
政治的社会化,必在经济社会化底社会中,才能行”;“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底;一种经济制度,是跟着一种生产方法来底。不从根本上着想,不从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讲‘应该’,讲‘奋斗’,讲‘法律’都是无补实际底。
”在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冯先生主张,“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教育制度亦须工厂化”;“对于教育人材,亦要集中生产,大量生产,细密分工”;“教育制度工厂化与教育商业化并不是一回事,亦不是一类底事。
教育商业化是不好底,但教育制度工厂化,则是好底,是生产社会化底社会所必要有底。”关于道德方面的变革,冯先生指出:“我们是提倡所谓现代化的。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底,或不现代化底。
”“只要有社会,就需有这些道德,无论其社会,是哪一种底社会。这种道德中国人名之曰‘常’。常者,不变也。照中国传统底说法,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是无论什么种底社会都需要底。
这是不变底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忠孝是因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之有而有底道德”,“忠孝可以说是旧道德。我们现在虽亦仍说忠孝,如现在常有人说,我们要对于国家尽忠,对于民族尽孝,不过此所说忠孝与旧时所谓忠孝,意义不同。
此所说忠孝是新道德。我们可以说,对于君尽忠,对于父尽孝,是旧道德;对于国家尽忠,对于民族尽孝,是新道德”。总起来说,冯先生认为: “中国现在所经之时代,是生产家庭化底文化,转入生产社会化底文化之时代,是一个转变时代,是一个过渡时代”。
所谓过渡时代也就是继往开来的时代,传统创新的时代。“社会上底事情,新底在一方面都是旧底的继续。有继往而不开来者,但没有开来者不在一方面是继往。”(以上引文均见《新事论》)
冯先生的这些话是在半个多世纪前中华民族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候写下的,今天读来,仍然是感到振聋发聩,对其识见的高超、理性的睿智和分析的透辟惊叹不已。就其主张向西方与工业化有关的现代文化全面学习而言,表现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精神,与“本位文化”派的保守倾向判然有别。
就其对继往开来的展望而言,表现了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保存民族个性的执著,与“全盘西化”派的那种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迥然不同。就其对中国当务之急的认识及其所设想的具体的改革步骤而言,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完全是一种现实性的切中要害的思考。
与以上两派停留于“乌托邦”层面的专尚空谈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也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冯先生把中国现在所经之时代定性为转变时代,过渡时代,清醒地估计到这个过程必然是曲折艰难,表现了一种高度的预见性,更是发人深省。
所有这些真知灼见贯穿了一条一以贯之的思路,这就是“别共殊”。冯先生根据这条思路,设计了一个“中国到自由之路”的现代化的模式。这个模式凝结了冯先生的根本关怀和哲学抱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个比他的纯哲学系统更有时代意义也更有永恒价值的探索成果。
50年代以后,冯先生对自己的新理学的体系作了自我检讨,不再坚持了,对自己早年所精心设计的现代化的模式也不敢再提了,但是,面对着当时的那种铺天盖地众口一词的批判浪潮,冯先生对自己的那条“别共殊”的思路却是情有独钟,始终不肯放弃,并且通过各种隐晦曲折的形式随时表现出来。
比如1957年所提出的“抽象继承法”,60年代所提出的“普遍性形式”说。后来从事《新编》的写作,又把“别共殊”的思路提升为贯穿于全书七册的指导思想,反复申言,关于普遍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道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贡献,他要把这种贡献发掘出来,作为未来新哲学的养料和资源。
实际上,在冯先生的心目中,“别共殊”的思路不仅具有哲学史的意义,而且是与如何妥善合理地解决中西古今文化的矛盾冲突紧密相连的,一当政治环境变得较为宽松,学术自由得到应有的尊重,冯先生的思考也就很自然地又回到时代主题上来。
到了晚年,冯先生对他一生的哲学经历进行总结,把他在各种艰难险阻的条件下始终坚持的“别共殊”的思路表述为一个“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命题。
在《三松堂自序·明志》中,冯先生说:“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
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思想,既听取赞扬,也听取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销,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屈原《离骚》曾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冯先生在这里所表述的心态,和屈原是完全相通的。
由于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是如同冯先生早年所说的,“是生产家庭化底文化,转入生产社会化底文化之时代,是一个转变时代,是一个过渡时代”,究竟选择何种道路、采取何种模式来顺利地促成这种转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在中国的思想界关于文化的讨论是波澜迭起,屡现高潮。
80年代的讨论是“五四”的继续,90年代的讨论又是80年代的继续。在这场长达整个世纪的讨论中,尽管各个时期涌现出各种不同的主义和各种不同的观点,五光十色,纷然杂陈,就其所持的思路而言,归结起来,不外乎三派,一派是“全盘西化”的激进派,一派是“本位文化”的保守派,另一派则是介乎二者之中至今尚无确定学名的中间派。
这三派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争论得不可开交,就其所争论的焦点而言,实际上仍然是如同冯先生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如何“别共殊”的问题。
如果仅仅局限于纯哲学的层面,关于共相寓于殊相之中而结为一体的观点,这三派是不难达成共识的。但是,从纯哲学的层面进入到实际的生活中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现实利益的驱动,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起来。
人们往往是把特殊的说成是普遍的,又把普遍的说成是唯一的。如果在实际的生活中,中国仍然处在过渡时代,没有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看来这场争论还得继续下去,我们也很难对这三派作出一个判定其是非的结论。
当此世纪之交反思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进程,我们对“全盘西化”派的历史功绩有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对“本位文化”派的良苦用心有了如实的同情的理解,承认是另一种启蒙,据此而言,对冯先生的超越于这两派之上的“别共殊”的思路,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正是由于这三派的互动互补,形成一种必要张力,才推动了中国现代思想不断谱写新的篇章,向前迈进。而冯先生这条独树一帜的思路随着历史的进展也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给后人以启迪。
作者:余敦康,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曾参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秦汉卷和魏晋南北朝卷的写作,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已出版的著作有《何晏王弼玄学新探》、《易学今昔》、《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诠释》、《中国哲学论集》、主编《易学与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