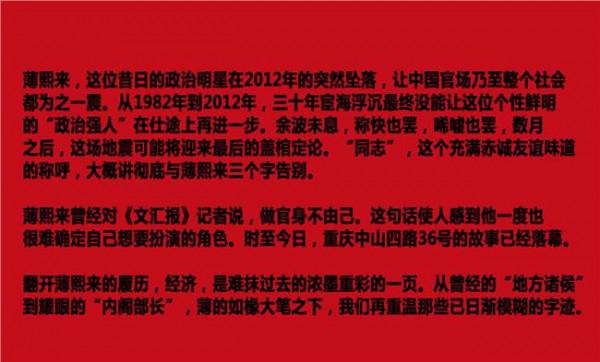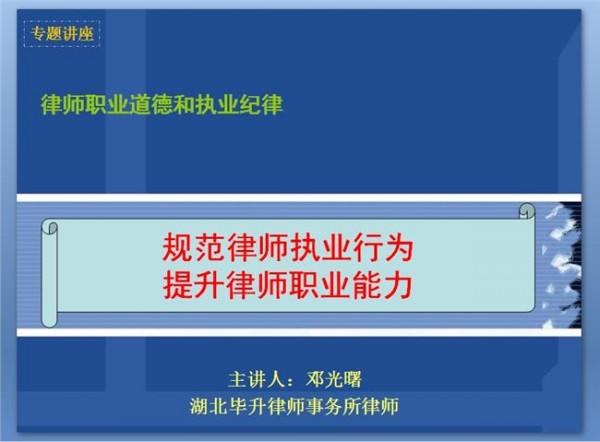如覆薄冰 薄熙来律师:获其信任很难 说如履薄冰不夸张
最终为刘志军辩护的是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列阳和他的助理娄秋琴。钱列阳196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从1994年开始从事专职律师工作,曾经承办2000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2006年的南京市委原书记王武龙受贿案,2010年的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受贿、滥用职权案等影响较大的案件。
钱列阳接到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为刘志军辩护的通知书,是在2013年2月1日。“因为法律上有规定,如果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必须要有律师辩护,就如同未成年人必须要有律师辩护一样。如果自己不肯请,那就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钱列阳说,法律援助中心也没有对他做什么特别交代,一切与他承办的其他法律援助案件无异。相比普通刑事案件,这些指派案件收入很少。“按规定,指派案件每个阶段的律师费是1200元,如果两个阶段连起来,则第二个阶段减半。
比如刘志军案,审查起诉阶段是1200元,审判阶段是600元,加起来1800元。”钱列阳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开玩笑说,“我一次次开车跑到昌平小汤山的秦城监狱,光油钱就得好几百。但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的案件,我作为律师是不能拒绝的。”
2013年2月6日,钱列阳前往秦城监狱,第一次会见刘志军。双方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钱列阳向刘志军简单介绍自己后,刘志军看了看他说:“审查起诉意见都对,我签字。”钱列阳明白了,刘志军不相信法律。“薄熙来相信法律,他不相信。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进来两年了,他不知道法律有什么用,也不想找律师。我是他见的第一个律师。”
会见中,刘志军非常抵触两个话题,一个是法律,一个是高铁,他说“谈法律头疼,谈高铁心疼”。他和钱列阳谈历史,还向钱列阳推荐了一套书——作家岳南2011年所著的《南渡北归》,讲的是近代文化名人梁思成、林徽因、胡适、傅斯年等人在乱世中的颠沛流离。从秦城监狱回来后,钱列阳特地买了一套。厚厚的3本,他认真研读起来。
第二次见面是2013年春节后,刘志军仍然回避高铁和案情。“他反复说,‘对我的指控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最好的辩护是不辩护’。他不仅自己放弃辩护,叫我们也放弃辩护。”钱列阳打了个比方,“刘志军的态度就好比是,‘这是一杯啤酒’,我已经签字承认了。那你就站在‘这是一杯啤酒’的基础上来说,别打开盖说这是茶。”
但钱列阳后来变得“强硬”起来,他对刘志军说:“抛开刑事责任,你为高铁做的工作我很尊重。也请你理解律师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为被告人做辩护,即使你都认罪,我也要做罪轻辩护。既然我尊重你,你也得尊重我。”刘志军听从了他的意见,双方的话题终于转移到高铁上。后来,再与钱列阳会面,刘志军表达了歉意:“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见时,我有点失礼了。”此后直到庭审,刘志军都很配合律师的工作。
外界曾盛传刘志军极为迷信,喜欢占卜。最后一次会见时,钱列阳的助理娄秋琴决定问问这个问题。意外的是,刘志军没有回避。“他说每次高铁开工前都会找人选个黄道吉日。以前没选好,开工就会下雨;选好了,就没下过。”
有铁道部的老同志曾回忆刘志军霸道蛮横,“想用你时你就升,不想用你时你就滚,有时三更半夜把你喊来开会骂一顿,让你摸不着北”。身陷囹圄之后,刘志军终于有所反省。他跟钱列阳说:“曾有一次,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告诉我,人要等到60岁以后才懂事。我一直没明白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终于明白了。你看我今年(2013年)60岁,我现在才开始懂事。”
2013年6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刘志军案进行庭审,只用了3个半小时。时间之短,出人意料。有人质问:该案有没有进行真正的辩护?钱列阳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其实在庭审之前,已经开了庭前会议。“很多人不知道有庭前会议这回事,我们扛着投影仪、带着案卷到秦城监狱开了整整一天,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参加。
该做的都没有省略,控辩双方争议的许多内容在庭前会议上已经处理完毕。如果没有庭前会议,都集中到法庭上审理,至少要两三天。”
“到了庭审时,控辩双方的辩论主要围绕两笔共计4900万元的钱款怎样定性展开。这两笔钱款是丁书苗为刘志军办事支出的,我们认为,刘志军并没有成为这两笔钱的所有权人,能否认定为受贿在刑法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钱列阳说,双方就此辩论了1个多小时。
2013年7月8日,法院最终认定,刘志军虽未直接占有那两笔钱款,但其行为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性质,据此认定刘志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并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志军对被指控的事实和罪名都没有提出异议,并表示不会上诉。
刘志军的妻子曾希望钱列阳“保刘志军不死”。当她得知是死缓时,对审判结果“很满意”,并一再向钱列阳和娄秋琴表示感谢。钱列阳说,按惯例,刘志军日后会获得减刑。“两年以后,死缓一定会转成无期,服刑若干年之后再转成有期徒刑。这并不是刘志军、薄熙来这些高官享有的特权,所有被告人都一样,这也是国际惯例。”
目前,钱列阳手头上还有几个涉及政府官员的案件,但他认为,“隐私权高于知情权”,在审判之前不能向记者透露案件任何信息。
王耀庭,让陈希同重新认识法律的价值
与前面的3位律师相比,王耀庭的资格更老,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律师之一,有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以刑事辩护见长。早在1993年,王耀庭就曾代理过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案。1997年,王耀庭因代理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而闻名业内。钱列阳等人提到他时,都尊称他为“前辈”。
据说,王耀庭走上法律道路,是受一部电影《历史的教训》启发,电影讲的是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庭上慷慨激辩,驳斥所谓“国会纵火案”的指控。上世纪60年代,王耀庭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把这部电影看了十几遍,萌生了做中国的“季米特洛夫”、当大律师的梦想。
1976年,“文革”结束后,司法机关人才紧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从“市优秀教师”的行列里发现了口才、文笔俱佳的王耀庭,将他调入法院。后来,王耀庭成为北京市第二律师事务所主任。
据《法制晚报》等媒体此前的报道,王耀庭成为陈希同的辩护律师,还得从他打赢的一场官司说起。1991年12月23日,两名年轻女顾客在国贸中心所属的惠康超级市场购物,遭到两名男服务员无端怀疑,被解衣、开包检查,查实无辜才得到放行。
此事被媒体报道后,评剧演员新凤霞的丈夫、剧作家吴祖光写了一篇评论《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职工》,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不料,国贸中心以吴祖光侵害其名誉权为由,提出诉讼。吴祖光于是聘请王耀庭作辩护律师。
王耀庭以“正当的舆论监督应受法律保护”为由,打赢了这场官司。从那以后,王耀庭和吴祖光、新凤霞夫妇成为朋友。1995年,王耀庭决定离开“公立”律所,自办合伙制律所,吴祖光给他的新律所取名为“逢时”。
上世纪90年代,陈希同的秘书陈建因涉嫌受贿被捕,陈建的家人正巧是吴祖光的朋友,他们请吴祖光帮忙推荐一个好律师,吴祖光就把自己信任的王耀庭介绍给了陈建。不久,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因涉嫌挪用公款、受贿被捕,陈希同的家人又通过陈建的家人联系到王耀庭,请他作陈小同的辩护律师。到1997年,陈希同案进入法律程序后,其家属再次找到王耀庭,请他继续为陈希同辩护。
陈希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六个被送上法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他5人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陈伯达)。所以,这起案件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密切关注。但是,大量的媒体曝光,让公众形成了“未审先判”的心理,这给辩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到底该不该接手这个案子?王耀庭内心有过矛盾。十几年的从业经历告诉王耀庭:如果律师的加入能使本案的审理更加客观公正,对中国法治进程来说,这就是一个契机。于是,1997年9月30日,王耀庭接受了陈希同家属的委托。
但是,陈希同本人的态度十分消极,对律师抱着怀疑和抵触情绪,总是说“爱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吧”。王耀庭在会见陈希同时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我跟陈希同介绍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历程,律师的作用,也列举了一些律师辩护成功的案例。我告诉他:‘努力,而不是等待。’”陈希同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在律师委托书上签下了名字。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王耀庭仔细研究案情,为陈希同制定了辩护方案。
1998年7月,陈希同案一审开庭。根据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庭审节录,审理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陈希同在对外交往中接受的礼物,是否都转交给了外事部门,有无占为己有的情况;另一个是陈希同指示和纵容王宝森擅自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八大处和怀柔范各庄新建两处豪华别墅,是否存在玩忽职守的罪行。
前一个问题,陈希同在大量的物证面前,承认了自己接受礼物,但否认自己占有,说打算将这些礼物转交给北京市政府外办,或捐赠出去。后一个问题,对那些豪华别墅,他承认“反正都已经盖了”,但又称“我没有私人占有”,并请求法院核实。
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陈希同情绪低落,已经没有上诉的欲望。王耀庭受陈希同家属的委托,再次与他会面,帮他分析利弊,说服了他同意上诉。当时有人问王耀庭,上诉能改变原来的结果吗?王耀庭说:“我做的事,意义在于未来。”
在二审中,王耀庭根据“事实证据之外,还要看主观方面”的原则,提出陈希同占有礼物方面的主观故意不明显,要求二审对有关证人证言加以核实;根据“一事不再理”(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诉和审理)的原则,提出陈希同已经以辞职承担了玩忽职守的责任,不应再承担刑事责任。但二审最终维持了原判,对这个结果,王耀庭很坦然,认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王耀庭的辩护也令陈希同重新认识了法律的价值。案件审结后,陈希同希望王耀庭继续担任他的私人法律顾问。王耀庭说:“给陈希同这样的特殊人物做法律顾问,工作繁琐,责任重大,弄不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对陈希同的要求,作为律师,我没有理由拒绝。”
在北京市司法局请示司法部同意后,王耀庭担任了陈希同的私人法律顾问。那以后,王耀庭每周都要与陈希同会见。陈希同遇到法律问题,王耀庭会随时赶去,提供法律帮助。王耀庭说:“我是一个最看重律师职业道德的人,我既然做了陈希同的法律顾问,就要尽心尽力为他提供法律帮助,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客观与公正。”2006年,陈希同保外就医。2013年,陈希同去世。王耀庭也淡出了辩护舞台。
为高官辩护体现我国司法进步
任何被告人,包括落马高官在内,都享有平等、合法的辩护权,这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内容。落马高官的辩护权从无到有、从不充分到比较充分,这个变迁过程,正是我国司法进步的缩影。
如今,薄熙来、刘志军、陈良宇等人有律师为他们辩护,而他们的“前辈”——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专员张子善等就没这样的待遇。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明令取缔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组织和律师活动,由此否定了律师辩护制度。
1952年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的刘青山、张子善,不但没有律师辩护,连自行辩护也没有。刘青山说:“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拿我当典型,处理我来教育全党……在历史上说也有用。我不求饶,死了比活着有价值。”
直到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才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具体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从而在立法上对辩护制度予以肯定,我国新的律师制度才得以建立。
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尚不健全的辩护制度再度奄奄一息。大多数辩护律师被认为“丧失阶级立场”“为坏人说话”,被划为右派。“文革”时期,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辩护制度彻底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后,198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委托律师等为其辩护。该法被钱列阳称为我国“第一代刑事诉讼法”。此时适逢中央准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进行公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还为此成立了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
司法部则指定了4名律师,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并被指定为江青的律师。
据张思之回忆,江青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不是法律审判”,她十分嚣张地对法官说:“我怕过谁!”还在法庭上高喊那句当时的流行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由于当事人的不配合,在审判江青时,律师的辩护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经过辩护,张思之带领的“两案”辩护律师组为姚文元、李作鹏、吴法宪等5人免去了13宗罪行。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王耀庭代理陈希同案轰动一时,但“启蒙作用”有限。本世纪初,落马高官在审判时依然讲究“淡泊明志”“不跟党辩论”,不懂如何行使法律赋予的辩护权。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判死刑。
他说:“我一直表态说不请律师。犯了罪,我负法律责任,接受国家的一切处理,不需要辩护。我不愿在法庭上与党辩论。我年纪已近古稀,不会再给党抹黑。如果法律规定必须请,我就请。”2004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的态度则是:“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
从行使辩护权的角度来看,在落马高官中,陈良宇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一方面,他和律师积极配合甚至“演戏”,另一方面他又同以前的高官一样积极认罪。此案过去5年后,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该法进一步维护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比如,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材料之日”提前到“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
钱列阳认为,随着立法上对辩护制度的完善,能够利用辩护权来保护自己的落马官员的比例在升高,目前约占一半左右。钱列阳尤其提到了薄熙来案的重大意义,“抛开薄熙来的犯罪事实和他造成的危害不讲,控辩双方的庭上激辩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是个典型的例子”。现在,钱列阳为政府官员讲解职务犯罪的法律知识时,课堂上静得出奇,官员们都在认真记笔记。
但目前,为高官辩护仍然存在一些困难。首先是有些高官“自暴自弃”,认为不管有没有律师,不管谁担任律师,审判结果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对此,高子程认为,“不能因为被告人的态度,就轻易放弃被告人最大程度的合法权益之追求。
律师对刑事法律的了解程度,对事实、行为性质的判断水准和准确度,要高于被告人,所以要保持独立辩护,不受被告人观点左右,也不受办案机关的观点左右。如果律师一开始就顺从被告人和办案机关,那辩护的意义就丧失了,就像医生无原则地顺从患者和家属,治疗的意义就丧失了”。
在高子程经手的案件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高官案件并非“难以改变结果”——2009年,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被控受贿近2亿元,被判处死缓;而同一时间,被控受贿1亿多元的首都机场集团原总经理李培英、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均被判处死刑。高子程为陈同海辩护时,调取了50多份新证据,证明其中1.5亿元受贿款有疑义,为陈同海争取到了缓刑。
王兆峰也谈到,正因为“高官案件受到各方的影响,有些环节上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有‘未审先判’的心理,觉得‘过程中的某些东西马虎点没关系’,证据的收集整理工作有时还未必有普通案件做得好。这就恰恰需要律师好好分析、甄别证据,将问题梳理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律师在这类案件中的发挥空间更大一些。”
其次,律师“取证难”仍然制约着他们为高官辩护。王耀庭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律师归法院领导,享有干部身份,是占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在办案过程中享有充分的取证权和会见被告人的权利,那一时期堪称律师职业地位的“黄金制高点”。
但在1997年,律师法将律师由“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变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同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律师等“社会中介机构”要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律师与法院取消“身份绑定”后,律师界通称的“三难”问题开始暴露——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造成“三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和民众以“无配合义务”等为由阻碍、拒绝甚至故意刁难律师调查等等。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针对这“三难”做了细化规定,明确了相关责任人的义务,辩护律师的“三难”困境开始有所改变。律师与薄熙来会见了几十次就是一个例证。
在钱列阳看来,辩护律师就像天平一头的砝码,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制约公权力;而公诉人打击犯罪,好比天平另一头的砝码;中间那根轴是法院,两头的砝码互相制衡,才能达到司法公正。“2014年是我执业的第二十个年头,这20年来,让我感到特别欣喜的是,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的专业素养都在提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案要案的法庭辩论,有时就像是在开批斗会,法官、检察官集正义与力量于一身,非常亢奋。现在,我们越来越习惯就案论案,就法论法。无论高官还是平民,无论办案人员还是辩护人员,如果每个人都相信法律,有很强的法律意识,让法律事实更接近客观事实,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就更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