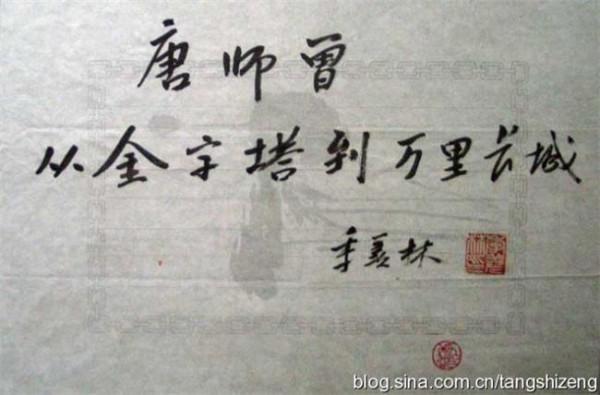一段曾湉 【梦想对话】第44期:曾湉 只想好好说“一段”话
1.《一段》这种声音剧场形式是怎么来的?这个名字是如何选取的?
声音剧场这个概念是我的一个尝试,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这种表演样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对于舞蹈剧场的解释——其实这个概念在东方国家我们会觉得是一个实体的空间,而在西方的语境里面它其实可以泛指在剧场环境内所发生的一切,这个概念讲的大概就是在剧场里面的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中的动作提炼,而且都是碎片化的,没有一以贯之的剧情,然后再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在这个剧场的空间里发生的一种新的解释样态,来展现我们的生活、情绪和状态等等。
其实在这里,舞蹈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实化的体现,那么我看到这个概念之后我就觉得和我做的事情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只是说我没有用到舞蹈这样的肢体语言,我是用声音做了一个重要的载体,所以我想,也许"剧场"这个名字可以用来作为我所做这种艺术实验的定义。
关于《一段》取名,开始也想了很多矫情的名字,什么虚头巴脑的都有,后来有一天我和编剧很多人在开会的时候,我突然说:“我们今天开会重复率最高的就是‘一段’这个词,因为我们的故事是碎片化的,我们永远都是在找这一段和那一段怎么接,如果再有一段什么样的最好,那不如我们就叫‘一段’吧。
”我们不要去抽象某个概念,“一段”比较接地气,简简单单。同时,它也确实代表了人们生活的一种状态,我当时就随口一说:“你看,叫一段,再深再浅的爱情都是一段,再长再短的陪伴那也是一段,你每个人的经历不管再痛、再悲、再喜也好,它也都是一段。
”我就发现,整个演出的架构就已经出来了,其实说它简单它非常简单,你可以说一段文字,一段话,一段故事,都叫一段,要说它抽象其实它也抽象,人和自己的每一段经历,人和人之间,人和事等等,谁跟谁都是一段。
2.《一段》中包含了12个故事,这些故事是如何选取的?
在整个台本形成的过程当中,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顺势而为,我一直都在说,12个故事或者说12个碎片,首先它们都是现成的一些作品,有小说里面的片段,有随笔,但是,这些作品都不是我一个个找来,也不是求来的,它们都是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偶然机会里被发现的,用我的话讲,它们是一个个自投罗网撞进来的,它也许是我很多年以前看过的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突然想到了,感觉挺有意思的,再翻来一看,觉得不错的,我就会把它按照我的要求立刻在电脑里改编好留在那里,像一个片段,我随手翻一本书,可能那一页,越看越觉得有意思,也会立刻把它改编出来等等。
这样各种的机会,撞到我的身边,我就把它们留下来了。
那么至于说这12个片段怎样才会被我留下来呢,有几个标准:
首先,必须是第一人称的;
第二,要有非常典型的、具体的场景。我很在乎的是,当台上的演员在讲述一个东西,那么在他开口的10秒钟,台下的观众立刻就能知道他是在什么典型的场景里说了这样一段话。另外还要满足一个条件,虽然它只是一个片段,通过这个片段的一席台词,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故事,是什么人在什么场景下,我大概就能知道整个故事的背景,所有人物的关系;
第三:通过这个片段,这个人物的性格是真实的并且是合理的,而且是鲜明的,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归纳起来就是,我们14个性格各异的人在12个故事背景下,讲述12段独白或者是对白,换句话说,其实就像12段精简到只有一段台词的独角戏或对手戏。
3. 通过《一段》中的这些故事,您想给听众传达什么?
我想传达的是,这些所有的片段都是来源自于活生生的生活,就像当夜晚来临,你站在自家门前望对面的那栋楼,有12个窗户,而每个窗户里都有不同性格的人,他在自己的空间里进行着自己的生活,他有他的故事;也许推开这扇窗口你看到的是一个厨房,在厨房里母子两个人正在争论关于吃饭的问题;推开另外一个窗户,你看到的是一个老人孤独的正在想自己的心事;又或者你再推开一个窗户,是一对年轻的情侣正在谈恋爱或者是一个正在忙于工作的人,正在那加班等等,所以就像12扇窗户里14个性格鲜明的人,在里面进行这12种不同的生活状态,这就是《一段》选取故事的基本情况,所以说,这些片段就像是你邻居家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煽情、不矫情、不拔高,也不去追求虚头巴脑的东西,我们就脚踏实地的说点生活中的真实。
4.您说声音是有表情的,怎么理解?
我发心回到根上,我是觉得我们可能看了太多虚张声势的东西,貌似深情但其实里面的情感是没有根基的,那么我特想说,声音是很厉害的,如果你闭上眼睛,不借助画面,你只是去听,把听觉发挥到极致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声音里听到年龄、表情、动作、性格等等。
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当我们好好说话,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时候,其实声音是极其美妙的,这种美妙和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貌似深情的那种表达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对声音的一种态度,非常简单。想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做出一台东西,整个这台演出是一个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就是代替我去表达什么是美好的声音。
5.您花了一年时间寻找到14个声音,你寻找声音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选择的标准,首先,名气大不大,和声音好不好听,都不是我的标准,而且跟煽情也没有关系,我一向认为,情就不是煽出来的,煽情就显得廉价。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手里的这些作品已经自成逻辑了,那么我就去为了这12个作品找合适的人,而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些人我并不都认识,甚至有的人完全没有过交集,我要为每一个片段去找就是它的那个人,而不是像,但是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就是直觉,等我找人家谈作品的时候,很多时候惊人的发现他本人的经历与故事里的主人公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是我在不止一个作品为它找到演绎者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情况,我觉得很神奇,所以有时候,我会问到:“你是不是挺喜欢这个作品的”,人家会回答说:“我不是喜欢,它就是我啊。
”所以我说,我相信自己直觉,那么这些人,这些声音,我不在乎天生的音质好不好听,他们有的甚至没有受过某种专业的训练,这对我来说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这个作品里的主人公是否贴合,他的吻合度是不是高。
6.在寻找这些声音的这一年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或感动的事情?
在这一年当中,有很多细节都印象深刻,比方说,当我找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做在一起来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创作道路上的某种共同的认可,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情。比方说,我第一次去找廖菁老师的时候,我说我要做这个事情的初衷,我讲了自己的发心,我能明显看到廖老师眼睛里闪烁着被某种共鸣激发的泪光,然后拉着我的手说:哎呀!
如果真的能把这件事情做出来,那就太美啦!再比如说,李野墨老师,我那天跟他谈这个事情,谈完从他家里出来,我记得已经快夜里12点了,他送我下楼,在车子启动的那一瞬间,他站在路边挥手,大声对我说:祝我们成功!
然后再比如说,像冯宪珍老师,韩童生老师,他们这次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参与,但是在这过程中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情真意切给予我很多肯定,这些细节都历历在目。
我甚至把老师们在各种时候发给我的一些短信息都保存了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都是一些极其珍贵的瞬间,像一盏盏灯,其中包括一个非常著名的配音演员,王蕙君老师,她虽然这次没有能够参加,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接到她的短信说:“曾湉,我哪天在北京,我不用开工,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我愿意给你提供我所能提供的帮助。
“我说:”王老师,那我真的会带着问题去找您啊。“结果王老师说:”拜托,不是你带着问题来找我,是我求你带着问题来找我好吗!
“我觉得老师们的这些瞬间,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压根我做这个事情就没想太多,我只是觉得,我想为我所热爱的专业和为我所热爱的声音做点事情,用这台演出来替我表达我的一种态度:就是声音它是有表情的,饱含深情的东西不是煽出来的,它是在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7. 这些演员的声音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您在寻找这些声音的时候,是否了解过大家对于《一段》的期许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是“想好好说一段话的人”,至于大家对《一段》的期许,说实话,没有了解过,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其实我挺任性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在我们排练、拍宣传照的时候,会有一些摄影师,剧场的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次听见这些段落、这些碎片的,有好几次,老师只是简单的说了几句,摄影师就说:“老师别说了,我要掉眼泪了。”每到这种时候,剧场的工作人员就会问我:“曾老师,这个编剧是谁啊?”我说:“怎么了?”他说:“好好啊,刚才有好几个片段好感动。”这显然我们没有去煽情,我们只是很本分的浅浅的淡淡的说了我们想说的话。
就像之前我说过“饱含深情的每一天,它看上去都是寻常的”,所以我们只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了我们想说的话,在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故事,说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淡淡的说,这个东西就像喝了一杯白开水,但非常解渴。
8.您说《一段》是一个“艺术实验”,那么您对这个实验的预期是什么样的?
不敢谈预期,也没有预期,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实验性的做法。我们所有的主创脑子里其实都有无数个问号,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往前走,包括所有的演员们,我们所有人在一起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实验,所以我说这是一场艺术实验,我们尽量的让它接近自己原先想做的那个样态,但是那个样态,就像声音剧场这个词不太容易理解,就像舞蹈剧场刚产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无数个问号需要我们去解答。
而恰恰有了这种未知,有时会给人恐惧,但是未知也是会让人觉得有盼头的一件事情。
我们整个主创包括导演、我还有所有演员,灯光,舞美,我们都是共同地在做这一个实验,也正是基于这个,我们先做3场看看吧,看看到底能否呈现出一个气质能忠实或无限接近于我们一开始的想法的东西。
而且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合适的词来描绘它的时候,竟然得到了那么多朋友的关注和支持,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荣幸,也是极大的惊喜,我希望做出来的《一段》最后的呈现能无限接近于我的发心,那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成功了,之前冯宪珍老师说“祝我成功“,我当时跟冯老师说“成功不是我的目的,呈现才是我的目的,我要尽可能地让它接近于我的想法,按我本源的想法去呈现。”
我一直挺相信一句话“我们尽力把眼前的事情做到极致, 那后面的美好就会自然呈现”。其实至于这个美好,它呈不呈现,有没有之后的美好,对于我来说,我现在不想这个事情,我就是觉得,按我的想法去做,做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如果有以后的话,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像一颗种子,哪怕它就是一颗种子埋在那里,那它至少也有发芽的可能性吧,这个发芽我不是指带给我们一些实实在在所谓的物质上的这些回报,这些都不重要,我指的是,我们所有这些人的艺术理念得以生根发芽。
9.《一段》是一个新形态、新事物,免不了遭受质疑,你如何看待他人的质疑?您退缩过吗?
我觉得这世界上不存在一样东西是可以被所有人都说好的,要辩证地看待这个事情,任何事情都有质疑与肯定,所以这对于我来说,我都是有准备的,而且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更别说对于一个新的事物,更需要时间让人去接受它,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对我来说,我都不会退缩的。
其实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负能量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从他们各自的经验角度出发,告诉我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商业属性,票房上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或者甚至说,你不要做啦,这个事情不会有人喜欢的,谁会来看啊,等等吧。
一个人提出质疑,你不会觉得什么,两个人,提出质疑也还好,到三、四、五个人都来说,而且都是从专业和经验的角度来说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有波澜的。但是,我从来没有退缩过,我记得哪怕被说得最惨的时候,人家直接说你不要再做了,你自娱自乐玩玩还成,你干嘛要做这个事。
我记得当时,就是出现了生理反应,我突然变得特别恶心,特别想呕吐,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但记得当时我可能也挺倔的,别人问我:“你再想想要不要做”,我说:“你要我想什么呢,你要问我想不想做这件事,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不用想,我一定会做,而且我一定让它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尽可能地去实现。”
我觉得质疑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像说傻阿甘一样,如果说即使你做完了,还是有人说你干了一件很蠢的事,但是只要自己不觉得蠢就无妨。就像我老公说的:少数派是荣耀。
在台里的时候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怪人,可能是因为我比较遵从自己的内心吧,别人眼里在乎的事情好多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事情可能在他们看来也挺匪夷所思的,所以,我没有退缩,也不必退缩,质疑嘛很正常,当别人说我是怪人的时候就已经是质疑了不是嘛,不过无所谓,我反倒觉得这是一件挺值得荣耀的事情,证明了我很专心的和自己在一起。
10. “愉悦地做一件事情”,如何能够做到愉悦大众(迎合市场)呢?您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说实在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太想过,我没有去刻意权衡过所谓自己愉悦和大家都愉悦之间该如何去把握这个分寸,我做这个事情的发心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我要表达我的态度,这些老师们愿意无条件的支持我,我们站在一起,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的发心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要一起来试一试按我们的态度和理解,把这个故事说出来,看看是不是能打动更多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至于怎么权衡这个关系我真是无法回答,因为起根上我就没有想过如何去权衡,有时候我说勇于自省,但是我永远任性。
但是有一点,我所有创作的出发点,我主张的创作概念,就是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是要源于生活的,是要真真实实扎根在生活里的,它是从生活中长出来的,就像12个窗户里面有12家人,他们过着各自平常的日子,所以,你一定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阳春白雪,这肯定不是。我认为《一段》至少是我自己的一个出发点,是极其接地气的,我们讲的就是你家邻居,你生活的某一个侧面,所以,这不是我主动去迎合,我觉得接地气是我的一种创作观。
11. 央视是播音主持梦寐以求的平台,属于金字塔尖式的工作,离开这样的岗位,从事一个需要从零开始的工作,您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从台前到幕后,您的心态历程是什么样的?
我从小到大一路都是那种好学生,价值观里被赋予了太多共性的东西,就是你似乎觉得大家都视为目标的目标,就应该是我的目标,大家都在争取的东西,我也应该去争取,其实明明心里也许并不乐意,但是你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我在央视平台上干的不错小有成绩。但是,我一直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因为我明明知道自己不会很开心,甚至说有很多焦虑、疲惫等等,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忘了是在哪听来的还是我怎么就突然想到的——“有能力做和是不是愉悦的做,是两个概念”,我其实在学校学习的时候,语言艺术是我非常笃定喜爱的东西,而不是新闻方面的,那么我要去做我愉悦的事情。
其实离开央视之前的几年,我就已经慢慢的有了这个想法了,而我们现在做了父母,你会看到自己的孩子,你会有更多的意识,觉得是我要保护他天然本性的一些东西,保护他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力,但是我觉得,客观的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相对来说抹杀个性、树立共性的东西多,但共性这个东西有时候也挺讨厌的,它会让你失去对自己的判断或者说我不太敢承认对自己的判断,我明明不高兴,可是觉得我得这么做。
我可能是被二次激发了我个性里的某一种任性的东西,或者是对自己的认识,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好朋友,还说我“你身上有一点点人之初的东西”。
当然,我会把它理解为褒奖,说白了,我身上有一点点挺轴的、挺二的、挺楞的东西,我没有想太多,我就是比较简单。
所以当我突然意识到,我每天从事的工作虽然被很多人羡慕,但是我自己做起来并不开心,它并不能给我愉悦感,也并不能满足我精神上的需求,我不爱它,既然这样那好吧,那就让我去做我特别爱的事情,遇见爱的事情我就能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歪点子冒出来,不管靠谱还是不靠谱,我还是会很激动,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巨大的愉悦。
像我现在做这个演出,工作量也很大,尤其是临近演出了,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但这个过程并不会让我觉得从精神上觉得焦虑,因为我做这个事情,我足够爱它,所以我完成它的愿望就足够的强烈,我眼睛看着那个目标,在抵达目标之前的所有遇到的波折,在我这里都是可以克服的,并且我心生愉快的去克服它们,因为我的眼睛永远盯着前面,而不会被眼前所有的这些困难、波折所困住,这种动力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这就是因为你爱,你特别想做。
像我老公说的“人特别难得会非常非常想做一件事,这种状态恐怕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一辈子不会有几次。”
所以有时候我会讲,我离开央视,跟央视无关,不是因为它不好,纯粹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跟它尺码不合适,也不是说因为一些别的,就是因为我想做我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12.您在央视的工作描述为“一个好学生的坚持”,那么如今对于《一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坚持”?
我觉得不需要坚持,因为你足够爱嘛,你想做这个事的愿望足够强烈,所以不存在坚持不坚持,你哪怕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你也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你为了做这件事情你要先完成去做很多你不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会觉得把这个过程是在坚持,因为一提到坚持这个词,我认为它带着某种悲壮的色彩,或者说不情愿的色彩,你才会觉得是在坚持,坚持是挺苦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足够想做一件事情,你的愿望足够足够强烈,那你就不会有悲剧色彩在里面,你一定是极大愉悦的,即使这个过程会花费你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是这些跟坚持没有关系。
就像我很喜欢的一个舞蹈家希薇·纪莲,她就说她每天花费在练功房的时间很长,但是好多人也都说练功很苦啊,可是她说:我压根没觉得这个过程苦,因为我每一分钟都很享受愉悦。
我为了做《一段》把这个演出呈现出来之前,我要先学很多我不擅长的,还要解决掉很多不擅长的工作,比如说我要去找个剧场,我要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细碎繁复的工作,这些我都不擅长,但是为了要做我想做的事情,这些我都可以克服,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觉得是在坚持,而是每取得一点进展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愉悦的。
13.您说自己是个“有情怀的疯子”,而创业成功也正需要这种“死磕”精神,您想对其他创业者或其他怀揣梦想的人说什么?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确实有死磕的精神,我觉得就是要做打心眼里让自己愉悦的事情,做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不要被太多所谓的普遍意义上的成功所迷惑,就算人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他的成功在你这根本不把它当回事。
而也许,你所谓的巨大成功,对他眼里也什么都不是,因为人生不同,所以一定要去努力的发现和找到自己打心眼里想做的事情,就像我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歪点子,也许还会止不住的往外冒,而这个过程是非常让人觉得享受,如果你真的怀揣什么梦想的话,那就要去努力发现和寻找自己打心眼里愉悦的事情,然后去把它做了。
我压根没觉得自己是个创业者,虽然好多人说离开央视你创业了,也许事实是这样吧,但是我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创业者的心态,我没觉得自己是在创业,我只是觉得我像一个手艺人一样,我去打造一个按我的想法实现的一个作品,至于实现了作品就意味着什么?它能不能带来什么这都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没有想过,所以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创业者,包括有记者也采访过我,上来也是从创业者的角度,但是采访结束的时候都会说:曾老师其实您真的不是一个创业者,“好吧,我真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