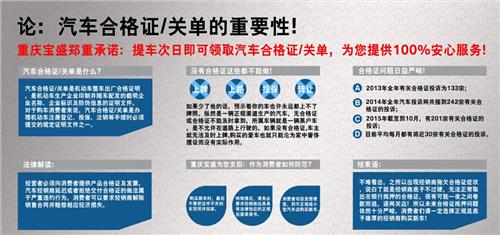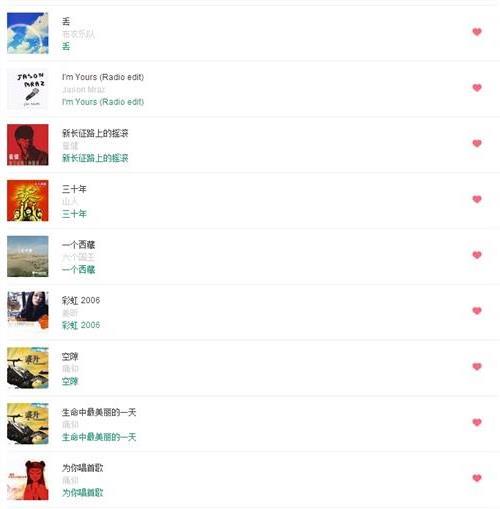张玮玮和郭龙 张玮玮:把专辑拿出来 才能和它告别
这是 2012 年 5 月 27 日。一早张玮玮起床后直奔西北饭馆,吃了一大份臊子面。“今天一起来的感觉就是——啊,世界就在脚下。走起!”而郭龙则打开了电脑。“(微博)挣了 70 多个粉丝,昨天回去 380 多条 @我。”
他们刚刚经历了“坎坷的乐手转型之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前晚,也就是 5 月 26 日,张玮玮和郭龙筹备了四年的创作专辑《白银饭店》在北京麻雀瓦舍首演。玮玮说:“感觉跟考试一模一样。”
事实证明他们不仅通过了考试,而且成绩斐然。当晚,六百张预售,二百张现场票、四百张碟全部卖空,刷新了麻雀瓦舍的票房纪录。“我一上台一看,观演关系不对劲,以前麻雀的距离特别合适,能模模糊糊看到前排的人。昨天,十多排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舞台灼热的灯光中,玮玮向观众讲述了近来某日失眠的夜里听隔壁打电话的故事。
“特别紧张,也累,但其实是大释放。”
听音悦:张玮玮:我们终究都会离开家
我们的采访发生在北京的江湖酒吧,面前的玮玮和郭龙都还穿着昨晚演出时的衣服。近看才发现,郭龙道长 T 恤上的“好人”左上角,其实藏着“我不是”三个小字,他露出一个闷骚的坏笑:“低调。”而玮玮身着白衬衫,儒雅如胡适,近两小时的讲述风趣而诚恳。“我今天能说那么多话,就是跟我昨天释放过有关。”
这的确是一张凝结了太多意志力的专辑,四年的光阴里,每一个音符和文字都一遍遍打磨着两名歌者的内心。这也是一场与自己的较劲,有摸索有咬牙,但最终不论哪个自己胜出,都是向过去郑重其事的告别。
关于狂欢之后迷失的故事
《白银饭店》专辑内页文案四千六百字,在行将结尾的倒数第二页,玮玮写了这样一段话:“当我们背着乐器走在异乡的路上,多希望有个温润丰满的过往,可是我只有这个故事可讲。”其实玮玮可讲的故事太多,只是这次,他想通过《白银饭店》这张专辑,结结实实地讲一个关于狂欢之后迷失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北京,在白银,在每个不安分的青年的脚下。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们在河酒吧,一直玩到天亮。”玮玮的回忆像是被擦得锃亮。那天清晨,他和一个朋友站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带着狂欢后疲惫的身体和些许颓丧的情绪,两个青年对彼此倾吐着心事:“咱们都是没根的人。”
他们在北京一天天飘着,也回不去老家,因为没朋友,没事业,回去也无法生活。大家看似每天在一起喝酒唱歌,但“在一起”是个动荡短暂的东西,它只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着自己想去的地方,“转眼就散了。”
这委实调动起玮玮记忆里关于故乡白银的片段。
在玮玮所撰《白银饭店》一文中,白银被这样加以描述:“孤零零的白银,一张作废了的社会主义蓝图。五十多年前,远方的开拓者怀着响应祖国号召支援大西北的理想来到这里,他们从地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因此,白银很少存在真正的本地人,大家保有不同的口音、生活方式,在这里狂欢、喝酒、告别。
“有个人喝醉了,不停地对别人说他要走了,要永远离开白银了。大家很冷淡地任由他掏心挖肺告别,因为所有人都习惯了,这个人每次喝醉都要和大家玩这个生离死别的游戏,谁都知道明天醒来他仍然还在,哪儿也不会去。那个人就是我”。
从小到大,玮玮在相似场景之中周而复始。不论是最早的白银饭店,还是到北京之后出没的霍营、树村、三里屯河酒吧,再到后来的“民谣圈”,“总是有一拨人,特别好,然后没了。小河、(万)晓利、老周(周云蓬)我们这一拨人,其实现在也不在一起了,我跟小河都已经半年没见过了。”谈及此处,玮玮成了传说中那个忧郁的风琴手。生活动荡无根,他们希求在民谣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最稳定的东西。
专辑以白银做题,事实上却是玮玮和郭龙对“在北京十多年的一个交代”。一位名叫卡司的作者在乐评中写道:张玮玮离开白银在北京呆了 13 年,如今搬至上海,我似乎也明白了他写这些字,写这些歌,在每场演出之后唱黄河谣是为了什么。
每个缝隙都被熬着夜打扫过
在《白银饭店》首发活动论坛上发帖,有歌迷动情地留言:“终于等到了,泪流满面啊。”打磨了四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玮玮和郭龙比任何人都等得更辛苦:“第一次做专辑,压力太大了,把时间都浪费在纠结上。”
专辑里的十一首歌曲,大部份写于 2007 至 2009 年。事实上,它们的问世早于玮玮和郭龙专辑《你等着我回来》中的很多歌曲。
做之前玮玮想得很简单:绝对不分轨,绝对不打节拍器,15 天内搞定前期录音。“冬子录完,我还跟他说:‘你疯了吗,又分轨又打点儿花四万多块钱,咱们是民谣,哪用得着那么多?’结果第一版录完我给冬子打电话,我说:‘冬子,对不起,我为我当初跟你说的话道歉,我太浅薄了。
’”第一版录音完结于 09 年夏。“始终就是不满意,怎么都不满意。”经历了第二版、第三版的打磨,2012 年 3 月 26 日,第四版录音终于在万晓利家的工作台上竣工了。最后录制完成的这张专辑分了轨,打了点儿,严格执行了传统的录音标准。
万晓利导出的混音文件,玮玮截屏纪念并如数家珍:“白银饭店(正片)、白银饭店(新店)、白银饭店(再次混音版)、白银饭店(混音终结版)、白银饭店(混音终结吧终结版)、白银饭店(这是最后一次版)……”
混音是乐器摆出来的感觉,声音怎么处理。其实就是对歌曲的二次创作。《白银饭店》所有歌曲的人声是纯干的,只加了一个“板式混响”,就像对着一块玻璃说话,有一点点回音,而摒弃了常用的房间混响或大厅混响。“晓利给我听了好多例子。我俩听涅槃的那张《没事儿(编者注:Never Mind)》,他说:‘你听,科特柯本的人声一点混响没加。加混响大家肯定喜欢,但其实那个东西是骗耳朵的。大家必须得一起往新的方向走。’”
万晓利还调整了原有的编曲结构。譬如《秀水街》,他直接砍去原有的前奏,用合成器弹了一个圆号,之后把声音的位置移到开头,于是你便听到如下情景:一声长长的圆号从渺远处弥散开来,引着渐强的吉他,一点一滴渗入耳朵的空隙,营造出一种旷远的空间感。“他制作的和声也非常精致,不是摆在一个平面,而是好像远处有个窗户,人在窗户那边唱。”
5 月 28 日,玮玮以一条微博表达对万晓利的盛赞与感激:“万晓利为这张专辑的混音付出了近五十天的工作,这十一首歌里的每个缝隙都被他熬着夜打扫过!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万总,向你致敬!”
朕为这个本子操碎了心
说来也巧,翻了四版的不止是录音。“布的封面,可永久使用的腰封,十四页的连页,奏折与手风琴风箱灵魂附体。纯手工折制粘贴,十一首歌,九幅手绘图片,四千六百字内页文案。”说起这本子,总爱自称“朕”的玮玮,像是说起一位一表人才却常不从圣命的皇子。
奏折本子的原型来自琉璃厂,旧时用来请人题字。为显礼仪,求字画者不能单拿纸张,须整本呈上,题罢,喷水,便可裱做扇面。“特别早以前我就想好了,我的专辑一定要拿它做。”
实施的过程异常艰辛。印刷厂工人把它分解开,玮玮惊了:“以前我以为就是一张纸,其实它是两两相对,而且不是贴,而是双面裱起来的。”印刷厂也望而却步。终于,攻克了诸如布面翘角、字体间距、标题镶嵌效果等各种技术难题,以及诸如停电、工厂搬迁等人类不可抗力因素,首批 400 本专辑在 5 月 26 日麻雀瓦舍演出当天被抢购一空,之后又经历了暂时性的补货危机——“朕为这个本子操碎了心”。
翻开专辑的腰封和内页,你会看着那些个有点痞,有点糙,却很生动的人物小画像会心一笑。绘制这些画像正是玮玮的妻子,申申。“我俩刚认识的时候她就喜欢没事儿帮我画个头像,特喜欢把我的眼袋画的特别大,头发秃得特别厉害,但是特别好看。她会把我的一个眼睛画得往下掉——她说我们家人全是这样的,典型的蒙古眼睛。”
申申负责且不止负责整张专辑的视觉设计,所有的事情她都要帮玮玮张罗,费了特别多心血。“我俩桌子上一人一张纸,每天晚上睡觉前把第二天要干的事情全部都写下来,第二天起来就开始干完一条划掉一条。”
“有时候挺伤感情的,尤其是设计这种事,我要坚持这样的,她觉得那样好,能说谁是对的?到最后弄弄就不高兴了,然后俩人就随便吧。隔了半个小时,哎呀,再考虑一下吧。”
即便如此,仍难免有遗憾。在专辑内页的五个人头像旁边,有一窄溜儿折出来拼贴的接口。“就为了那个我就快跟他们拼命了,我说怎么能弄出这么难看的东西,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玮玮心有不甘。
拿出专辑才能和它告别
录完玮玮就发现,这张专辑其实还是按照乐手的方式录的。万晓利对他说:“你看你心思全花在二吉他、手风琴上,你必须把你的位置给调整过来,去想整体的东西。”我们现在听到的专辑,人声有一半是在万晓利家重新录的。
玮玮写道:坎坷的乐手转型之路上,我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如今我迫不及待地想拿出这张专辑,因为这样我才能和它告别。下一步,山长水远。
2004 到 2006 年,北京众多民谣乐队解散,野孩子、IZ 等位列其中。主唱单飞,乐手陷入尴尬。“后来又一阵为了生存都要变成录音乐手了。我还记得我录的最后一首流行歌是陈楚生的《山楂树》。”玮玮不无豁然,笑声在空气中温和散开。“如果朝着这方向发展,不出三四年,再回头看,你已经变成那种人了。”
2008 年,为了熬过痛苦的转型期,玮玮闭关修炼半年。“开始自立门户,心里有些关过不去。朋友里好多座大山,座座在前面屹立着,高山仰止。”“小河、晓利、老周……参加过他们那么多次录音,你知道标准在哪儿。”他跟自己较着劲,“老想去挑战,最起码得保证那个标准。一直都处在一个准备的状态,总是觉得自己准备不好。”
使这么大的劲儿肯定会出问题。“像《米店》、《花瓶》这时期的歌我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写了大家都喜欢;你真的那么卯着劲儿去弄这么一个,只能说尽力了,很认真。但是它失去了最根本的自然。”
他向万晓利倾诉自己的苦恼:“这种方式特别不舒服,感觉一直是顶着雷在做,而且别人还知道你在做,就像完成作业一样。”万晓利告诉他需要一个心理调整,把别的事儿都忘掉:“哪一个人出专辑不得这样?万青也会出第二张,出第二张的时候怎么抗过第一张这么厉害。”
对于玮玮,所有的过程现在是想明白了:“你要挖掘自己,这是永恒的。”“不可能闭关半年就把自己挖着了。首演的朗诵我觉得很好,观众也觉得很好,挺舒服,挺放松,一点不是胡闹。我就在想,搞文艺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什么是适合你的?然后我就知道,我们完全可以朝这个方向做点别的事情。
——无论什么方式,表现的比较傻,过程比较坎坷,或者这张专辑好不好……只要还在找自己,就是好事。我们又不是做了这张专辑就死了——又不是高晓松,如丧了——我们是如来。”
“下一张我是肯定不会打点儿分轨录了。我买了一个罗兰的录音机,下一张就去找不同的地方录。”玮玮打算找一个混响好的空房间,话筒一支,录一版《花瓶》;《石头房子》要去小索的墓地录;另有一些可以在深夜或是凌晨找一个地方录,去满足那个情境。
“不回避任何环境声,风声,说话声,自然的声音……任何一个声音都可能变成它里面的一个气氛。编排上也肯定是连起来的,故事感更强一些,最后做一个叙事的底子。捡起来一些自然的东西,抓气氛更重要。”录音方法、编排方式,这些都是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寻找它,其实也是自我挖掘的过程。
万物生长靠太阳,花开花又落
无论是“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还是“最光明的那个早上”,抑或是“就这么一个人,一夜又一夜走在路上”,玮玮的歌词总是设定好时间、地点、人物的坐标,把曲调叙成娓娓道来的日子。
“我爸说我,你这歌儿不对啊,音乐讲究起承转合,A 段转 B 段,B 段转 C 段,甚至可以加 D 段。但我的歌通常没有那种。” 就像当年白银饭店舞厅里一直在循环的音乐,慢慢的,玮玮就注意不到它了。
“我们把写好的旋律录下来,一遍遍地循环播放,然后就在那个永不疲倦的旋律里坐着,等这个词自己长出来。”这种方法是最适合写叙事型歌词的——《白银饭店》、《雾都孤儿》、《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都是如此。“但是现在还不是很能控制的住。歌词还并不是纯叙事,还是有抒情、铺垫、形容词这些东西。我希望我将来写出的歌词能做到所谓‘说而不做’——讲述,但不会明显的把自己的态度露出来。”
“你看西北的老民歌,开头第一段和最后一段都是完全一样的:‘鼓对鼓来锣对锣,牛郎织女下银河,万物生长靠太阳,花开花又落。’打开来,然后开始讲:你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最后我去了哪儿,绵延十几段。最后又‘鼓对鼓来锣对锣,牛朗织女下银河,万物生长靠太阳,花开花又落……’”
短短 26 个字写尽自然秩序与平衡之道,首尾呼应成一种大圆满,在玮玮的叙述中文字像是有了血液,在流动,有力量。
“这就是真正的中国民谣,词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这点跟大部分国家都不太一样。因为中国人不跳舞,音乐的功能性不在于发泄和释放,而是要推你的情绪,但是情绪光靠音乐推,肯定没有文字那么厉害。”
玮玮大概明白了自己希望通过民谣寻找的根:一直循环着的,慢慢的就注意不到了的旋律,承载着情绪,让心有所归属。
白银少有西北本地人,但是有全甘肃最大的监狱。监狱里的人来自西北各地。而监狱里的牢歌,都是西北传唱了很多年的老歌,在监狱寂寞的夜里,大家都要唱着那些歌才能睡着。仰赖于此,西北民谣才深深影响了玮玮和郭龙。它们有的比较现代,比如首演当天郭龙唱《晨风曲》那个路子,此外,著名的《李伯伯》、《两只山羊》也是监狱里面唱出来的。
“监狱里放出来的人跟我们说:‘玮玮,你跟郭龙要是进了监狱什么事都没有。’”玮玮说,会弹吉他的人在里面太受欢迎了,他们给大家提供了最需要的抒发的渠道。
“那阵子只要监狱里面有人放出来,我们就拎着酒找他去听歌。牢歌可比任何流行歌力度要强的多呀,全是大烟酒嗓子。”玮玮还透露了一个众人皆知的秘密,“只有刚放出来那半个月,你找他唱还行,过了半个月,他重新回到社会,再唱就不对味儿了。
他不停的唱,不停讲里面的故事,身边围满了人。”玮玮和郭龙所有讲故事的能力,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叙事的东西就是有意思,有些故事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那都是真真正正澎湃过的荷尔蒙。”
我们为你沿江而来
“最光明的那个早上,我们为你沿江而来,可是你的愁云消散,我们搁浅在白银饭店。”
歌词写于重庆,本来叫《巫山神女》。玮玮在一个小镇,买了一尊小神像,老板给他讲了一个巫山神女的故事:“一个原著民的神,特飞,勾搭过什么楚怀王之类的……”像写“沿江而来”之时,他特别清楚地看到雾蒙蒙的长江,一帮年轻人顺江而下,下游是一座座城市,武汉、上海……到了那里,人们迅速就把自己丢了,完全未知。
“沿江而来”四个字也出现在《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中。很多朋友已经认了它的原名《革命杀手》,改名的原因很简单:“‘革命杀手’四个字太愣了吧……而且专辑封底排版的时候,所有歌名排在一起,忽然觉得长出来一串挺好看。另外就是怕审查过不了。”
孟京辉导演特别喜欢这首歌,在 2010 年的话剧《三个橘子的爱情》中专门为了这首原本用不到的歌加了一场戏:“孟导说:‘硬加,不管!突然就变到民国。’”但把这首歌归于爱情名下,玮玮觉得有点委屈。
“其实我写的三流演员是我,革命杀手是我喜欢的那些人,张佺、晓利、小河……那阵子我在剧组天天呆着,演了 300 多场戏,生活其实挺颓的。每天复制复制复制,想起音乐圈的朋友觉得自己很不上进,像是背叛了组织的感觉。”
当时我在从台北到北京的路途中,一口气看完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1949》,情绪特别饱满。历史长河除了几个大人物留下姓名,得有多少无名小卒投身革命:有理想的、混日子的、求生存的、投机的、稀里糊涂被卷进去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吗?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最终都是在一个安排好的故事里面,你看不到主宰你的东西到底打算干什么。
”于是,他写下“谁在日夜交替的缝隙里打牌,我们随着他的运气落在地上。”宗教般的前奏响起,神圣之光便自周身注入毛孔,俯首倾听,在手风琴和鼓点中恍若穿梭至东欧,置身魔幻现实主义幻景之中。
饿着的时候人最接近真理
甘肃,兰州,清真寺。拱顶大殿顶尖月牙向天,两边两座塔护卫般耸立,它们被称作“唤醒塔”。在玮玮儿时的记忆里,兰州特别静,西关十字和黄河对面那两个清真寺唤醒塔的声音,全天都能听见,一天五遍,飘向整个兰州市每一个角落。玮玮称自己被那个声音被召唤过的,有过超体验:“我觉得特别舒服,特别好。有时候早上起来我就听一会儿,一听就觉得被一种更有力量的东西牵引着,人就醒了。”
玮玮最喜欢的音乐就是宗教音乐:“我手机上还下载了沙特阿拉伯出的,最经典的,《古兰经》的……APP。有中文版的,就是民国一个回族人翻译的最经典的古兰经。”
2003 在新疆伊犁,玮玮差点入教,一个哈萨克朋友帮他全部联系好,只要他下定决心。“我想了特别长的时间。那时候刚好赶上斋月,早上 4 点钟起床吃一顿饭,太阳升起来一直到落下之间,老教的人连唾液都不能往下咽。
跟着他们过了半个月,最后受不了了,我就去吃饭了。但其实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对身体对心理都特别好,每年一个月,给身体排一下毒。饿着的时候人是最接近真理的,最愿意去想真理是什么,饱着的时候全是扯淡。”
除了宗教音乐,玮玮还特别喜欢东欧和南美的音乐以及各种魔幻现实主义著作。“我是拉手风琴的,全世界最好听的手风琴肯定是东欧和南美的,别的地方没法比。只有搞过社会主义的国家有一股特别莫名其妙的飞劲儿,美好,残酷,所有的东西混搭在一起。”
“野孩子”对我们来说就是宗教
演出的最后,玮玮与郭龙照例唱了那首“野孩子”时期的《黄河谣》,不再拨弄任何乐器,只是端坐着清唱,“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像一场庄重的仪式。
玮玮说:“唱黄河谣根本想不了别的事情。”郭龙说:“不坐端正唱不了那个歌。”那是一首七拍子的歌,并不是正常的换气。它那么慢,还一直抓着你,就因为是七的循环,让你刚快到休息那个点儿,立刻就又转起来了。
“‘野孩子’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近年一直在弄这些事,心里一直有对佺哥的愧疚感,觉得又把组织的事情给耽搁了。我现在自己做的这些东西,跟野孩子完全不一样,如果完全静下心来弄自己这些,肯定自己的要更好一些。但是没的商量,那是一辈子的事儿。”
“每年中秋,我们演大河之上。张佺说:‘现在演不好,没关系,十年之后就演好了。’“野孩子”有那种东西——它不看眼前,几年以后再说,这是最有动力的东西。”
“‘野孩子’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宗教。它本身有一种宗教的东西,里面的核心是很神圣的,是你不能亵渎的。就是那种野孩子的态度和精神,做事纯粹,扎实,乐观,积极。关键是只有它,没有别的任何事情,不在乎有谁听,一心往标准上扎。”
此前,张佺、张玮玮、郭龙三人的组合已经被叫了两次“野孩子”,一次在 2011 杭州西湖音乐节,一次是今年的成都大爱音乐节。玮玮曾经说:“要达到当年‘野孩子’的状态才能叫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