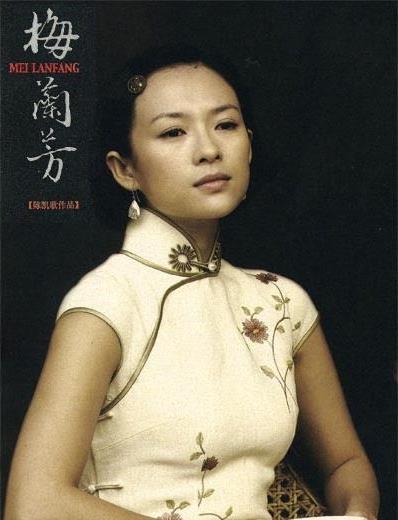停猎期间走进都兰猎场
“山上有岩羊。”沿着红水川开越野车进山,都兰国际猎场的导猎员勇军随手指向车窗外的群山。距离越野车几百米的陡峭岩石上,只能看到颜色枯黄的矮小灌木,根本看不到任何动物活动的迹象。等勇军停车熄火,支起一架小型狩猎望远镜,才看见山上果然有一群与枯草、山石颜色近似的岩羊,一共34只,由一只公羊率领,队伍末尾,还跟着两只不到一岁的小羊。
和那种随便扔几只野鸡供游人打猎取乐的所谓“猎场”不同,都兰国际猎场没有围栏,也没有大门,开车进了山,就都是猎场的范围。勇军笑着解释:“外面的人有误解,以为是巴隆国际狩猎场、沟里国际狩猎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这几个狩猎点开车容易去,不然翻到山背面去,动物还多着呢!” 不过,这里也不是城市人想象中的那种野生动物园:坐辆吉普车,动物们就在车窗外触手可及,靠几只猴子拉动花生销量。这儿能看到的野生动物,时常距车都有几百米,几千米,甚至一公里远,想看清楚需要借助望远镜。要找盘羊,还得骑马上山。
勇军从在山坡上扬起一把土:“风向不好,咱们得绕过去。”勇军远远地望见山那边有一群白唇鹿,想要靠近些观察,又怕白唇鹿闻见人的气味逃走。这一大群白唇鹿有100多只,其中有不少是顶着长角的公鹿。在都兰猎场,最了解野生动物情况的就是猎场的导猎员,他们虽然说不出什么理论来,但靠长期经验总能判断得很准确。要成为导猎员,最重要的是了解山里的情况,除了熟悉地形,还要知道动物们都在哪活动,习性如何。导猎员们通常早晨4点起床,4点半出发进山。青海日出得晚,经常进了山,天还黑着。如果时间推迟,风向就变了,动物所在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了。
都兰国际猎场是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每次巡山,猎场每人每天发50块钱补助,效益好时也有发100的时候。这样一算,每年光巡山,猎场的费用就不小。“上山要吃要喝,车要烧油,巡山一个月大概得花四五万吧。”?从创办开始累计创汇200多万美元,停猎两年后,欠了将近300多万的外债。猎场20多个职工一年多都没发过全额工资了。周围居民也都挺奇怪:“猎场以前挺红火,这两年不知道为啥就不行了。”
两年前的叫停,可以说是源于一场媒体风波。以往参与国际狩猎需要向国家林业部提起申请,但在我国《行政许可法》出台之后,再走审批的路子就行不通了,野生动物资源也必须拿出来公开拍卖。然而,拍卖涉及到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自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有钱就可以猎杀野生动物吗?”“为什么只让外国人打,不让中国人打?”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几乎一边倒地指向国际狩猎,淹没了猎场和野生动物学家们解释的声音。
除了极端不理性的人之外,公众质疑最多的可能就是:“怎么能打野生动物呢?那不是会越打越少吗?”说实话,勇军和其他导猎员也只能凭自己的经验:岩羊数量大,就在两群里打一头。猎人们打猎看中的都是有角的公羊。从角上也可以看出年纪,越大羊越老。“以前打猎时,60%的老外都是一次性打两种动物,只有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才打得起盘羊。狩猎有季节限制,效益好时一年也才只接待不到100人,估计一年最多也就打掉200只动物,根本不会影响种群。”
经济因素有时候也是调控的手段之一。猎场开出的价目表上,野牦牛价格最高,差不多有11万元人民币,岩羊至少也需要4万多人民币。而过去靠岩羊肉出口创汇的时代,一斤肉只能卖四毛钱。猎物的价格是国内四家旅行社根据国际上的价格协商出来的,岩羊、藏原羚数量多,可以适当降低价格,吸引猎人来打猎。盘羊数量少,价格就定得特别高,“盘羊都在山上,想打必须骑马翻山,加上价格特别高,真来我们这儿打盘羊的老外很少。”
作为野生动物研究者,美国蒙大拿大学的哈瑞斯教授给出的解释是,国际狩猎不会影响种群数量。因为几乎所有的国际狩猎物种都是一雄多雌制。即使进行狩猎,只要种群中有足够的成年雄性使雌性受孕,第二年春天幼体的出生数量就不会受到影响。即使误杀了一些雌性,也远远达不到威胁种群数量的地步。
不过,即使这样,猎场职工们还是很关心都兰地盘里有多少动物、又到底应该打多少。尤其是,根据华盛顿公约,一旦涉及附录中的动物出口,比如盘羊,都要经过国家濒危动物保护委员会的“无害化”科学判定。将来如果重新开猎,在出口时,必须能拿出可靠的数据。
猎场资料室里上一次的统计结果还停留在1996年。“要是能统计一下,对媒体和公众都好交待。去年哈瑞斯说要从蒙大拿大学申请一些经费,帮我们做盘羊的计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也没了消息。”
上山之后,牧场的围栏越来越少。有几座山坡上,藏原羚就在家羊附近吃草。“打猎对牧民放牧没啥影响”,农牧干部出身的新任场长航庆嘉开玩笑似的地说,“现在家羊和野生动物相处很和谐。”因为多生活在陡峭的山上,岩羊受到人类放牧的影响比较少,然而盘羊和家羊之间的冲突就比较大。根据哈瑞斯教授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现,盘羊在大的和小的空间范围内都要回避家养山羊群和牧羊人。在家养山羊放牧区域内,盘羊很少出现。在有家羊的地方,盘羊就只能转移到更高的坡上。为了在远离放牧者的营地的水源喝水,盘羊不得不走更远距离到河边饮水。野驴也和牧民的家羊抢草场,达盛林说:“我们每年都得派人手偷偷把野驴赶到对面玛多县境内去。不过我们刚轰过去,人家就又给轰回来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草地,各家牧民都修建起了草场围栏。这些围栏把草原成块成块地割裂开,又把草原密密麻麻围得水泄不通。野生羊没有草吃,只能向别的地区迁移,一道道围栏又阻挡了他们的迁移路线。大些的羊还好,小羊一般都跳不过。情况最严重的是鹅喉羚,全国总数大约只有3000只,却经常因为跳不草场的围栏,被挂死在上面。人和动物不仅争地,也争水。在水源紧张的地区,一些地方政府花钱给牧民的水井安上了可以上锁的井盖儿。这样虽然减少了争夺水源的纠纷,但野生动物们也喝不上水了。“有猎场的地方这些情况就要好一些。猎场职工们去和牧民说说,他们就同意在围栏上开一个口子,或者把井盖打开。沟里有人承包了1万多亩地,我们去跟他说,他就用拖拉机挖出了一个水塘给动物喝水。”
从县城进山去猎场要经过香日德。勇军和一路遇见的牧民打招呼,热情地用蒙语聊几句。有牧民说,最近一段时间放牧,又看见过三群白唇鹿,总共有300多只,其中有一只大公鹿可能生病了。因为猎场经常会雇牧民当向导,或者从牧民家里雇马上山,猎场和牧民们的关系很好。猎场没有地权、林权,国际狩猎收入的一部分要用来支付给牧民草场补偿。营地扎在了谁家的牧场里,也有额外的补偿。“那时老外的小费一次都会给个一二百美元。猎场红火的时候,有的牧民也不放牧了,在家养马,专门等猎场的人来雇工、雇马。这两年停猎之后,给牧民的草原补偿款几乎就没有了。”但在都兰待了这么多年,哈瑞斯教授还是担心国际狩猎的实际收入没法真正用在对野生动物和栖息地的保护上。按照规定,国际狩猎收入的8%交给省里作为野生动物保护费用,剩下的资金40%归省里,4%上缴给州政府。县里留下的56%中,25%要上缴地方财政,最后留在国际猎场的并不多。不过他也表示了自己的乐观——国际狩猎场至少早已杜绝了偷猎现象。
没有国际猎人光顾,猎场当年号称全县最好的餐厅被改造成了动物标本制作室。工作台上散落着胶水桶、尺子和木板,小屋里堆着已经处理过但还没来得及制作的动物皮毛。勇军和同事被猎场送到西宁去听外国专家教标本制作,地上就摆放着两只他们自己做好的岩羊标本。之前,秦皇岛野生动物园曾经向都兰提出过购买标本,不过给的价格比较低,手续审批也很麻烦,所以没卖出去。“我们也不敢卖高价,怕没人买。”听说北京也有专门做动物标本生意的,从国外进口皮毛,在国内制作、销售,不过销路都不太好。
今年8月,省里批下来了都兰国内狩猎场试点,很快新注册了一家国内狩猎公司,不过职工们还是愿意留在猎场,都不赞成把两家剥离。“将来国际狩猎如果恢复,两家会不会打架?万一试点失败了,我们还得有个活路嘛。”对于开放国内狩猎,场里领导们至今也没敢轻举妄动。“我们不敢宣传,一是怕又引起反对,二是宣传多了怕偷猎的人进来。以前还能打猎那会儿就经常有人问,你们都在哪打呀?可是老外就会先问,打猎有没有许可、要付多少费用。”另外一方面,航场长和职工们对国内狩猎者的素质都有点担心,“老外来打猎都不怕辛苦,虽然上高原、住帐篷,只要成功打到了猎物就很高兴。有的老外,打猎成功率高,第一天打到了猎物很后悔,觉得自己吃得苦还不够多。国内人的心态偏娱乐多一些,和老外不一样,比较难伺候。就算来打猎也是玩得多,要住宾馆,不少还提出要吃野味。”
从山上下来,航场长报告给职工们一个好消息:都兰国际猎场评上国家4A级景区了。“本来是要申请3A级的,后来人家说,你们索性跟着昆仑文化生态旅游区一起,就能评个4A级。”“这下可以搞旅游了!”旅游比起狩猎可能更大众化,门槛更低。猎场准备明年在旅游上大干一场,“在山里可以多建点能洗澡、吃饭的活动板房给游客们住。”现在已经有投资者想在都兰开家国际青年旅舍,选址在热水镇。那边有温泉,柏树林里生活着马鹿。
都兰的山区里正在修一条通往玛多的公路。可是猎场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大家都挺茫然。越野车开过旷野,头顶上一大片乌云追过来,顷刻间冰雹铺天盖地,一只藏原羚被冰雹打得四处乱跑,不知该奔向哪里躲避。开着车穿行在山间简易的公路上,勇军随手指点着山上的动物。也许要不了多久,进山的路上就会修起景区大门,或者停上载满游客的轿子车,长出一片片活动板房,甚至是星级宾馆、小别墅,而有着心型白屁股的藏原羚和白鼻子的白唇鹿,却再也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