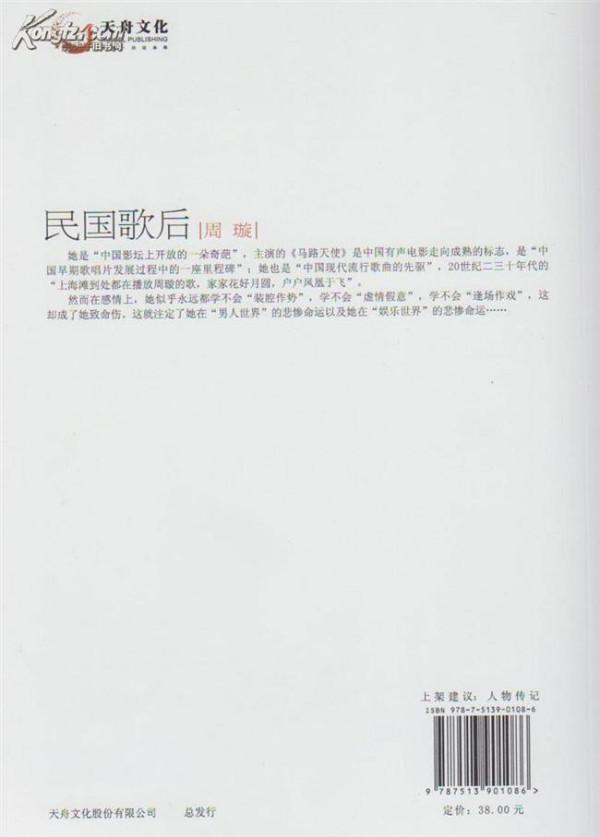周璇儿子周伟 周璇儿子周民周伟的照片 周璇儿子周民父亲是谁
所以蔡琴演绎的怀旧金曲才能在浦江的夜潮声中赢得强烈的共鸣。同时,人们不由得怀念起许多怀旧金曲的首唱者——金嗓子周璇。 当上海人沉醉于怀旧情绪之中时,从手摇唱机里传出来的老歌依然能勾起无限的遐想,
在刚刚落幕的上海图书交易会上,一本刚刚出版的《周璇日记》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这本书之所以让书商和读者不忍释手,是因为它最真实地记录了周璇在悲情时刻的缕缕思绪。
1951年春天,周璇在拍摄她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时,突然精神错乱,不久被送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这本日记就是她在疗养院以及回家后那些日子里记录下来的文字。从这部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患病后的周璇,可以看到一代影后、歌后生命渐渐殒落的余辉,以及在她身后的整整一个时代。
但是,无论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在上海当代文化史上,提及周璇,不能无视黄宗英的存在。后者不仅频繁出现在《周璇日记》里,更是周璇悲情故事的见证者,也是周璇的儿子周民的养母。读者一定记得,10年前,周璇的另一个儿子周伟,与黄宗英打了一场官司,最终以黄宗英败诉而告终。
其时,这个消息被媒体渲染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许多曲折至今也无人梳理得清。从此,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艺人似乎"退出江湖"。最近在某网站上,围绕周璇的身世与患病,又有人无端地掀起了一阵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波澜。
近来这几年,黄宗英先后两次脑血栓发作,今年3月底又做了一次腹部手术。得知《周璇日记》即将以出版物的形式公开后,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一场大病后的这位著名作家和表演艺术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甜姐儿捧金嗓子
笔者说:"您就从怎么会收养周民开始说起吧……"
"这大概是前世的缘分啊……"老人是这样开场说第一句话的。她是指的周民,她的意思是和周璇的儿子周民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前世的缘分。
接着,她便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大约是在1935年还是在1936年吧(笔者注:应是1937年),我记不准确了,赵丹和周璇一起拍《马路天使》,那时周璇还是一个小姑娘,她在片场拍戏,休息的时候还趴在地上和别的小朋友打弹子。赵丹和她,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小孩,没什么来往的。
"我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大概在1946年1947年间,在上海金都大戏院演话剧《甜姐儿》(笔者注:这部话剧几年里连演数百场,使"甜姐儿"黄宗英驰名上海滩)。一天演两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中间从5点到7点是周璇的独唱音乐会。这样就碰到、认识了。有时我会站在侧幕里听她唱歌,给她捧场,圈里说,算是‘角儿捧角儿’吧,但也没有什么深交。
"1949年解放后,她从香港回来时,赵丹和我与周璇也没什么往来。
"上海解放不久,周而复出面组织成立了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我担任了这个协会妇委会下的福利部部长。这个妇委会由袁雪芬、筱文艳、丁是娥等各个剧种的成员组成。福利部为了解决演员的后顾之忧办了一个托儿所。
"这个剧影托儿所先是在靠近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家协会)那里,先是接收3岁到7岁的小孩。后来应大家的要求又办了一个1岁到3岁的班。这个托儿所后来转到延安西路、定西路那里。这个剧影协会第二托儿所的所长叫朱茂琴。
"第一托儿所的所长叫薛素珍。我十六七岁在上海时就认识她了,薛家是大老板,相当有钱,家里有洋房、轿车、游艇,复兴西路上越剧院的房子过去好像就是薛家的。他们全家都倾向和支持共产党。
"剧影托儿所成立了一个理事会,我担任了理事长。袁雪芬也是理事,我们之间的感情蛮好,她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现在她就住在我家对面(上海淮海中路上的新康花园)。这就是50年代初的情况。"
周璇在枕流公寓突发精神病
"大约在1951年吧,有一天,有人匆匆赶来说:快、快,周璇在枕流公寓的家里,精神病发作了,在房间里烧东西,要把小孩从窗口摔出去。枕流公寓居委会的干部也来电说:赶快去人处理,否则要出人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便和黄晨(笔者注: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夫人,也是剧影协会妇委会成员)、吴茵等人赶到枕流公寓周璇的住处。
"到了那里,见周璇的房间里一片混乱,她在烧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我赶紧安抚精神紊乱、烦躁不安的周璇,黄晨便抱起周民,把他送到朱茂琴的剧影第二托儿所去。当时周民只有10个月大。按托儿所的规定,起码要1岁的小孩才接收,但周民是个特殊情况,只能特殊对待,我说先把他送去再说。他们说床位也没有。我说把这里的小床搬过去安置他。
"剧影协会的张立德、老凌也赶来了,还有在场的居委会干部,面对这个突发事件,大家觉得必须立即作出处理,我们商量下来,决定要把周璇送进精神病院。
"周璇的养母在一边说,她用盆子敲我,我吓煞了、吓煞了……我安慰她说,不要怕,我们会处理好的。我们当即叫来刘琼和韩非,让他们两人把周璇哄出去,说带她外出散心,其实是把她送往精神病医院。"
就这样,周民离开了他的亲生母亲周璇,剧影第二托儿所成了他的栖身之地。
"周民大约是1951年8月被送进剧影托儿所的,当时他大约10个月左右,所以我们填他的生日是1950年9月。
"小时候,周民长得虎头虎脑,很可爱,大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大头’,争着要抱他回家。那时候托儿所里有一个炊事员叫洪雪珍,她在民民的生活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托儿所里民民年纪最小,洪雪珍特别喜欢他,常常把民民抱在手里,给我印象很深。"
说到这里,黄宗英眼神里流露出慈祥的母爱,她说:
"那时候,小孩小,费用很大,我把工资几乎全花到托儿所里了。当时赵丹一个月的工资是360元,我是230元。第二年冬天,上海麻疹流行得很厉害,有的托儿所出现了一些事故;我们理事会开会商量这件事,我们已经把工资都贴进去了,但还是没有条件请专职医生24小时看护,小孩都还小,我们责任很大,就请来上海最有名气的儿科医生俞鼎新,抽空来托儿所检查一下。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理事会决定把剧影第二托儿所停办。理事会在开会时提出,其他小孩可以由家长领回去,周民怎么办?商量下来,大家都说,吴茵你年纪比较大,有点经验,你就把周民领回去吧。好的好的,吴茵说,我也喜欢这个小孩。于是,理事会共同把这件事决定要来了。"
赵丹的父亲说:"这是老天爷把他送来的……"
"上午决定了这件事,到下午,我下班回家吃晚饭时,忽然见门厅里怎么有一张小床,一看这是周民睡的小床嘛,是谁把他送来、扔在这儿的?说好送到吴茵那里去的,怎么送到我这儿来了?再看,民民这个小鬼头和赵青、赵矛(笔者注:系赵丹和第一任妻子叶露茜所生的儿女)爬在地上,三个人滚在一起白相(玩)得起劲。
"我就问了,周民怎么到我们家来了?家里人说,吴茵的婆婆不肯收下。那时,吴茵、黄晨他们和我们住在一幢楼里。
"这时,赵丹的父亲就说了:宗英啊,我们没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自己就来了,这是老天爷的意思,我们就收下来吧。
"我说,多一个孩子倒没有什么,可是我工作那么忙,没有时间来教育他。
"赵丹的父亲说,这你就不要管了,孩子就交给我吧。这个小孩大头大脑的,很活络,非常讨人喜欢。于是,就把他留下来了。(笔者注:2003年4月1日,赵矛和周民去南通祭扫赵丹墓地,又专程赶到如皋骑岸,找了很久,才在别人家的地里找到爷爷的坟,烧了纸钱。)这样,民民就成了我们家的孩子。
赵丹喜欢和小孩玩,赵青、赵矛那两个孩子大了,十几岁了,周民才一岁多。"
周民曾改名叫赵民
"1950年10月底,我到波兰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回来后在全国各地做了两百多场报告,宣传世界和平,历时3年。还要参加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这些日子里我特别忙,很少回家。
"回到家后就听到风言风语:黄宗英收留了周璇的私生子。
"民民已经3岁多了,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的家庭。因此,我们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想小孩长大了,被人私下议论,也对他不利。
"这时,我们正巧要搬家,搬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去,这是一个机会,干脆趁此机会把民民的姓改了。
"于是,我们就去找了地段户籍警。当时的那个户籍警和我们家关系蛮好的,我们对他说民民他妈的事情剧协在管着,我们有时去看一看,她的毛病是抑郁型的,我几次见她躺在床上连脚上的棉鞋也没脱,这个小囡就只有我们来管到底了。结果没费什么周折就把周民改成了赵民。
"那时,上海虹桥精神病院的院长叫粟宗华,在他主治下,周璇的毛病还是时好时坏。星期日,周璇也回家。我们去探望她,离开时她总是送我们到电梯外,她会伸起双手,向我们挥动,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嚷嚷道:‘宗英姐姐,再会再会噢!’其实她要比我大几岁。
"我在1953年12月27日生下了大女儿赵橘(笔者注:因赵丹演过《屈原》,《屈原》里有"橘颂",所以取名为:橘。)。第二年夏天,天气热嘛,我让橘橘和民民理了一样的男小囡头发,并排坐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两人像亲兄妹,一模一样。我常指着照片对别人说,喏,这是我的大儿子,这是我的小闺女。
到了1956年,周璇的毛病有所好转了,精神病院的粟宗华院长和剧影协会领导要求我们配合治疗,让我们带民民去探望他生身母亲,带周璇出来玩。
"当时是组织上派汽车,让刘琼和韩非去医院接周璇,由他们两人安排,带她出来喝咖啡、吃西餐,要让民民陪着去西餐馆。
"我想赶快要把民民的姓改过来,否则会影响周璇情绪的。我又去找了户籍警,把户口簿上的赵民又改成周民。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赵青、赵矛的娘是叶露茜。每到星期六,叶露茜就打电话过来,要赵青、赵矛到她那里玩。剧影协会领导也打电话过来,和我商量怎么安排周民去看望周璇。
"这时候,我的小孩也开始懂点事了,赵橘就在一边问我:‘姆妈姆妈,他们怎么有两个姆妈,我怎么只有一个姆妈?’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我和赵丹,我就把这个笑话讲给周总理听,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蛮有意思蛮有意思的’。
"1956年,周璇出来活动,新闻纪录片厂还给她拍了一段片子。记得是在我们家里拍的,周璇一边弹钢琴,一边还唱了歌,赵丹也在旁边。这段新闻纪录片公开放映过,当时影响蛮大的。这都是组织上为了配合她的治疗作的精心安排。观众看到了电影,也很高兴。"
周璇究竟是怎么死的
"转眼到了1957年。那年夏天,周璇突然生病了。她住在当时的虹桥精神病院。那年夏天上海流行急性脑炎,她感染上了,被紧急送到华山医院治疗。
"当时我正怀孕,产前我曾到医院探望过她。有一件事,我很受感动。那年夏天,上海的天气很热,当时又没有空调,我见到她的病房里摆满了很大的冰块。
"护理人员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市委市政府开会研究决定的。他们专门调用了工业用冰,放在周璇的病房里给她降温,这种规格和待遇,在那个年代属于破例的。可见政府对她的重视。
"周璇在华山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终于没能挽回生命。她是因传染上急性脑炎去世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疑问,那种无端的猜测是没有根据的。
"周璇逝世后的治丧活动,我因为生育很少参与。只是在追悼会上,电影局安排由我宣读了一篇悼词。那么多年过去,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表示要带好民民,把她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好孩子,让她在九泉之下安息。她的遗体火化后,香港报章上也刊载了种种猜疑。我看没有什么意思,也是没有必要的。
"而周民就到了赵家门里,跟定了,成了我和赵丹的儿子。
"我们又把周民安排到荣毅仁的妹妹荣素珍开的上海第一妇婴托儿所,这是当时上海最好的托儿所了。
"为了照顾好这个特殊的儿子,我特意把在剧影协会第二托儿所的炊事员洪雪珍接到我们家里来,专门照料周民。因为周民从小是洪雪珍带大的,和她熟悉,和她有感情。民民长大后,也没忘记这个体弱多病的老保姆,还常去探望她,塞钱给她。"
"说到这里,黄宗英似乎动了感情,忽然提高了音量感慨地用上海话说:
"民民叠格(这个)小人是有良心格(的)噢!"
关于周璇的遗产
笔者提到,周璇病故后,海外陆续有善款汇到国内来,据说折合人民币有40多万,后来被有关部门退了回去。笔者问:"这件事您知道吗?"
黄宗英答:"这件事我不清楚,50年代,我们不会对组织上提这种问题。"她又说:"大约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银行有人找我,对我说周璇在海外有一笔遗产,他说你抚养周民已经有将近10年了,你是他的养母、是他法定的监护人,只要你出面签个字,就可以把这笔款子转到国内来。
"我说,我们不要这笔钱。中国银行的人说,这不是你们要不要的问题,国家需要这一笔宝贵的外汇。这样,我就签了字。具体有多少数目,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记得,我们只取过1000元港币,后来这笔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什么都要凭票,我记得取了这一笔外汇后,还给了一大堆布票,我买了布,请裁缝到家给周民做了几套新衣服,橘橘(指赵橘)都是穿民民穿下来的棉袄,外面罩一件衣服。
"‘文革’抄家的时候,周璇还有像三五牌香烟那么大一个首饰盒被抄走了,后来归还抄家物资时,是民民去取的。东西没了,好像折了21元5角吧。还拿了两只女式手表回来,给孩子作个纪念。"
"我和赵丹从来没对民民谈过周璇"
"我们私下里还说起周璇,但我和赵丹从来没有正式或非正式地对民民讲过有关他妈妈周璇的事。从来没有,也没有对别人讲过此事。在你们这次采访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这件事。我们觉得不应该去揭别人的隐私,这不符合我和赵丹做人的准则。
"周民不喜欢电影和电影圈里的事,赵丹的事让他整理,他不写。周璇的事,我先让他写,他不写,他不愿听,他说听了这种事就烦。他好像还挑挑拣拣,不知他心里怎么想。他有怪脾气,家里好了,热闹了,他就走开;困难了,不太好了,他就回来了。
"有几次我从侧面看毛毛(笔者注:周民的女儿),像周璇,非常像,轮廓像,神态像。
"民民从小头就长得大,小时候外面买的现成衣服都套不进去,要请裁缝到家里专门为他做。赵丹和我,还有弟弟、妹妹都叫他大头。我们家里经常唱上海流行过的那一支童谣: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赵丹从小就特别喜欢民民,经常把他扛在肩上,带他去吃西餐,带他到文化俱乐部去玩。在家吃饭的时候,赵丹总要说:‘来,大头,坐到我旁边。’
"有一度政治空气紧张,赵丹很迷信,外面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要出席一个什么会议,总要在小纸片上写几个字,吉还是凶,好还是不好,去还是不去等等诸如此类的卜语。他每次占卜的时候,总是会把民民叫到身边:‘来,大头,你来给我抓阄。’仿佛只有大头抓的阄,才会给他带来好运似的。
"‘文革’中,赵丹被审查期间,总要在纸片上写几个字,也要民民抓阄。"
周民在红卫兵的皮带下扑在赵丹身上保护他
"‘文化大革命’了。大字报上写着:‘赵丹是反革命’,民民就在大字报旁边写:‘赵丹是革命的’。
当时大字报贴到了我家门口、走廊上、房间里。一天要来五六十批红卫兵,许多市民也围在我家门口看西洋镜,看了大字报,还要上楼来凑热闹。
"周民就去撕大字报,用毛笔去改大字报,用纸去覆盖大字报。他带着弟弟妹妹赵橘赵左赵劲,到处撕写赵丹和我的大字报。
"他是赵丹和我的铁杆‘保皇派’,他也是我哥哥、他的大舅黄宗江的铁杆‘保皇派’。我的孩子里,黄宗江最喜欢他了,我的嫂子阮若珊也喜欢他。
"他还要和别人和红卫兵辩论,人家说赵丹是反革命,他一定要说赵丹是革命的。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冲到我们家,抄家、抢东西,还用皮带抽打赵丹,他就冲上去和红卫兵撕打,被家里人拉开。红卫兵继续殴打赵丹,周民不顾一切地扑在赵丹身上,对红卫兵说:‘不准打我爸爸!’
"红卫兵转而打民民。事后,我就对他说:‘民民啊,我求求你,你走吧,你和赵丹、黄宗英没关系,你和我们脱离了关系,人家不会寻到你的,你走吧……你再这样下去,要被人家敲死的。’但他不肯,他不吭声。
"在那个非常时期,他变成了家里的老大,庇护着爸爸妈妈,庇护着弟弟妹妹。在那些日子里他常说一句话:‘做人要像一个人样子。’所以,后来赵丹就更加喜欢他了。
"赵丹‘解放’后,第一个就想到周民,想方设法把他从农村调到省城。那次他到江西的一个剧组去,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周民。他见到当时江西的第一书记江渭清,又和管文教的省委书记黄知真讲了,最后黄书记把周民安排到了省文联。
"后来赵丹去世,根据政策可以调一个孩子回来。当时我们有三个小孩子在农村,我们就先把周民调回上海,进了《萌芽》编辑部。
"不久,我又找了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要求落实政策,把那个人(指周伟——笔者注)从内蒙古调到北京中影公司。
"后来,那个人写了一篇文章《我亲爱的妈妈黄宗英》,寄给一家报刊,那家报刊的编辑把这篇文章拿来给我看,问可以不可以发表啊。我说,这么写啊,把我抬得那么高啊,我没有那么好,这不行,等我死了以后再说。太肉麻了,我就没同意发表。你们知道,我父亲是工程师,我们是知识分子啊。对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太在乎。
"那时候,只有我的女儿赵橘还在外地,她是先去插队,后参加高考,进了当地的师范学院。当时,一个朋友从美国写信来要帮助我女儿出国,我想先把她办出去也好,将来回来也可以不受户籍的限制,也可以回上海。
"‘文革’结束后,赵丹补发工资,大概是2万元。赵丹讲这是血汗铜钿啊!上影厂来电话要家里去取钱。他就让民民去拿。取了钱,民民直接存到静安寺那家银行,当时给每个孩子和亲戚账户上都存了一千元。
"后来,搬到新康花园,也是民民到电影局去跑,才解决的。
"1980年,赵丹追悼会上,捧骨灰盒的也是民民。
"所谓遗产官司,那些钱,最后也是民民出面到外省去办来的。我不要,一分也不要。我给民民的要比那个人多得多。
"人是要凭良心的。"黄宗英一字一顿地说。
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笔者问:"那么周民的生父究竟是谁呢?"
黄宗英答:"最后都不能肯定。朱怀德不承认,解放后他害怕人民政府,我们让他一个月送48元来付周民的托儿所费,他乖乖地送来,就是不承认。
我们都有这个怀疑:就是生父另有其人,谁呢?那是周璇在香港的事(笔者注:指怀孕),难说,周璇不说,谁也说不清。都没有根据。有一位社会名流说像某个人,但也没有医学根据。当然,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世了,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笔者又问到了唐棣。
黄宗英答:"不太了解这个人,50年代,领着个孩子跑东跑西,到处要钱,要知道周璇是个精神病人啊,怎么受得了!他到我们家,我们还给了他100元钱,‘文革’中又到湖南路来,我们那时也没有钱,都领生活费,就没给。
"反正我和吴茵、黄晨几个到周璇家去时,见到周璇大橱里有许多东西,裘皮大衣什么的。后来她疯了,送精神病院后,再去时就什么也没有了。许多人都说是他串通女佣人,做了手脚。"
黄宗英最后说:"这都是历史了,都是过去多少年的事了,就让它过去吧……"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弱,就仿佛是那个年代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