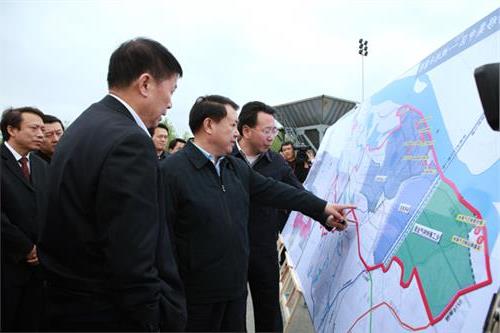陈敬容的爱情 陈敬容:老去的是时间
1989年11月15日,著名诗人陈敬容治丧办公室寄给我一份讣告。讣告上写着:陈敬容于1989年11月8日22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根据本人遗愿:治丧工作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兹定于1989年11月17日火化。 她的遗愿像她的一生一样,平凡而简朴。陈敬容活着的时候,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独自一人,在都市的一角,过着平静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死后也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一个人带着她的诗和情,静悄悄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接到讣告后,我久久不能平静。陈敬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她一生的不幸和坎坷久久地存留在我的脑海中。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和她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那时,我的孩子很小,又要去十几公里以外的郊区上班,她常常过来关照我。
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每到甜枣收获的季节,她总是捧着一个小碗,给我送来一碗又甜又脆的大红枣,我觉得她很热情,像母亲般地关怀我。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彼此也还算信任,空闲时常坐在一起聊聊。
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但从不谈她的过去,更不谈她创作上的成就。时间久了,我从周围人的口中对她过去的生活知道星星点点。 十年浩劫,我和她完全失去了联系,各自都离开了这个四合院。
1978年,为了编写《中国文学家辞典》和《中国现代女作家》,我又想到了她,几经打听,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一天,寒冷异常,北风呼啸,我和一位朋友来到位于北京正南方向的一座寺庙――法源寺。那时的法源寺还没有修聋,一幅破落、凋零的惨景,院子里来往的人很少,走进里院,使人觉得有些悚然。
有人告诉我陈敬容就住在这座破庙的一间房子里,按照看庙人的指引,我找到了那间房子,庙的后院有三间瓦房,分住两家人,中间的堂屋,两家公用,放些碗橱等零七八碎的东西。
两家人的门口都是锁头将军把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有格子的木窗棂,屋子里很黑,我只好趴在窗玻璃上观察,判断陈敬容住在哪间房子里。很凑巧,诗,帮了我的忙。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不太整齐的杂志,正中间,有一堆摆放不很端正的稿纸,我一眼认出,那上面的字是陈敬容的笔迹,那是她的诗的手稿,我在门上给她留下了一张纸条。
回来的路上,我高兴极了――找到了诗,就找到了陈敬容,找到了陈敬容也就找到了诗。
过了两三天,我接到了她的来信,她约我尽快到她的房子里谈一谈,我又一次到了法源寺。走进她那又冷又黑的房子。火炉燃得不旺,仿佛进了冰窖一般。当她伸出手来跟我握手时,我发现她的手粗糙得如同常年在农村劳动的老农的手,并且所有的骨节都突出增大。
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下水道,每天要提几大桶水。那时,她和女儿住在一起,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都由她一个人承担。机关比较早就让她办了退休手续,她只好靠着为数不多的退休金打发日子。
后来她又搬家了,搬到了宣武门西大街一所高层住宅,我去看她的次数多起来了。新宅说是三居室,实际上每间都不大,而且一个朝东,其余两个全朝北。三个屋子都临街,整天车流、人流昼夜不停。
陈敬容只好闹中取静。她一生中最后一段时光,是她最满意,也最快乐的日子,她可以关起门来写诗,写散文。她告诉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么无忧无虑过。她是那么爱诗,诗情注入在她的生命里,她活着,诗就在她的心中孕育。
最后的十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也是她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成熟期。经过令人发指的十年浩劫,陈敬容诗中的天真与浪漫少了许多,但真诚依旧,增加了更多的成熟以及对人生的体验,这些深邃的思想,蕴藏在独特的意象中,更加婉转,更加富于哲理。
在她晚年的诗中,形式上中西结合得也更加浑然一体。 “偷读” 陈敬容,笔名蓝冰、成辉、文谷。1917年9月2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城。乐山旧制为嘉定府,古称嘉帅。
它是距峨眉山百里左右的一个半岛形地带,三面为长江支流所环绕,只有一面陆路,经几个县通往成都。那里气候宜人,风物多丽。古往今来,哺育了不少有成就的文人。盛唐诗人岑参,现代作家郭沫若都出生在那里;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在那里的凌云山上读书,凌云山有东坡洗砚池,历来被视为名胜之地。
她家里虽不富裕,却足可温饱。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教小学,居然学会了新式的算术。陈敬容四岁启蒙,全靠祖父。童年时,祖父常教她读书,但只限于“正经书”。
起初读《三字经》、《孝经》,后来读《史鉴节要》、《论语》、唐诗等。小说则无论新旧,一律不许看。祖母因为自己不识字,最反对读书,她总是愤愤地说:“读了书做女王吗?我不读书,也活了一辈子。
”祖父很希望父亲能光耀门庭,父亲终于在四川军阀手下当了一名不大的官儿,东奔西跑,常年不在家。母亲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念过私塾,结婚后,千方百计要去县城女子师范读书,由于祖母的竭力反对,终于没上成,一直引以为憾,因此,对女儿读书,十分支持。
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上有一位拖着粗大辫子年长的同学,常常给大家讲一些旧小说里面的故事,如《七侠五义》、《再生缘》等。同学中有这类书,互相传看,他们被带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她从这些书里读到了在教科书里读不到的东西,感觉特别新鲜。少年时代的陈敬容,在抑郁、沉闷的环境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橱里、架上、桌子上堆满了虫蚀的线装书。
书房的窗子很大,但被窗外一道整年长满青苔的墙挡住了,光线不好。有时她看见祖父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前看书。她很羡慕祖父有那么一个大书房,心里想:“一个人能读那么多书,真了不起!”她多么希望也像祖父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探取书中的奥秘,但森严的家规却把她拒之门外,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准进书房的。
她十二岁那年一个冬日的黄昏,一家人都在房间里烤烘笼,陈敬容瞅准时机,悄悄地推开书房的门,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聊斋志异》,拿回自己的房间,塞到床褥下。
待到深夜才坐在油灯下阅读。她在1946年写的散文《偷读》中回忆道:“怎样的惊奇、狂喜,又怎样的骇怕!那些鬼怪、狐狸的故事,真叫人毛骨惊然!好像他们都在窗隙里、门缝里向我窥看,好像他们已经进到屋内,躲在那些拥挤的家具背后。
但是这种恐惧却不能夺去我阅读的兴趣,我便把两手捧住了脸,只留两只眼睛,朝向书本上,偶然也举眼望一望四周,但马上又骇怕地收回来。” 从此,她读书的兴致愈来愈大,想方设法躲开祖父的目光,在书房里大加搜索,慢慢地发现了《三国志》、《列国志》和名目繁多的小说,又从叔父商店的学徒手中借来了《封神榜》和《西游记》等,贪婪地阅读。
开始偷读时,心还怦怦地跳个不停,当专心地读一阵子以后,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
后来她考上了县立女中,逐渐接触到五四初期的作家鲁迅、朱自清、郭沫若、叶绍钧、冰心等人的作品。另外,教师也选了一些活页文选给学生阅读。她又接触到外国作家都德、左拉、拜伦、柯罗连珂等人的作品。有时,省下零用钱,还到旧书铺去租书来读。在学校里忙于应付功课,读课外书的时间较少,只好偷偷地带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