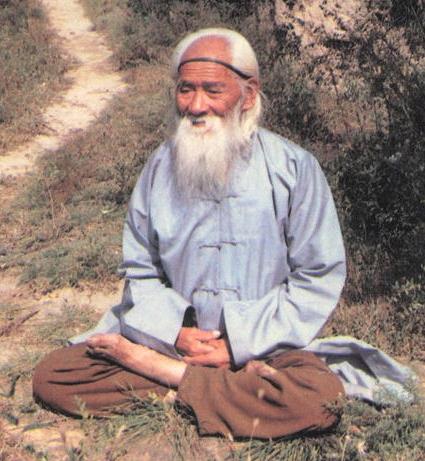明韵田家青 田家青谈明式家具(二)一件家具一个古人
古时工匠说起木头就像说起人,比如说起不好加工的紫檀,他们就说:“‘脾气’大很难‘伺候’。”这里是把物和人平等看待,不像西方总是在征服。在明代木匠眼中,木头和人一样,都有灵魂,木头其实是活的,随时依环境发生变化,温度、湿度的变化,木头也会变形和热胀冷缩,再直的一根木头,从中间劈成两根,每一根一定会慢慢弯曲,这些都是木头的“性格”。
聪明的木匠悟到了木头的特性,顺势而为,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西方人几百年都无法解决的最挠头的问题,其中关键就是思维的差异。有人说,“征服”是西方人对待自然的理念,西方人对“不听话”的木头的“征服”,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用铁条和钉子箍起来,做成框架,将木板箍住,令其涨无可涨、缩无可缩,但木头是坚忍不拔的,宁开不屈,绝不妥协,很多干脆从中间撕裂或是劈了。
第二阶段,他们将木头切成薄片,一横一竖地用胶粘在一起,三合板由此诞生,让木头自己较劲,似乎解决了木头“反抗”的问题,但木片一年365天时时刻刻都在收缩膨胀、在反抗,过了几十年必使胶失效,这些薄板都一片片撕开了。
到了现代,人们干脆将木头碾碎成粉末,然后加入树脂,压成胶合板,这似乎就彻底解决了木头“反抗”的问题,但实际是一种无奈和彻底的失败。古代中国人不想征服木头,而是要与木头共存,他们只用很简单的方法,在每道工序上有相应的办法,用“抽缝”等技巧,给木头膨胀和冷缩的空间,很简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反而可以让木头听话。
中国家具榫卯更是一绝,很多明式家具不用钉不靠胶,只用榫和卯斗合在一起,历经几百年沧桑,木料已近朽烂,但主体结构仍然不松不散,仰仗的就是严谨的榫卯结构,反映的是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出于对自然和万物的敬畏、那时的工匠对木材都要材尽其用。量材而用。古人做家具不依赖图纸,这是最人性化的方法。工匠要依现有的木料建议主人做什么,先做大型家具,剩下一些材料,就做中号、小号的,再剩下的小型的文玩用器,直到除一堆锯末,只做够牙签,什么都不剩下,一点儿都不糟蹋。
“如果这么多年来,人们能依照明式家具的理念生活和生产,当今恐怕就用不着为气候变暖着急了。”田先生说。
其实最让田家青着迷的是明式家具的“语言”。田家青看一件家具,看它的造型、用料、结构和工艺,就能看出家具背后设计和制作者的艺术修养、品位爱好、性情格调、为人处事⋯⋯这就是所谓的“见物见人”。工艺上,田家青看就是“眼”和“手”。
“眼”就是眼力,属于艺术范畴;“手”就是手艺,属于工艺范畴。“眼高手低”,做出的家具造型漂亮,有艺术性,但手跟不上劲儿,做工粗糙;“眼低手高”是“匠活”,最糟糕;“眼高手高”者固然让人钦佩,但也还有人品高下之分,有“偷手”的:把表面工夫做到完美,暗底下的榫卯却做得很马虎,这是较油滑的工匠;如果是“眼高手高”,家具的暗处都使得上劲儿,一丝不苟,是实在的人;若还有创新,这件作品在历史上就会有相应地位,成为经典,我们虽然无法知道他的名字,但见到这样的器物,人们会肃然起敬。
田家青见过一件明代书柜,他相信这件柜子是当年一个文人做的,因为从选料、用料、结构、制作方方面面都能看出稚嫩但认真之处。
例如柜子的四个侧面都做成“扇活”,一个柜子等于做了两个柜子的工,结果费了工夫,反而不结实,从工艺手法上看,他没有木匠的基本功,是个特别认真的票友。最有意思的是家具里标识榫卯关系的“暗记”(通常工匠用简单的小道道,称为“苏州码”),居然是用一手极漂亮的楷书写的千字文。
一般一件家具工匠只要打两三个暗记就够了,他却不厌其繁每个相交地方都写了。从这些特征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追求完美,书生气十足又迷恋家具的明朝文人。
田先生说,明式家具是在文人参与下才达到艺术的高峰。田家青要求工作室的同仁一定要习练书法。“不习书法,你对明式家具就很难有感觉。”田先生说。例如,明式家具中经常会出现的“罗锅撑”,如果你没有感觉,就会把它做成“拧着脖子”的样子,难看极了,这种东西教是教不出来的,是工匠艺术素质的直接表现,需要自己感悟,如果你学过了书法,自然就能领会那种感觉,想“拧脖子”都难。 田家青早年藏有一个清代的明式紫檀香几。几面丢失了,但仍有独特的残缺美,属于维纳斯式的遗憾。15年前,田家青将其收录放在专著里,结果有不少人仿造,以谋得高价,有上当的人,居然还设法寄来照片找他来询问。实际这件香几一直在他书房中,根本没出过门。伪品僵直、呆滞,一点精神气儿都没有,与真品相距十万八千里。有书中照片可以参照对比,这位“爷”却楞看不出来,可见其眼神!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现今人们对家具审美的水准:“多差的仿古家具都能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