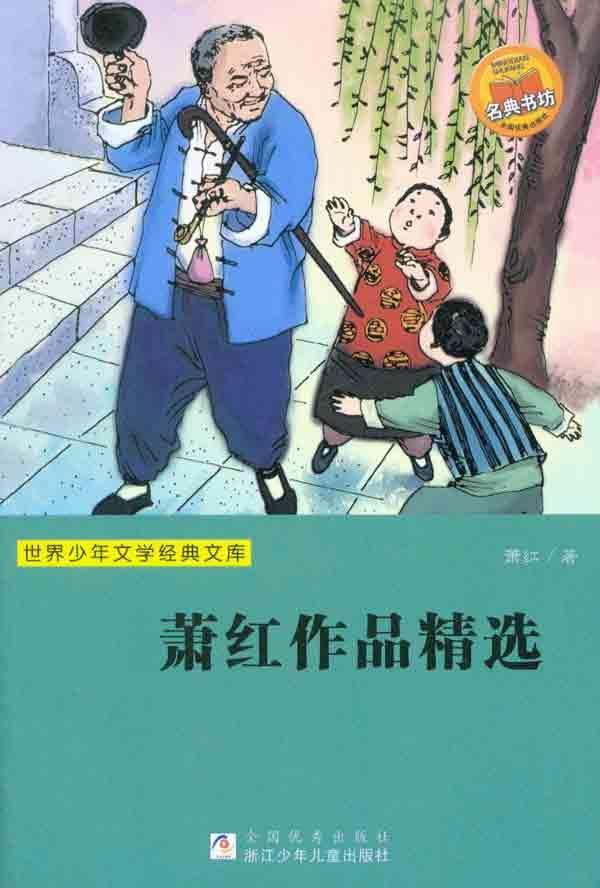萧月华的孩子 萧习华散文:月光下的晚餐
那是个夏天,我们生产队的大木船实在是破损得不行了,在走船中,水就从船板的缝隙处从外拼命地往里挤,隔一阵子船上的人就必须把水舀出来。于是,队上决定对大船彻底进行修补一次。尽管当时停下来是个损失,这条船是队上的集体经济,它像一个大男人一样为队上挣着现金,但破船难以行走江河,更经不住狂风恶浪、险滩激流的摧折。
在某一天,船就被拉了回来,停在大坝外的河边。又一天,队上的男女老幼齐上阵,把大木船从水里拖上岸来。大船就像一条巨大的死鱼躺在河岸上了。
我们这群小孩子可就特别高兴了。去上学的途中,有事无事都要绕道去到那里。或在船舱里追逐打闹一番,或在船舷边站成一排向天比射高尿,或在船篷里的吊床上躺一会儿,或在船的水边用薄片片卵石扔水漂儿,或在那儿的草坪上做打石碑的游戏。
玩得忘乎所以,一些孩子就忘了大人交办的事情,那阵子我们就多了一些挨打的机会。而河坝里遍地长着的黄荆柴,其枝条,就成了打我们屁股的“凶器”。但是仍然阻止不了孩子们贪玩好耍的劲头。
船就搁浅在岸上了。大人们的心里就装着一件大事。这时,要计划外出去山里购树木了。修船的树,是一些不怕水沤的树种,比如长在山中的青冈等。大人们知道,得抓紧时间把大船修补好,为集体多挣钱。树陆续买了回来,就得请水木匠来做船了。于是,大河边就异常热闹了起来。
我们这些学生娃就有事情可做了。上学或放学时都要跑到那里去为大人帮上一手。比如帮大人递递工具、搬搬木板。我们也盼着大船早点修好,盼着大人们脸上绽开笑容。
急是急不起来的。大船最快也要在秋天里才能修好。大船修好后在下水前,全队人要隆重庆贺,庆贺的方式就是全队社员大会餐。那时田里的稻子也收割了,才可保证大会餐时人人有一碗喷香香的白米饭。这些在我们梦里飞翔过多少次了。
我们生产队在当地的名声很大。一个大河坝,几百亩平整的土地,像个小平原。大跃进时曾放过“卫星”,上边领导一高兴就为社员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奖了打米机、磨面机和抽水机,全队的农户点上了电灯。老百姓用不着跑老远的路去打米磨面了。另外因为有了抽水机,就自然扩大了生产队种植水稻的面积,人均可以分配百十来斤稻谷,吃米的机会就比周围数十里的村民要多些。
在修船那段时间,我们这些孩子都对读书的事不上心,成绩纷纷往下溜。大船像牵了我们的魂儿。总认为大人们的动作太慢了,是有意与我们小孩子过不去。于是在船边玩耍的时候就不耐烦了,不如以前听话了,极力摹仿和嘲笑大人们做工的动作,当然也做一些捣蛋的事情,常常受到他们的训斥。他们看见我们放学了,就忙停下手中的活计,把一些锋利的工具,如凿子、斧子、钻子收起来锁进木箱子,怕伤了我们。
在我的印象中,大人们是一边在改着木板,一边在拆卸着大船。不久大船的影子就没了,变成了一地的旧木板了。新改的木板也铺了一地。大人们把好的旧木板放在一边,把不准备再使用的坏木板码在另一边。这阵子,我们又增加了另外一些玩耍的项目,就是把旧木板拖下河,赤条条在河中嬉戏。不管会不会游泳,只要抱一块旧木板在水里就不会当“秤砣”。这些日子不断有小孩子被锈铁钉挂伤的事情发生。
大船继续在河边慢慢地修;而老百姓的日子也在慢慢地熬。
农时季节,金黄的玉米已收回队上保管室,一部分已分配给了社员们。那一年,附近有的地方遭了旱灾,土地裂起几寸宽的口子。好在队上有抽水机,只要河里有水,庄稼都不会渴死,可能会减产,但不会造成绝收。
由于旱灾断了一些老百姓的口粮,我们时常看见邻县一些人来到我们河坝里讨口。那些讨口的,与我们现在看见的讨口子不一样。从外貌来看,他们都穿得整洁,不像现在一些讨口子那般脏兮兮的,没个人样。背一个背篼,背篼的形状像一个朝天的大喇叭。
只要见着背喇叭背篼的,我们就知道讨口子来了。村民往往是把上顿未吃完准备留着下顿吃的剩饭端出来给他们吃,瞬间见他们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他们不进屋,站在门口,吃完你端给他的剩饭,然后接受你用碗装的一碗或半碗玉米,千恩万谢地走了。这些讨口的,平均每家一天要遇到好几起。
社员们一不小心就成了施舍者,自然就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他们的幸福生活,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只是用不着也像别人一样背个喇叭背篼去乞讨而已。他们也有一天只吃一两顿饭,饿着肚子熬日月的时候。
大木船就在人们的盼望中慢慢开始变成船的样子了。大概是水稻收割以后,大船就修好了。大船被木杠支撑着不与地面接触,大人们给大船要上好几遍桐油才行。船就黄铜一般,亮堂堂的,风景在大河坝里。此时,河风吹来,油香就满河坝飘荡。
不几日,大人们就开始操办庆贺之事了。庆贺之后,船就该下水了,要趁这秋汛时节,好水好风好行船。
从夏天挨到秋天,那一天说到就到了。首先是大人们绝早起来,把队上集体喂的肥猪牵两头去公社交。按当时的规定,杀一头肥猪返回半边肉,两头肥猪可交一头毛猪给国家,另杀一头把肉挑回来。
从上午大人们就忙乎着了。全队三百多口人吃一头肥猪,应该是很丰盛和奢侈了。那时的肥猪不如现在的肥猪大,一般毛重有两百来斤就算是挺大的了。全队人平有好几两肉,在那时应该是很满足的事了。
聚餐安排在晚上。我们下午很早就放学了,跑到船边等待那幸福时刻的来临。我们去的时候,突然发现河坝里的狗多了起来,好些狗不是本队的,而且都是瘦狗。我们这群小孩子为熬过这难挨的等待,瘦狗们给我们提供了攻击的目标。
我们就用鹅卵石把这些瘦狗追打到老远老远……不一会儿,狗们又聚了过来,我们又追打开去。我们的欢笑声与狗的叫声“幸福”地交织在一起。三番五次,如此这般,天就黑了下来。蜻蜓在未黑净的天空里飞翔。月亮从云层钻出来,先是模糊后是清晰,愈来愈明亮起来。
河坝里临时拉起的电灯亮了起来,村民一家子一家子陆续到来了,自带着碗筷,提着马灯或打着手电筒,河坝上流动的灯火映在水中……我们这些娃子分别被大人们领去。聚餐规定,当晚不论大小老少,人人有份,只要有一张嘴巴就得算一个人,那怕你是婴儿。每人两碗白米饭,菜可分而食之,每桌一小碗烂红苕烤的酒。
会餐开始了,每十人一桌,基本上都是亲情组合。于是,在草坪上就围成若干个小圆圈。人坐在地上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蚂蚱在我们身边蹦跳,蝙蝠在夜空里上下翻飞,水鸟也在远处惊叫,周围的野蒿散发着青香,河水的响声哗哗传来……
星星般的灯火散落在大河坝里,幸福的话语在大河坝里迷漫……
每个人手里端着饭碗,每个人面前还放着一个空碗,不管哪样菜,请吃的时候大家都一齐动手,不多动一下筷子,吃不了的就放在自己面前的空碗里,会餐结束自己带走。那一小碗烂红苕烤的酒,被大人们依次一小口一小口抿着。
我在大人们多次鼓动和引诱下,终于端起碗喝了一大口。我才十一二岁,是第一次喝酒。酒从喉咙灌下去,就如一根火棍从喉头捅进了肠胃,体内升腾起烈焰,并隐隐作痛。喝酒对一个少年来讲,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成长的疼痛。可爱的白米饭,可爱的大肥肉,一路凯歌地滑进我们饥饿的体内,滋润肺腑,愉悦身心。在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身边也不时传来狗们争抢骨头的叫声。
晚餐并非最后的晚餐,它所带来的幸福感觉正在向黑夜深处进发,向明天憧憬,为我们的大船祝福,愿它踏着江河的波涛向着太阳出发、归航。晚餐也使聚众的人群感受当下生活,预测着未来的日子。
晚餐结束,人们各自带着未享用完的胜利果实,带着美好的满足,扶老携幼回家。原来草坪里不动的灯火开始动了起来,发散开去,开成满河坝的星光,开成满河坝的希望。明天队里的大船就要下水了,就要走江行河了,这希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醉酒后朦胧中的我,在皓皓月光下,在明晃晃的电灯光下,在灯火散去的河坝里,我看满河坝的鹅卵石,像堆了一地的馒头……光形成的雾气,也像蒸馒头的蒸气。这是真实的幻境,是一种幸福的幻境。心想这一地馒头够我们未来的日子享用的,以至于对渡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充满信心。
此事已过去多年。但那种幸福的感觉把我从少年滋养到青年。之后,在我尝过的美味佳肴中再也没有超过那顿晚餐所带来的幸福回忆。人是不能忘本的。在任何时候也不可放弃希望和追求。
呵,那月光下的晚餐!
2001年5月25日
作者简介:萧习华,本名萧绪华,男,汉族,1964年生,四川三台县人。成都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科、四川师范大学法学本科毕业。高级政工师。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四川省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现任四川华蓥山龙滩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1985年开始在《中国煤炭报》、《四川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煤矿文艺》、《阳光》、《三峡文学》、《写作》、《星星》、《散文诗世界》、《散文百家》、《北京文学》等全国报刊发表作品。
已出版《鸽子与鹰》、《生命河》、《另一个太阳》、《又是明月光》四部著作。曾获第四、五届全国文学乌金奖、中国煤矿文联阳光文学奖。














![萧月华之子 [连载9]中华之魂星辰谱(萧月华)](https://pic.bilezu.com/upload/3/26/3263f987e23b88b0f67c948ec83d8880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