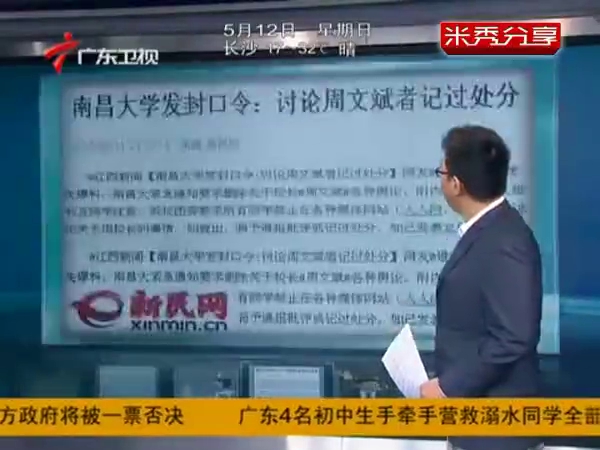周志文是sb 周志文:“边缘中的边缘” 是我真正的伤痛
周志文,原籍浙江,1942年出生于湖南。1949年随二姐夫军队撤退至台湾,此后在台受教、成长。毕业于台湾私立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获硕士及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专长明清文学及思想史,有论文四十余篇及《晚明学术及知识分子论丛》等专著。
亦擅文学创作,有短篇小说集《日升之城》,评论集《在我们的时代》、《瞬间》,散文集《三个贝多芬》、《冷热》、《布拉格黄金》、《寻找光源》、《风从树林走过》、《时光倒影》、《同学少年》和《记忆之塔》等。
1989年5月初,即将度过47岁生日的台湾私立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志文来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参加中国社科院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他还兼任余纪忠先生“中时报团”旗下《中时晚报》的主笔,所以一大早就搬出一把凳子到院中(寺院客房的电灯并不太亮),借着晨曦的光亮写社论,以便能及时传真回台湾。同行的龚鹏程教授笑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台湾报纸的社论在北京发稿”。
1965年自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周志文旋即入伍服役,次年退伍并开始在桃园的天主教振声中学“教了8年中学”。早在1971年,周志文就开始受朋友之托为《台湾时报》撰写评论,并在《台湾日报》、《中华日报》担任专栏作家,先后担任《中国时报》、《中时晚报》和《民生报》兼任主笔,见证了台湾报业兴衰的过程。
1974年至1981年,周志文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和中文研究所相继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彼时的台大中文系名师云集:毛子水、台静农、郑骞、屈万里、张敬、王叔岷……对于这些大师中的大多数人,当时台大中文系的规矩是,“称呼老师得用他的字号,尽量不直呼其名”。周志文读博士时,不但不缴学杂费,还享受各种奖学金和助学金,“那真是台湾教育的黄金时代”。
1981年,周志文以《屠隆文学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从台大中文研究所毕业,其后在淡江大学中文系执教10年,后返回母校台大执教15年,于2007年退休。此间,他也曾于1997—1998年担任捷克查理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于2003年任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人。从台大中文系退休后,周志文又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及珠海联合国际学院讲座教授。
在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和现代文学等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外,周志文的散文创作最受好评。其中,《时光倒影》(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和《同学少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8月)均有了中国大陆简体字版。
对于由专栏结集而成的《同学少年》,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的总编辑告诉著名作家朱天文说,周志文的文章是十年来所见散文最好的(不是“最好的之一”,是最好的)。而《第一次寒流》,编入了周志文主编的“台湾学人散文丛书”在内地出版,这套10卷本的丛书从前年8月到去年7月,终于出齐,逐渐呈现出台湾学人散文群体的全貌。
《同学少年》中部分篇章对眷村的书写,应该是最高水准的,可惜它在中国大陆的“眷村热”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近期,周志文的新作《记忆之塔》静悄悄地在台湾出版,诚如台湾权威的批评家、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所言,《记忆之塔》“是那个《同学少年》里衣衫褴褛的孩童上了大学后遇见的惊奇世界,涵盖了六零至九零年代,台湾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三十年间,一个文化人的养成过程与亲眼目睹的斯文扫地场景”。
1949年从中国大陆随二姐夫的军队撤退至台湾后,周志文和母亲及三姐、妹妹这些旁系亲属只能作为“黑户”,住进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罗东镇的眷村。也许是这种“边缘中的边缘”的生命体验,也许是幼年习得的天文知识和后来的文学、艺术知识,也许是专业领域涉及相对冷僻的古典文学,它们的合力过早地形塑了周志文淡泊名利的性格。
周志文没有记日记和自编创作年表的习惯,所以笔者只能根据他多部作品的蛛丝马迹归纳出他这些年来的行止。也许,这只是中国大陆读者全面认识学者和散文家周志文的一个开始。
关于人生
你提问中捻出“边缘中的边缘”,这是我真正伤痛的地方。这句话对我的杀伤力,不只是在我眷村的身份上,而是在我的整体生命上,在整个文化与地域认同上都遭遇到的难题。在台湾,我被认定是“外省人”,这十几年“外省人”又被操纵成有点被敌视的“中国人”,不管我的“台语”说得如何流利,如何自觉地爱这块让我成长的土地,但谈起台湾,在很多人的眼中是没有我的。
燕舞:您早年生活在眷村,后来又做过中学教师,最后才读完台大博士并执教于高校,其间又做过报社主笔,这是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取得这么多世俗成就,离开了最初的那种窘迫生活,你会有庆幸之感吗?
周志文:对不起,我不赞成你的论述,你说我“取得了这么多世俗成就”,是指在大学任教吗?做报社主笔吗?或是出了几本连自己看了都汗颜的小书吗?那些东西不要说世俗看不上它,距离“成就”也确实太远了吧。
我倒对你所说的“知识改变命运”很感兴趣,知识当然可以改变命运,尽管有好有坏,但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有点唯物的成份。为了调和“知识改变命运”的唯物色彩,不得不搬出“意志改变命运”这比较唯心的说法。我认为意志也很重要,求知有时也靠意志的力量,尤其当求知极度困难时。
当然,当视野被知识提高了后,自己的意志也同样提高了。所谓命运的改变,不见得都是因为知识的缘故,其实里面有唯物与唯心的成分。当然命运改变的结果有好也有坏,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燕舞:我读您的作品尤其是《同学少年》,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是您参加的葬礼特别多,是因为做了教授后还经常回到当年生活的乡下,还是您刻意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世事无常、功名利禄的虚幻?
周志文:这个问题让我讶异,是真的吗,为什么我都浑然不知呢?你记得杜诗有一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吗?我可能已到了诗中“访旧半为鬼”的生命过程了吧。一方面有点悲痛,一方面也只得任它了。
我很少借着死亡来提醒自己世事无常、功名利禄虚幻的想法(也许是有而我不自知),这种启迪来自大自然的很多。我从小就有看星空的习惯,很早就知道晚上天幕上的一束很不起眼的微光,都可能是比我们太阳还要大的一颗所谓的恒星从遥远处传过来的光,我们地球与它比起来,不只微不足道,甚至连存在都不存在(在它们所在的位置是绝对“看”不见我们的,因为我们地球不是会发光的恒星)。
但仅仅是我们这个连存在与否都有问题的地球,它的年岁都得靠几十亿年做单位来计算,你说我们还须藉人的几十年寿命来感悟人生的无常吗?
燕舞:由赖声川和王伟忠两位台湾知名创作人联袂执导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年初在中国大陆成功巡演;由“外省台湾人协会”举办的眷村题材的系列纪录片近期也在北京放映;《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廖信忠著,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也是去年以来的畅销书。
但我目力所及,您的眷村书写应该是同题材中写得最棒的单行本,而最棒的单篇文章可能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明珂研究员6月3日发表于《南方周末》的长文《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我之所以特别推崇您的眷村书写,是因为您“边缘中的边缘”的独特视角———眷村人是台湾外省人中的边缘,而您当年又是眷村中的边缘。眷村经历对您今天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志文:你这问题有故意触我痛处的感觉。先澄清一件事,就是我的小书《同学少年》并不是为了眷村而写,当然其中有几篇触及眷村的生活,但很多篇不是,大致上是写我青年以前的生活,那些无意中的描述,也许呈现了某些真实,可能是让你感动的地方。
你提问中捻出“边缘中的边缘”,这是我真正伤痛的地方。这句话对我的杀伤力,不只是在我眷村的身份上,而是在我的整体生命上,在整个文化与地域认同上都遭遇到的难题。在台湾,我被认定是“外省人”,这十几年“外省人”又被操纵成有点被敌视的“中国人”,不管我的“台语”说得如何流利,如何自觉地爱这块让我成长的土地,但谈起台湾,在很多人的眼中是没有我的。
我住过的眷村是个规模小的眷村,这种小的眷村在台湾整个眷村史上也不怎么能沾上边的,但同样有生老病死的消息,有的庄严,有的荒谬,有的既不庄严也不荒谬。是不是因为我“边缘中的边缘”的特殊触角所看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存在的事实。
关于大学
学校同仁被无关紧要的形式束缚得没时间好好研究、好好教学,他们有数不完的会议、评鉴,报不完的报表,还有就是“publishedorperished(不出版就死亡)”的压力,我发现中国大陆的比较优秀的教师,都被那些形式压力挤到边缘,跟台湾的没有不同。整个中国,不论哪一方,都没有传统的经师与人师了,这是教育上的真正不幸,希望两岸从事教育的人好好思考一下。
燕舞:在《记忆之塔》中,您对东吴大学的回忆几乎全都是灰色的。台大的经历显然愉快得多,您的硕士和博士都是在台大念的,后来又执教台大多年,那作为学生和教员两种不同身份,对台大的认识和体会是不是也有一个变化或深化的过程?有了在台大多年求学的切身经验,您在给自己的学生讲台大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时,是不是会更有体会?
周志文:我在台大的经验比起在东吴的当然愉快又“健康”许多,因为台大毕竟是大学校,天地比较宽广。台大依然结党分派,但你不去理它,它也不会来理你,这是它唯一的好处。不像其他学校,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一些令人烦的事,你不理它,它也会来惹你。
你所说的台大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老实说不很响亮,有点老调,我们台大师生是从未注意过它的。我在《记忆之塔》的最后一篇文章《在我们的时代》中曾开玩笑,“台大的精神就是:台大没有精神”。没有精神其实很好,如果表示是自由的话。
不只是对台大,我们对这世界的一切,包括知识与感情,岂不是同样在不断变化或“深化”?
老实说,台大有台湾最好的藏书,我其实没有好好地用到,我很少进那座高岸又冷峻的图书馆大楼。我的整个人生不是由知识与书本堆砌而成的,但我感谢台大给我的空间,让我有反刍我已有的知识,让我有冷静观察我的世界的机会。在其间,我发现某些以前从未见到的光,很小很小,但值得长期等待与守候的。
燕舞:傅斯年先生虽然只是国民政府接收台大后第四任校长,但似乎他的功绩最为后人景仰和谈论,台大校内纪念他的“傅园”和“傅钟”更是经常为人提及。傅先生虽以历史研究名世,但他1920年代末由英国转往德国留学时,也学过语言学;1926年12月应聘中山大学兼任文科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也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尚书》、《诗经》和陶渊明诗等课程;而且,他也出版过《诗经讲义稿》。
您对傅先生这样一位极富历史感的老校长是不是更有亲切感?您觉得他对台大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周志文:谈起傅斯年先生,我的心情很复杂。傅先生主持台大的时候,我还在宜兰乡下做小学生,而且他任校长的时间不长,好像还不满两年,我谈不上“认识”他。
但直到今天,台大同仁谈及傅先生,还是有崇敬之情,我想一个是“唯物”的说法,一个是“唯心”的说法。“唯物”的说法是,傅先生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台湾只有台大算是大学,师大还叫师范学院,成大还只是台南工学院,也没有中兴大学,只有台中农学院,“政大”也还没“复校”,台大对台湾所有知识分子而言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学术殿堂,台大校长自然受人崇拜了。
从“唯心”的角度看,傅先生是人文学者出身,他把人文精神带进了大学殿堂,他每周都与学生“通讯”,发抒自己的教育与生活的理念,登在学校的刊物上,而且也身体力行,自然能感格学生。他还亲自上一堂“国文”课,并且要求台大的大一学生必修的“大一国文”上学期上《孟子》,下学期上《史记》,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近三十年,到我进台大教书前后才逐渐改变。
傅斯年其实没怎么样,但他之后的校长没一个像他一样,都是热门的理工背景的学者出身,学有专精但欠缺人文素养,他们干的时间比他都长很多,但没留下什么可道的“遗迹”,可见在大学里,精神的建设远比物质的建设重要。
燕舞:傅斯年先生担任台大校长时也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显然有利于将史语所的顶尖学者以双聘的方式请到台大来,这对台大中文系具体又有什么影响?
周志文:当然有影响。是不是源自傅斯年,倒不见得。傅曾任中研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最多只能拉上史语所这条线,其实傅斯年之后的钱思亮校长在交卸了台大校长之后就又“荣任”了“中研院”院长,可见两单位的合作关系原本就很深的,“中研院”的某些单位就直接设在台大。
史语所与台大文学院的“合作”关系很深,我读研究所时,屈万里先生就是“中研院”的院士与史语所的所长(另还兼过“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系里龙宇纯、张以仁都是与史语所“合聘”的教授。史语所的王叔岷先生“终生”在中文系授课。其他如历史系、考古人类学系(后改名为人类学系)的合作也很频繁,这使得我们台大的学生受惠良多,至少使我们开扩了视野。如果说在台大受教育,学术的“眼界”会比较大些,这话是可以成立的。
燕舞:您是哪一年开始来中国大陆教书的,是龚鹏程教授介绍的吗(他此前也在北京师范大学有教职)?您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本部和该校与香港浸会大学在珠海合办的联合国际学院都有教学任务吗?在这里教书和在台大有什么异同?
周志文:我到中国大陆的几个学校做过短期的讲学,由于我与龚鹏程是长期的好友,我的行止可能与他有关,但在北师大却不是他“介绍”的(我与北师大的“关系”,说起来比他还深一点呢)。我后来在珠海的联合国际学院也是短期客座的身份,都没有任何“任务”可言。
我很喜欢与中国大陆的学生相交,他们比台湾的更质朴,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一般而言,也比我在台大的学生用功些。台湾这几年的教育只能用“涣散”一词来形容,学生也比较不能集中精神,这一点,中国大陆的学生较好。
我对中国大陆政府与社会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教育表示认同,但我也担心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跟台湾一样,都太重视形式。学校同仁被无关紧要的形式束缚得没时间好好研究、好好教学,他们有数不完的会议、评鉴,报不完的报表,还有就是“publishedorper鄄ished(不出版就死亡)”的压力,我发现中国大陆的比较优秀的教师,都被那些形式压力挤到边缘,跟台湾的没有不同。
整个中国,不论哪一方,都没有传统的经师与人师了,这是教育上的真正不幸,希望两岸从事教育的人好好思考一下。
关于创作
做主笔的,往往也可放言高论,所以台湾报纸上的社论,常可见到很好的文章。……我认识的很多主笔,都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骨气的。报社对这种主笔也十分尊重,主笔应邀写稿,后来因故不用,而高额的稿酬还是照发不误的。在台湾社会我看过不少人格分裂的人,但没一个是因写社论而起的。
燕舞:后来做过一阵子《中国时报》的兼职主笔,之所以没有放弃教职而改做全职,除了担心做全职后可能要写自己不愿意写的文章,是不是更主要的还是觉得自己“不够新闻”?
周志文:台湾的言论比较自由,而且几大报都是民间人士主办的,根本不接受政府的那一套。我曾担任《中国时报》与《中时晚报》的主笔,这个报系的主持人余纪忠先生,早年信奉自由主义,在他主持下,“中时”报系的言论比当时的《联合报》还要开放许多,他聘主笔,往往是因文笔“大胆”、见解高明而受他赏识的结果。
做主笔的,往往也可放言高论,所以台湾报纸上的社论,常可见到很好的文章。当然社论不署名,代表报社的意见,主笔下笔时也会考虑报社的立场而稍稍收敛,但不能收敛太过,否则就没有“舆论”的作用了。我认识的很多主笔,都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骨气的。报社对这种主笔也十分尊重,主笔应邀写稿,后来因故不用,而高额的稿酬还是照发不误的。在台湾社会我看过不少人格分裂的人,但没一个是因写社论而起的。
燕舞:您主编的“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从2008年8月到2009年7月,已累计出版了颜元叔、黄碧端、龚鹏程、林文月、汉宝德(建筑学家)、陈芳明、尉天骢、金恒镳(森林学家)和马森以及您自己在内的9位作家型学者的散文集。
但我觉得按照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文科教授,一般都应该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不必用“学人散文”特别突出。另外,这些散文集中很多文章都选自报章专栏,我对它们的品质还是有保留意见,大众媒体(而不是专业文学期刊)的专栏还是一种不太为我信任的文体。
周志文:谢谢你对“学人散文丛书”的批评,你说得很正确,丛书不能保证每本与每篇质量都一样好的。你说你对部分文章有保留意见,其实你说得很客气。那部丛书是一种尝试,学人的散文与一般文学家的散文毕竟不同,他们在散文中的“知性”往往被纯文学的作家诟病,但知性也是一种特色。
对你所说的“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文科教授,一般都应该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不必用‘学人散文’特别突出”,我是不很赞成的。文科教授尽管受过严格的训练,除了学术领域的,能拿得出来的文章(譬如散文)其实不多,要算好的,就更少了,所以定名为“学人散文”没什么不对。而且里面的人选,除了我之外,都可说是一时之选。至于选文有点参差,丛书的封面没能统一,影响了丛书的水平,是该由我这主编负责的。
燕舞:张瑞芬教授给您的《同学少年》和《记忆之塔》做的序言,都建立于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而且把您的写作放置在一个大的框架下来考量———比如,评价《同学少年》时她会联系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凤凰的书写;对《记忆之塔》,她有一个精准概括:“是那个《同学少年》里衣衫褴褛的孩童上了大学后遇见的惊奇世界,涵盖了六零至九零年代,台湾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三十年间,一个文化人的养成过程与亲眼目睹的斯文扫地场景。
”我因为喜欢张教授给您的两篇序才又去网上查了查,才知道她早年写过《胡兰成、朱天文与“三三”———台湾当代文学论集》。
像她这个重量级的文学批评家,在台湾还有哪些?台湾批评家的价值中立立场如何抗衡出版商或其他利益集团的商业“收编”或“招安”?
周志文:我不是批评家,我看不出台湾批评界整体的面貌,其次台湾这地方不大,但太过多元,几乎没法让你用一家一派来代表台湾。
据我所知,台湾的批评家几乎没有被出版商或其他利益集团“收编”与“招安”的状况,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的出版市场很小,没有什么收编与招安的力量,其次台湾阅读人口不算多,也不太用心,但总有主见,不会被收编的评论者牵着鼻子走。通俗读物尤其畅销书的状况我不清楚,也许有“收编”的事吧。
我认识张瑞芬教授很晚,因为她在台中,也没见过几次面,我很喜欢她对文学尤其文字敏感的程度,她从古典文学出身,后来“投身”到现当代文学的批评阵容中,由于她用功,下笔快又准确,不久就成为权威。
像她这样做批评的,在台湾有很多,几乎在中文系、外文系、台文所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都会对现当代作品做评析,有的把重点放在诗上,有的放在小说上,有的则放在议题上,如“后殖民文学”、“同志文学”之类的,但很少张瑞芬样的成果斐然。
张瑞芬与他们不同的是她的文学视野比较大,她虽然以散文批评为“专业”,却对其他文类也兼容并蓄地阅读分析,她写过几篇小说的评论,也是掷地有声的,她的文字有一种奇特的光彩。
她在评论中偶尔会流露出一点感性,她有次与我讨论,我说这感性是你“介入”文学的原动力,何必要全数抛弃呢?我认为在批评中作者偶尔流露的感性是合理的,因为他研究分析的是一个生命的创作,哪一种文学与艺术能脱离生命呢?哪一种生命是能排除所有的感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