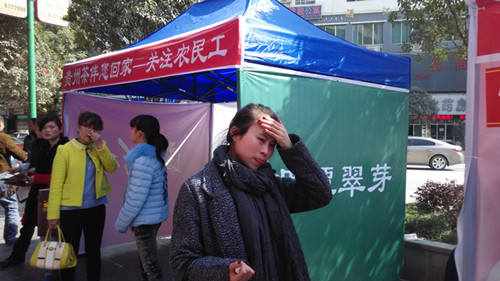贺雪峰村治的逻辑 贺雪峰: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2006年中央宣布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农业税在中国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皇粮国税已内化为中国农民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河北民谚“交了粮,自在王”(梁漱溟,2004:140),“自在王”是说国家不扰民,无 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原因不是国家不想治,而是传统国家是典型意义上的弱国家,缺少深入社会的治理技术。
“自在王”的前提是“交了粮”,“皇粮国税”不可免,但是,皇粮国税不能太重,必须轻徭薄赋。税赋太重就会引发严重问 题[1]。
进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不得不以现代化作为回应,现代化的前提是增加从农村社会的资源提取,以发展现代事业,如建立现代警察制度和教育制度,用于洋务运动,发展军事工业。传统的弱国家的基层治理制度 难以满足从农村社会提取大量资源的要求,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现代行政体系,以有效地从农村抽取资源。
晚清至民国,在抽取农村资源和国家政权建设之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 僚机构、而是靠复制扩大旧有的治理制度,即政权内卷化,从农村抽取的资源大多被非正式中间机构的贪污中饱所消耗,从而产生了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危机。[2]
真正完成国家政权建设,并能够从农村社会有效抽取资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通过政社合一的制度,将农民有效组织了起来,并因此完成了从农村抽取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任 务。
198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农村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国家越来越不依赖于从农村抽取资源来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以承包制为开端的农村体制改革,很快就由经济体制到行政体制。至1984年,人 民公社解体,乡镇人民政府成立,“乡政村治”的治理架构最终确立,国家将强有力地伸入到农村基层的组织体系收缩回去。
1980年代至2006年的20多年时间,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是在中国回应现代化要求中,要通过国家政权建设来扩大从农村抽取资源的1980年代前阶段,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从农村抽取资源,反而要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新 阶段的过渡阶段。
而1980年代前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家试图通过政权建设以有效抽取农村资源却很不成功的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完成了从农村抽取资源以建设 现代国家任务的时期。
这样,考察20世纪一百年的乡村治理,就有了三个十分不同的可考阶段。而正是通过窥视1980年代以来的过渡时期,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在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背后的逻辑线索。
没有疑问,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是承接19世纪中国回应西方挑战而不得不现代化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展开就是国家能否通过政权建设,建立起一个可以深入到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体系,以能够从农村有效抽取用于现 代化事业的资源。
具体可以展开为两个指标,一是组织体系能力,二是抽取资数量。较强的组织体系能力可以抽取较多的农村资源用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较弱的组织体系能力在强制抽取较多资源时,不仅会造成严重的政权合法性丧失 的后果,而且抽取出来的资源被中间层大量消耗,产生如杜赞奇所说政权内卷化的后果。
温铁军认为,20世纪一百年的工业化几乎都是由政府主导,都要面对如何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提取剩余的问题,也就是说:“谁能够解决政府与 小农之间交易费用高到几乎无法交易的矛盾,谁就成功”。
(温铁军,1999)温铁军的意思很明确,国家能够低成本地从农村抽取资源,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否则,国家就不可能有效回应西方的挑战。而除了英美等工业化超前的国家 更多依靠新兴资产阶级和市场外,德、日、法等工业化置后的国家,以及今天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一定要靠国家权力强制从农业抽取剩余来实现。
具体地说,为了回应西方挑战,中国不得不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转型,并进行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建设首先需要改变传统国家“无为而治”的状况,进而建立起强有力地向农村延伸的基层组织体系。不过,在缺乏现代技术条件 的情况下,试图建立起强有力的抽取农村资源的基层组织体系,却远非易事。
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的建立,往往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果,而非原因。考量中国的现实国情,一方面是小农数量庞大,高度分散,剩余很少,另一方面则是 农民的国民意识并未确立,却囿于一个个传统的村庄和宗族群体之中,中国是由一个一个以宗族等传统组织为单位的沙子组成的一盘散沙时,国家借以从农村提取资源的基层组织体系,更加难以有效建立起来。
如果不从国家与农民关系 的方面着手,我们将难以理解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效,同时也就难以理解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及其变迁的逻辑。
我们先从1980年代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说起。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实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制度,一是以承包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一是以乡政村治为架构的政治制度。乡镇政村治是指在乡镇一级建立人民政府,以取代解体的人民公社,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 选举村委会,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乡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看,有三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一是国家一直期待乡村两级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具体表现就是将各种现代性的任务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层层传达下去,这些任务最终都需要由农民 出钱出物和出工来完成。
这些自上而下的任务,与国家继续从农村收取的税费,是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两种方式,表现在农民那里,就是所谓“农民负担”。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或所谓的农民负担并非1980年代以来的新生事物,而是 自晚清现代化以来一直进行着的现代性事业的一个部分。
1980年代以来的乡村治理实践中,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的实施。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农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国家期待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户,在收获之后,能 够自觉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税费任务。
第三个因素则是乡政村治,是自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是由村民选举村委会来实行民主治理的制度,村委会并非乡镇的下级,也不被乡镇领导,而只是接受乡镇指导。从制度安排上讲,村民自治制度对 于维护村民的正当合法权益有利,村干部由村民选举,对村民负责。
在整个1980年代,分田到户不久,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有了相当的提高,农民负担不重,乡村干部不坏,轻徭薄赋,无为而治,乡村治理状况较为平稳,农村社会一片祥和景象。
但自1980年末期开始,乡村治理问题凸显,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农民负担过重持续得不到解决,二是乡村债务越来越多,乡村集体资产越来越少,三是乡村干部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干群关系日益紧张。最后,因为考虑到可能会诱发 的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国家不得不自2003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并最终在2006年通过取消农业税,来解决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恶化的乡村治理状况。
基于上述,我们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在1980年代末以后的10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农村的治理状况会迅速恶化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乡村治理逻辑在起着作用?及从中可以窥见整个20世 纪中国乡村治理中的什么秘密?
撇开1980年代不说,在1990年代的10年,国家为了快速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自上而下下达了很多达标升级任务,这从全国各地农村仍然残留的标语,如“人民工程人民建,建好工程为人民”等中依稀可见,也可以从中央下达 的数十个减轻农民负担文件所列禁止向农民收费项目中见到。
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向农民提取资源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1990年代国家向农民提取的资源数量,相对于人民公社时期,仍然是少的。问题是,为什么1990年代的压力型体 制,在短短10年多一点时间就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恶果?这就需要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去找。
国家从农民那里汲取资源用于建设各种事业,需要依托县乡村三级组织进行,正是通过县乡村三级组织,国家与承包经营的2亿多户小农打交道:国家从农民手中收取各种用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税费,而农民从国家那里得到部分公 共品供给的好处。
温铁军很早就指出,解决国家与收入很少数量极大的小农的交易问题,是理解20世纪历史的关键。(温铁军,2000)温铁军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但国家与小农交易的具体过程及机制,温铁军没有展开来讲,而这恰恰是理解20世纪 中国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
整个1990年代,在中央自上而下达标升级的压力下,县乡村三级除了向农民收取税费,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除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以外,县乡村三级自身的运转也需要通过向农民收取税费来维持。在1990年代中 国中西部农村,县乡财政收入的60%以上用于教育,如果县乡两级政府不能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诸如教师工资的发放、政府日常运转等都会成为问题。
也就是说,即使县乡两级为政清廉,没有任何贪污腐败行为,县乡两级也必须有效 地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如果不能从农民手中有效地收取税费,县乡政府将不能运转,各种达标升级任务也无法完成。
问题是,县乡两级不可能直接面对广大的农户,并从农户那里收取税费,县乡两级必须找到一个比农户大的缴纳税费的单位,这个单位就是村委会。有三个原因使得县乡两级无法直接面对农户,一是农户数量太大,每户所纳税费不 多,如果农户没有缴纳税费的积极性,或者说农户要抵制税费,县乡干部几乎不可能一家一户上门催收税费。
这样收税的成本太高;二是县乡干部对村庄的情况不太熟悉。村委会居于熟人社会之中,村干部住在村庄,与村民之间有着熟 悉的关系。
离开村干部,乡镇要收税,甚至无法找到纳税的对象。事实上,在1990年代,县乡向农户收税,根本不可能离开村干部,即使由县乡干部对某些“钉子户”采取强硬措施如牵牛摄谷子,也往往有村干部充当县乡的内线。
正是 村干部向县乡报告,谁是村中拒绝缴纳税费的钉子户,对谁采取强硬措施可以起到杀鸡吓猴的威慑作用;三是县乡干部无法有效核定每户应缴税费,也无法合理确定农户不能按时缴纳交税费理由的是否正当真实,农户是否因为疾病返贫 ,或遭受到了特大自然灾害而致粮食严重减产。
总而言之,因为农户的税额太小,而县乡对村庄农户的不熟悉,使得县乡两级向农户收取税费时,离不开村干部。农户作为一个纳税单位明显太小。只有当农户的负担很轻,他们有纳税积极性时,县乡才可以较为容易地从农户那里 收取税费。1990年代的情况显然不是如此: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达标升级任务,使得农民负担很重,一方面,由于干群关系普遍紧张,农户缴纳税费积极性不高,有些地方甚至普遍出现了抵制税费的情况。
县乡收取税费的困境在于,虽然大多数农户都是胆小怕事或有强烈纳税意识的人,却总有少数消极分子甚至钉子户不愿按时缴纳税费,甚至拒绝缴纳税费。拒绝缴纳税费并非没有理由,比如庄稼歉收或重病返贫,缴不起税费,或其 他编出来的种种理由,或干脆就是不缴税的“钉子户”。
如果县乡不能强迫钉子户缴税,或不能清楚地区分出不缴税(或减免税费)农户理由的村庄合理性,第二年就会有成倍增加的农户以相同理由拒绝缴税或要求减免税费。县乡收取 税费的难度每年骤增。
县乡两级为了能够将税费收取上来,就必须在村一级打主意。具体来说,县乡两级从两个方面来打村一级的主意,一个方面是从村集体方面打主意,因为中国农村实行双层经营的经济制度,村一级仍然是一层经营单位,县乡两级不 直接面对农户,而是将税费任务下达到村,再由村一级向农户分解,村一级变成了纳税单位。另一个方面是从村干部方面打主意。如果县乡两级可以调动村干部协助收取税费的积极性,县乡收取税费的能力必将大幅增强。
将村一级作为纳税单位,县乡两级将税费任务下达到村,县乡两级就可以从面向千家万户小农收取税费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然而,仅仅将村一级作为纳税单位还是不够,还必须调动村干部收取税费的积极性。村干部收取税费的积极 性,来自收取税费的难度和从收取税费中可以获得的报偿(及不能收取税费时受到的惩罚)的权衡,收取税费难度越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