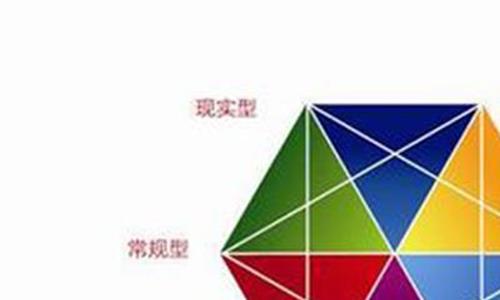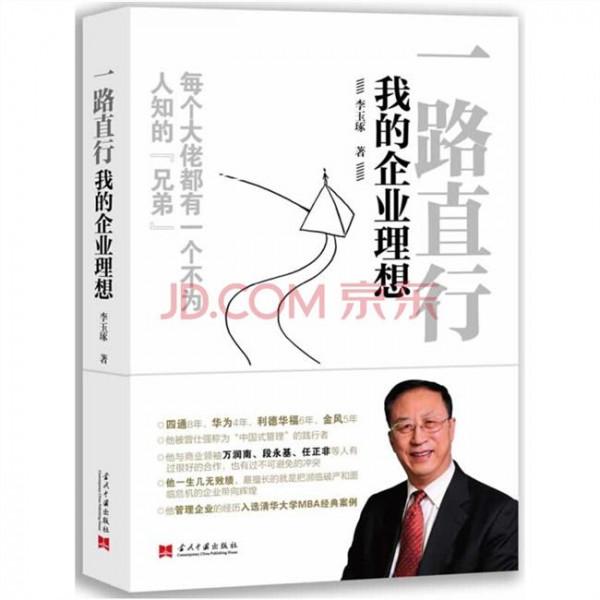第一职业经理人李玉琢 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实战手记
《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 他对最后一次见万润南的情形记忆犹深; 他与才智过人的段永基合作8年却不能成为知己;
他洞悉了四通衰落的秘密; 他与柳传志早已认识,却没有选择去联想; 他直言不讳评说华为接班人; 他三次力辞任正非的挽留而决然离开华为; 他六年贴出了几百份震撼人心的企业大字报; 他经历了沉痛打击后,写下了关于资本的思考; 他,就是历任四通集团副总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利德华福总经理的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李玉琢。
“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盛赞他为“中国式管理”的积极践行者。 近日,同道新文图书公司重镑推出李玉琢二十年企业生涯心血之作:《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该书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此书由曾仕强作序并推荐。书中为读者呈现了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跌宕起伏的企业人生。
在18年的企业实践中,李玉琢分别任职于四通(副总裁)、华为(执行副总裁)和利德华福(总经理),均很好地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并以其能力和品德赢得了历任老板的信任。在四通的时候,他是四通打字机的生产部长,后来又做了OA部部长,把四通的打字机做得十分风光。
在华为,他将快要死去的莫贝克拉回赢利的轨道,最后以60亿人民币卖给埃默生;他任华为合资合作部部长时,辗转全国和各地电信局组建了合资公司,为华为开拓市场立下汗马功劳;在利德华福,他同样也是将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打造成高压变频企业中国第一品牌。
18年中,“辞别”与“重新上路”是李玉琢的主题。他的离开皆因冲突而起,而冲突的根源在于李玉琢的性格(英雄情结,自尊自爱,锋芒毕露)与独立精神。
因为英雄情结,使他39岁时毅然放弃计算中心,投入四通创业大潮;放弃四通,投身华为;放弃华为,投身利德华福。因为自尊自爱,使他看不惯四通后期的权力斗争,离开段永基;让他无法接受利德华福投资者的猜疑、刁难,愤然而去。
因为锋芒毕露和独立精神,使企业强人任正非不断调动其工作,让利德华福投资机构的某些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该书一经推出,倍受企业高层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的关注,他们认为书中对于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检阅与反思。
对于中国顶级企业的商业领袖也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节选: 我眼中的万润南 20年过去,现在的人们所熟悉的企业家是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等,知道万润南的人越来越少。
即使提起四通,大家马上想到的也就是段永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段永基就是四通的创始人和代言人。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万润南没有卷入“六四”风波,那么,现在的他有可能是中国企业界最赫赫有名的人物。
万润南在四通的时间并不长,整四年。我和他共事时间更短,才两年多。但无论是做人,还是管理企业的能力,他都是我佩服的第一人。
也许早期投身的企业容易给人更深的影响,是他第一次向我们灌输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形态理念,如醍醐灌顶;是他告诉我们最大管理跨度8~12人等概念,把我们引上了企业经营这条道路。
尽管他不是我的导师,但我以他为榜样。他办企业的理念、追求和做法上的高度是我始终追赶的目标。 万润南,1946年生人,属狗。中等个子,一米七出头,白净脸,双目有神,相貌儒雅。
许多女同志认为他是美男子。 万润南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读书很多,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他很能写,也很有思想,讲话经常引经据典,他对四通中高层干部提出的“上下同欲者胜”就引自兵法。
万润南的修养比较完善,很难看出他有什么缺点。不像段永基和任正非,尽管也是大聪明、大能人,但他们身上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万润南是大师级企业家的风范,他的谋略与招数都融化在无形之中。尽管四通高层之间矛盾重重,但万润南的驾驭手段很高明,能摆平各种矛盾,使其各尽其责,又不致掣肘、激化。
段永基这样精明的人都对我感叹:“李玉琢,咱们这些干部加起来都不如一个万润南!” 在我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深受万润南影响的还有一条,那就是他的决策方式。
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说就是“听多数人的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人说了算”。这其实就是企业中的“民主集中制”。 四通衰落的真相 一个伟大企业的成功一定是和理想分不开的,四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营企业经营理念,并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独树一帜,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这些超前的思想、观念及做法,是同时代任何一个企业无法企及的。 在我看来,四通的衰落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六四”,另一个就是标志着创业理想沦丧的“打工意识”大辩论。
四通本是全体四通人以主人翁的精神拼命干出来的,积累的财富也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我认为让大家树立所谓的“打工意识”,无形中把具有实际支配权、控制权的人(少数几个四通高层)置于老板的位置,就是要把大家共同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
可以说,四通经营上的失败是打字机之后的“多元化”,这方面出问题是明摆着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想纠正有可能;但思想上的失败,意识上的混乱——把四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强硬地用一些十分错误的(至少是可疑的)东西来替代——是无法扭转的。
以这次辩论为标志,四通从根底上完了。 我眼中的段永基 段永基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没有谁能正确评价他。
我在四通的8年间,段永基始终是我的领导,我们合作时间最长,是非常默契的工作伙伴,但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同路人和不分彼此的朋友。 段永基跟万润南同岁,1946年生人,1970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曾做过几年的中学教员,再后来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研究生。
毕业后到航天部621所工作,做到研究室副主任。四通成立不久段曾带研究所的一个粉末冶金项目进来,但没搞多久就下马了,他也很快离开了四通(崔铭山认为:段是因为四通被查才离开的,说明段当时不坚定,是逃兵。
但我从万和其他人那里未听到此说)。段永基第二次正式加入四通大概在1986年中,初期只是在进口采购部门做王安时的助手,这一段共同工作为二人后来的合作与友谊奠定了基础。
合资企业办起来之后,我和段打交道就多起来了。
我作为中层干部经常要和他一起开会,我觉得这时候段永基办企业的能力开始显现出来了。安排事情头脑清楚,十分干练。好像什么事都胸有成竹,其实有些事也不是很有把握,但他总能临危不乱,想出解决办法来。
他的工作精神也是我很佩服的。他很少休息,任何短暂的时间都能休息,或者在车上随便眯一会就够了,精力充沛,脑袋瓜子永远在转。他到现在都是这样,早上8点以前必然出现在办公室里,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一定是晚上10点钟以后。
段永基的精力头两年基本都放在合资公司(SOTEC)的发展上,我和他的合作非常好。我当了副总经理后,合资公司的事基本不用他操心,他也十分放心。
此外,段永基才气横溢,讲话有说服力,文章写得也好。在四通,像他这样能说、能写、能干、又有思想灵性的人,除万之外,无人能及。 在合资企业的前期和四通的前期,段永基的工作是极为优秀的,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他是万润南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 在“六四”风波那样一种可能危及四通存亡的重要时刻,段挺身而出采取各种措施,使四通避免了可能的混乱、分裂和解体,表现了四通领导层从容应付危机的能力;在那微妙阶段,当人们认为不便由他主持公司工作的时候,段同意由沈出面,并没有计较权力的得失。
但随着事情的平息,公司逐渐恢复元气,外部压力减轻之后,内部的问题开始露出头来。 一个问题是沈主政时期,沈、段一个比一个更积极地批万提出的办公司的一些思想、理念、口号、做法。
我一开始以为是政治需要,后来发现是真的,是真的要否定四通当年正确的东西,以至于完全拧着劲做事情,在用人上、经营上、内部关系上,都尽量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做法。这就会进入误区。
万润南有政治上的问题并不一定说明四通这些方面也错了,这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硬着头皮非要逆着来,不仅不是纠正什么,反而自入斜路。 另外就是派性和权力斗争的逐渐表面化、公开化。
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使段必然身陷其中:第一,“六四”危机和工作组进驻阶段,出于公司的稳定的考虑,大家同意将董事长、总裁大权都交与沈,但公司的主要经营工作仍然由段全力维持,本来从能力、实际作用、威信以及公司最后时刻的安排,段都是当仁不让的最高领导,但事情逐渐过去后,沈却并没有意识到主动及时地让出至少是总裁这样的职务与段,这就逼迫段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权力要求。
斗争的后果是,四通从此再未平静过,以沈和段为首的明争暗斗使四通的元气大伤;第二,尽管段始终处在较为主动有利的位置上,但1991年他得到总裁职位后,因无人掣肘,独自决策过多,严重失误增加,一年多后反而迎来七董事联合倒段的个人危机;第三个后果是段个人性格上的变化,主要是对人的不信任,这既可能有他自己身陷权力斗争中形成的习惯,更有朋友叛变(如王安时的反目)给他的教训。
颇具亲和力和行动能力的老段不见了。以至于后来段宁可信任司机,也不相信包括我这样与他并肩工作多年的伙伴。
“六四”后,四通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失去了方向。无论沈主政时期、段主政时期,他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四通的产业方向这样重大的问题,头脑发热和多头政治,使四通这样本来方向明确的企业,从此在可能想到的各个领域都插上一脚,留下数不尽、还不完的窟窿账。
所有这些后果中,四通的许多领导人(包括万在四通鼎盛期分封诸侯式地将许多高层派出创业的后遗症)都或多或少地负有责任,段自然也不例外。
以他的地位和能力,他完全可以把四通带到另一条更为健康的路上去,正如联想、华为的领导人那样,这两个公司同样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却并没有像四通一样宿命般昙花一现。
惟一不变的仍然是段的聪明和能力。他永远都是能解决问题的能手,可惜他的精力和智慧过多地耗费在无穷无尽的“挖坑”与“填坑”过程中,这是十分可惜的。
他仍然表现出异于常人的顽强斗志,无论多么不利的局面,他都有办法渡过难关。 段永基对我的影响很大,正面的影响使我在四通8年而无悔,负面的结果让我这个准备在四通干一辈子的人也只好无奈地痛哭离去。
他的前期告诉我哪些事情该做,他的后期也使我明白了什么事情不该做。 我为什么没有去联想 在我决定离开四通的时候,也曾有过去联想的闪念,并没想到深圳那么远的地方去工作。
联想我很熟,柳传志我也早就认识。我在中科院计算中心013机房工作时就认识柳;另外,四通、联想比邻而居,两个企业创业者都是科学院出来的,相对有一种亲近感。
但是,我并没有主动去找柳传志。 在老婆陪我参加的那次招聘会上,我也看到了联想的招聘摊位,但我没有想去联想的冲动。
联想搞汉卡,也销电脑,不具有四通打字机的独特性,在我这个学计算机的人看来,联想没有什么新的技术。
联想卖的电脑是普通技术产品,属于自己的东西有限,普通技术产品的弊端就在于门坎低,谁都可做,靠量取胜,利润很薄。做这些东西太平淡无奇了。而我愿意做独特的、有挑战性的事情。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联想的伟大,它的伟大就在于能把一种平淡无奇、谁都能做的产品经过顽强努力做到中国最大,又能在与世界电脑巨头的较量中争得一席之地。
这也是做企业的一种方式,但联想的平实对我缺乏吸引力。
比较之下,华为使我产生了更多的兴趣。第一,华为是搞通信的,我的专业敏感告诉我,随着电脑的普及和应用的深入,未来几年电脑技术必将与通信技术紧密结合,通信行业将有一个飞跃的发展;其次,华为当年拿电路板给深通公司加工时就有人对我说过,这家搞通信的公司设计水平很高,来人的素质也挺高,产品也比打字机更复杂、更精密。
进入华为之后,我又发现,华为是我喜欢的那类富有想像力和充满激情的企业。
八评华为接班人 一大批“娃娃副总裁”们被任正非摸着脑袋长大,任正非给他们高待遇,破格任用,但对他们的要求是听话、忠心,即使任正非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也得如此。
任正非的脾气很坏,是我见过的最为暴躁的人。
我常看到一些干部被他骂得狗血喷头(高级干部尤甚)。有一天晚上,我陪他见一位电信局局长,吃饭吃到9点。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他回公司还是回家,他说回公司,有干部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李鹏要到华为)。
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到了会议室,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没两行,“啪”地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于是骂了起来,后来把鞋脱下来,光着脚,像怪兽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半个小时。
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干部,讨论一件事情到最后就会说:“你这个方案不行,任总不会同意的,老板会生气的。”大家讨论问题,已经离开问题的本身,常常以老板的喜怒哀乐为转移。
任正非提倡对事负责,可华为高层很多人恰恰是对人负责,他们在渐渐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同时,可能丧失独立的意志和人格。那些独立意识和自尊心比较强的人要么走掉了,要么其智慧和能力也慢慢退化了。
我走之后,孙亚芳说我离开华为是因为没有接受华为的文化,她说得对。我的认识的确与华为文化有很大不同,我不喜欢被驱使的文化,我喜欢独立空间的能力发挥。
我认为高级干部应该为老总分担工作,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汇报工作。 我觉得任正非应该培养李玉琢式的干部,但他没有,而且似乎也不愿意。这一点上他还不如段永基。
段永基为干部的成长着急过,对于各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干部相对还是会给一定的工作和发展空间的。 下面请看任正非的几位曾经被认为可能的接班人的情况: 李一男: 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硕士研究生毕业,初到华为时在研发部,于郑宝用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部总裁。
他后来做了莫贝克第三任总裁。上任之前,他找过我,问了莫贝克的情况。他是华为副董事长,1996年他才二十五六岁时就是华为副总裁。任正非对他很亲切,人们都背地里叫他是“任正非的干儿子”。 李一男的业务能力很强,他管理研发部时,大家都很佩服,说三道四的很少。
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管理水平一般,没有独立办企业的经验、能力和耐性。在后来单独办企业的过程中,他有意无意要照搬任正非的一些东西,这反而可能导致失败。
像李一男这样在华为如日中天的人,最终也会离开,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诧。据说是因为他与孙亚芳矛盾比较尖锐,工作看法冲突很严重,彼此之间曾经互相吵过。
开始时,李一男负责的是与市场总部平行的产品总部,当时孙已是董事长,难免对李一男所管部门的工作指指点点。
李一男认为她是外行,当然不买账。通常情况下任正非会站在孙亚芳一边,最多是哄一哄李一男。李一男在华为一直顺风顺水,何时受过别人的气?见任正非支持孙亚芳,而不是自己,自然怒从心头起,心想还不如出去创业算了。
我临走时向他道别,他居然跟我说:“走吧,走吧。”一点也没有挽留可惜的意思。当时很奇怪,现在想来,他恐怕那时就有了出走的念头。我后来曾问过他何时有了离开华为的念头,他说是被派到莫贝克的时候。
那应该是1999年底。 郑宝用: 我1995年刚进华为时,郑宝用是华为惟一的常务副总裁,大约半年后他却突然被撤了。
郑宝用是个很有能力也很有思想的人,是华为开发的有功之臣,如果好好培养,能干成大事。能不能成为任正非的接班人我不好说,因为接班人不是说想培养谁做就能培养成的,我认为做企业家得有素质、悟性和能力,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郑宝用人品不错,与大家关系都很好,脑筋反应也很快,华为的海外市场(香港市场)首先就是由他打开的;据说莫贝克卖给爱默生的主要谈判也是他做的。
在李一男之前,郑宝用负责研发。有人说后来郑不得不离开研发,是任正非有意在他与李一男之间制造矛盾,让郑宝用难以工作。
郑宝用的常务副总裁为什么被任正非撤下去?一种说法是,任正非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防止郑宝用有松懈之心;也有人说是他与孙亚芳的矛盾导致他被弃用。 后来任正非就让郑宝用负责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和临时的事。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飞机,我直言不讳地说:“郑总,我觉得你这几年很压抑,你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解的人,应该在华为单独地挑起一些工作。可是你现在像是在打短工一样,东一茬西一茬的,你不觉得委屈吗?”他叹口气说:“很多人都劝我离开,但是为了华为大局,我不能动。
华为到今天不容易,很多弟兄在看着我。” 大约2003年时,他不幸得了脑瘤。华为倾力为他医治,居然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我估计他再担重任的可能已经不大,保持身体健康对他是第一位的。
聂国良: 我刚进华为时,聂国良是电源事业部总经理。莫贝克改组,他带队整建制加盟莫贝克任副总裁。不久回到华为总部,迅速晋升为常务副总裁。据任正非说,提拔聂是由于他能大胆引进人才。
任在华为从未公开提到哪个人是接班人,但在1997年初让聂到莫贝克兼职的时候,任曾说:“我准备让聂国良将来做华为的总裁,因此只能兼任莫贝克的一些工作,不能调去。”那一阵聂成了华为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什么事都交给他,大有权倾一时之势。
后来聂在莫贝克做了整整3年的总裁,没有表现出格外的领导能力,但还是很尽心很努力。有一次在青青世界,因为一个干部的使用问题被任狠狠地骂过之后(我与付恒科在场)曾向我哀叹:“没法干,怎么做都不对,看来只好辞职了。
”不久聂就提出辞呈,做了一段审计工作之后,大约于2000年离开华为。 有一次我在深圳见他,问起离开华为的情况,他不满地说:“交上辞呈不久任正非就找我谈话,说了几句出去做事不容易的话,没有3分钟就把我打发了。
”显然在任正非的心目中,聂从来就不是有分量的干部,聂的威信、能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任连稍微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聂怎能不伤心? 据聂自己说,任正非之所以用他仅仅是为了平衡郑、孙二人的关系。
果真如此,任不是也用他对付过我吗? 孙亚芳: 对于任正非这样一个个性极强又极具操作力的强势领导人,在华为公司,孙亚芳是他最给面子又最能听得进话的人。
孙的真正作用,也许并不像她目前所担任的职务——董事长那样规划企业或决策指挥,大多的场合是助手、参谋、政委的角色,尤其任不愿出面或不便出面的场合,由她充当特使的角色,则会比任的暴躁、刚烈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工作的推进。
孙的聪慧、干练以及对任的脾性、思想的领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及的,包括她极好的英语,都是任所倚重的。任、孙合作长达15年,如果不是由于思想理念的一致以及为人处事的合拍,则不可能会这么久。
在干部面前,在多数场合下,任对孙似乎言听计从。说她是任最为信赖的助手似不为过,不然也不可能将董事长这种法理上的最高职务让她担任而不是别人。
孙尽管在公司高层多年,并见过许多世面,但她成为华为未来第一人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很大,因为她从未单独操作过企业,她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三辞任正非 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
主要意思是:在华为工作了4年6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
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惟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封辞职书,大致内容和前两封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来谈话。” 郭平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
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质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
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
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凝重。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都要走的人了,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轻的了。
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
”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
”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呆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20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
”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
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
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
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
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左右,任最后对我说:“好,李玉琢,那你先养病去吧!
”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辞职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赴京,考虑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准我辞职,走时给任正非留下了一份离职报告。
写完离职报告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 就这样,我于11月5日启程飞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