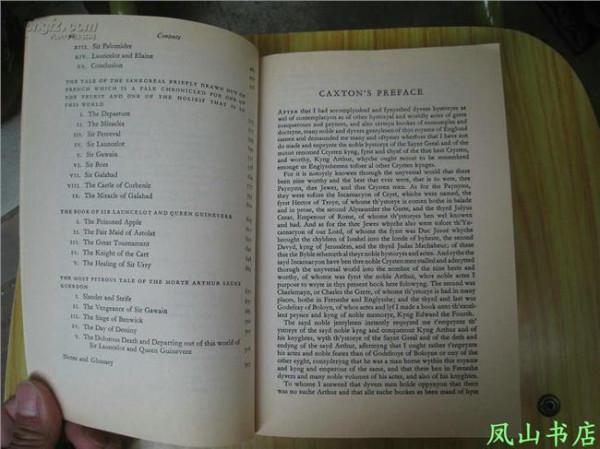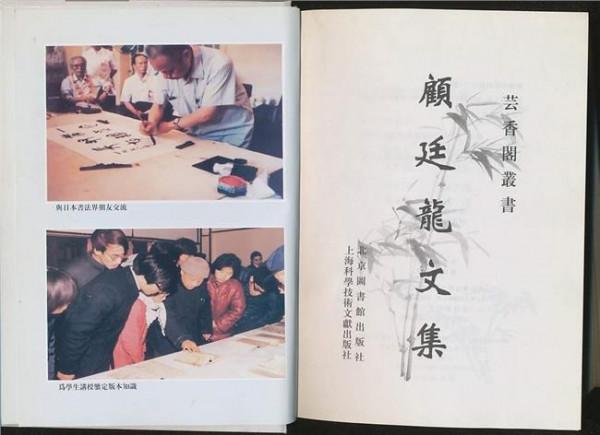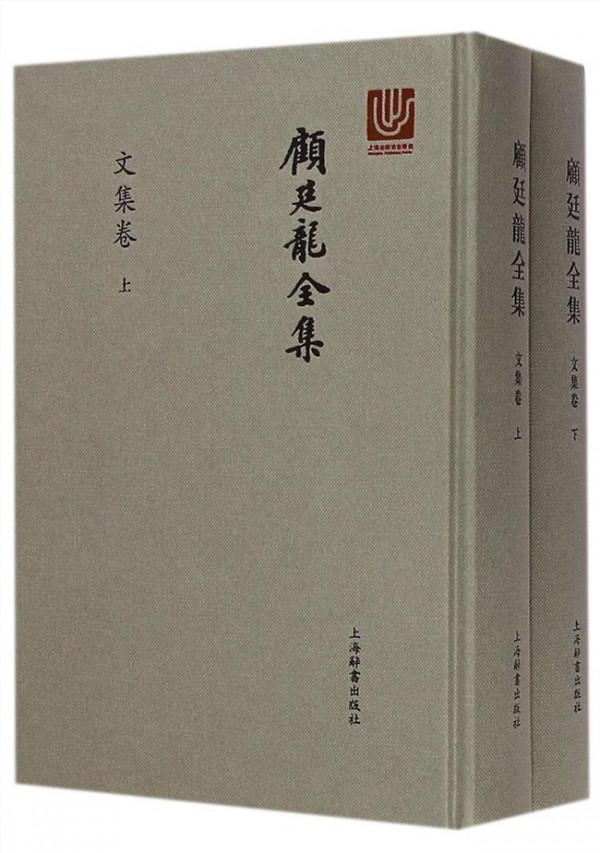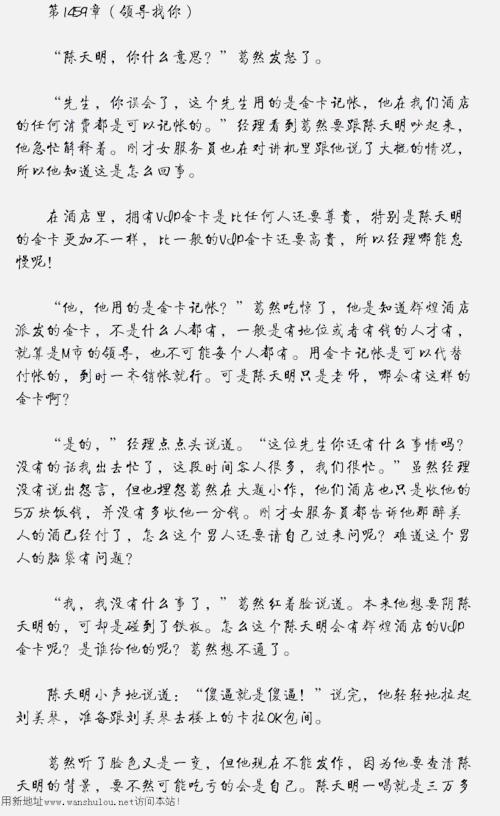《顾廷龙文集》集外文引言
先师顾廷龙(1904-1998)先生是中国图书館事业家、目録学家、版本学家、文献学家、书法家。他从1932年任职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从事採购古书的工作始,1939年为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1953年任合众图书馆代館長、1955年任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館長、1958年任上海图书馆副館長、1962年改任館長、1979年再任馆長、1985年为名誉馆長。
先師的貢獻並不在于曾主編《合众图书馆丛书》、《中國叢書綜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索引》、《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續修四庫全書》等重要圖書,也不在于編有《叶景葵杂著》、《涉园序跋集録》、《王同愈集》、《尚书文字合编》(与顾颉刚合编)、《明代版本图録》(与潘景郑合編)等,而是更在於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他夙興夜寐,備嘗艱辛,殫精畢力,竭心盡意地协助叶景葵、张元济等創设合众图书馆,為國家、為民族保存了大量重要傳統文化典籍。
津以為從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南京奏准清廷創設江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前身)始,至2007年止,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百年中,出現了許多重要學者專家,他們博古通今,見多識廣,業精於勤,自強不息,在事業上功成事立,作出了出色成績,如王重民、趙萬里、潘景郑、冀淑英等。
但在館長任上,有杰出成就及貢獻者卻不多,前輩如沈祖榮、袁同禮、蔣復璁、杜定友、劉國鈞、李小緣、裘開明、錢存訓等皆屬此類人杰。而先師從事图书馆工作近六十年,老成練達,處實效功,视图书文献为生命,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图书馆事业,他是事業上的德厚流光、北辰星拱的人物。
先师的《文集》於2002年7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7年了。今年8月22日,是先师去世十一周年的日子,津无以为献,谨以所輯「《顾廷龙文集》集外文」作为紀念。
先师文集的編輯,始於1980年秋,当時先生和我都在北京香厂路招待所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編輯工作,先生是主編,我是经部分科副主編,师徒两人朝夕相处。
某日晚,我对先生说:除了《吳慮(客下加心)斋年谱》、《古匋文晋(三子下加日)録》外,您过去还写过不少文章,包括在一些书上的題跋,我很想回到上海後,将之收集起來,将來或許能編一本集子。先生听后並未反对,只是説,当年在燕京大学時,有过几篇文章,在某報上也发表过一些,但時过境迁,再找就不容易了。你想做,那就試試看吧。
次年,我们在上海進行善本书目經部的複审,有一天,先生交給我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他的几篇论文的抽印本。从此,我就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先生文章的收集工作。
星期天,我根据先生提供的線索,在徐家汇藏书楼翻阅旧報紙老期刊;星期六的下午是业务学习時间,我就抄録在善本书庫中的某些顾跋,加上先生陸续交我的一些抄件以及印刷品,到1986年年初,已有近百篇约二十萬字的初步成果了。
也正在這个時候,我作为美國紐約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訪问学者,将去那里作图书館学的研究。離沪前的一天晚上,我去先生处辞行,並帶去了我整理收集的先生旧日发表的文章和题跋。
我告诉先生:我雖去一年,但不知道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为了保險起見,這些抄件及收集的文章还是由您保管,等我从美返国后再継续收集整理吧。1987年秋,我回到上海没几天,就和先生一起去深圳参加中国图书館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了。
在火車上,我们又談起編《文集》的事,我表示,等我有暇,当再继续您的《文集》編輯工作。先生也告诉我,他又有了几篇新作,还想起「文革」前写就的几篇前言。然而,這之後,我工作的担子加重,部门工作之外,会议应酬接待,使我难以分身。1990年4月,我離沪定居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自此为先生所作诺言終成空谈。
然而,文章的継续收集及編輯並未中断,先師又委托陳秉仁、任光亮代为查找並复印,1995年6月20日先师致陳任札云:「親友每勸吾收拾旧稿,自问实无佳什。
文革前沈津兄为我抄了不少,甚为可感。」信中提供了一些線索,請陈任收集(按,此当为1981年時事)。誦芬院士在《文集》編后記中説:「此部文集,蓋由先父弟子沈津先生始輯於1981年,继而由王煦华、朱一冰先生续輯並繕録整理於1996年,约得25萬言。……遂委陳君先行为之增补而总其成。」
《文集》出版之前的2002年3月末的一天晚上,在北京的誦芬院士打來电话,他问我,你是否知道我父親的文集已編好,马上要付印的事?听了此言,我表示已有較長時间没有此方面的消息了,且先师健在時有言:文集的序言,要請王煦华、沈津写。
所以我还在等通知呢。誦芬院士嘱咐我説,那就請你将《文集》的目録細看一遍,如有修改意見还來得及。由于時间緊迫,我請他立即致电上海,請有关人员当天(国内的早上)必须将目録送到上海书店出版社,交金良年总編輯第二天赴美交我。三日后,金总和我在华府的美國亚洲学會图书館年會上晤面,当晚我即将目録匆匆浏覽一遍。
返回哈佛後,我抽暇将《文集》目録和我在「燕京」期间陆续收集到的数十篇先师文章加以核对,汰其重复,补其所遺,共得十四篇,請金总返国後交有关人员增入。匆匆之间,津对目録中某些訛误还是未能驗出,如非先师之文也混入其中,又相同内容且引文一致的两文也未能去其一,這是颇为遗憾的。
我想说明的是,《集外文》,共73篇,計跋62、序3、传1、札2、其它5,都3萬餘字,均为2003年津撰写《顾廷龙年谱》時,得之於顾师寓所之箱篋,也有工作之暇巡架翻書所得,以及姚伯岳兄提供的二篇。
前面的23篇跋文,見於《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论文集》。最后的二通信,是从津处所存众多先师致友朋手札(复印件)中选得,其一为致陈叔通信,陈为「合众」董事,1949年後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長,此信涉及「合众」解放初期的阅览、人员、经费、捐款等情况,盖为「合众」於1953年5月捐献政府,由私立轉为公立前之見证。
其二为致南屏札,南屏者,不知何许人,時间当为四十年代,先师对办图书馆的見解以及困难之处言之歷歷,一覽无遗,言词率直,坦诚相見,此札当可视为「合众」在四十年代煞费苦心保存传统文化之一斑。
先师一生勤奋,学识渊博,治学严謹,著述不輟,所撰大部皆已刊布,未发表者,津雖小有拾遺補苴,当仍有遗漏,亟盼大雅君子,多有遞補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