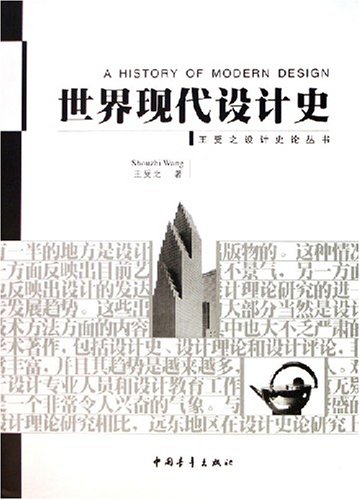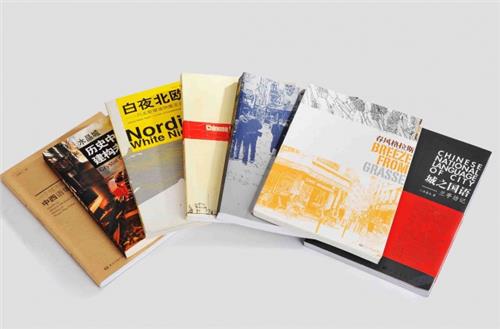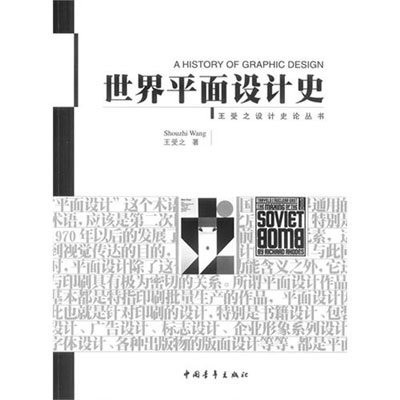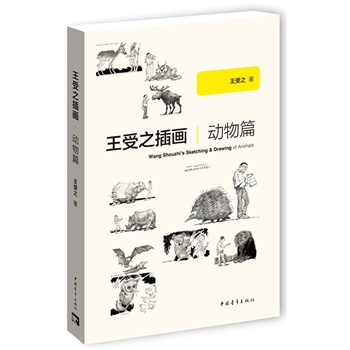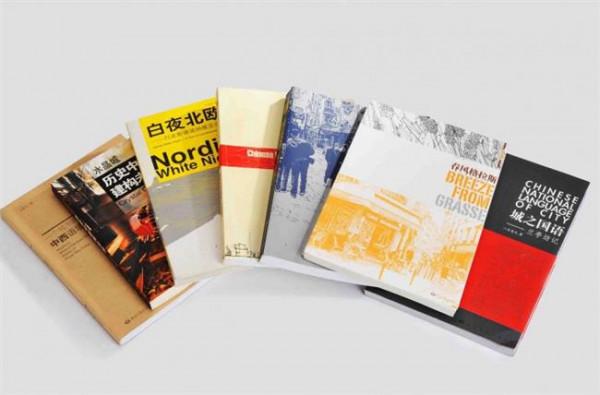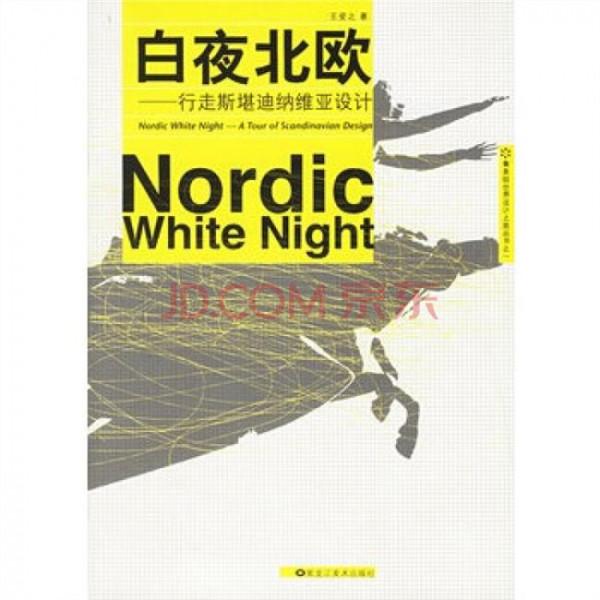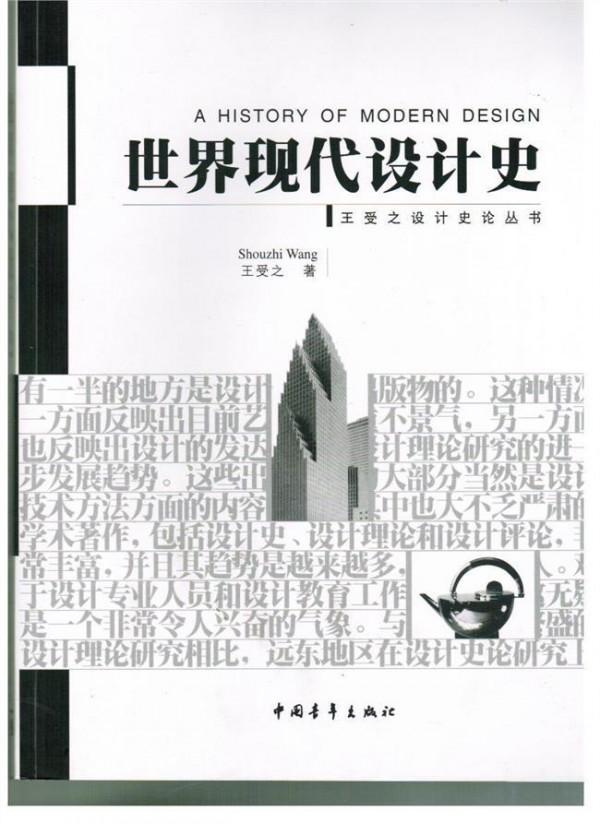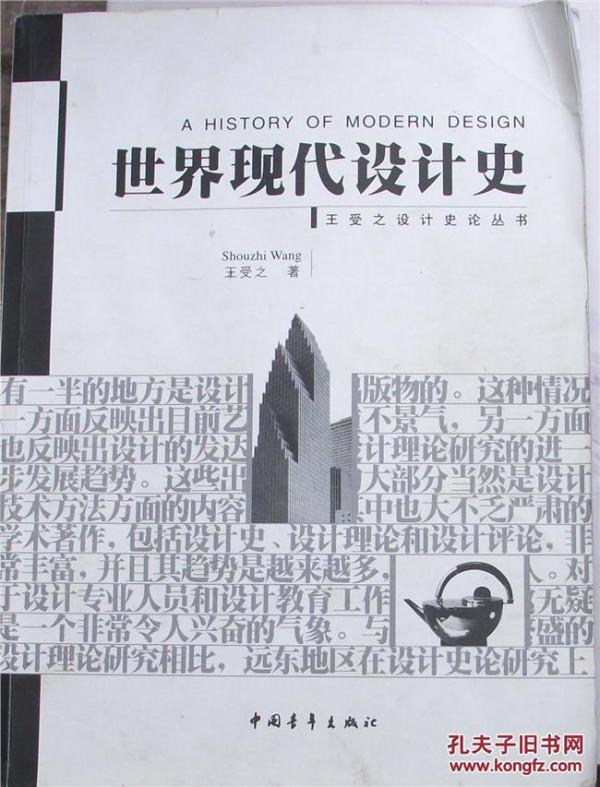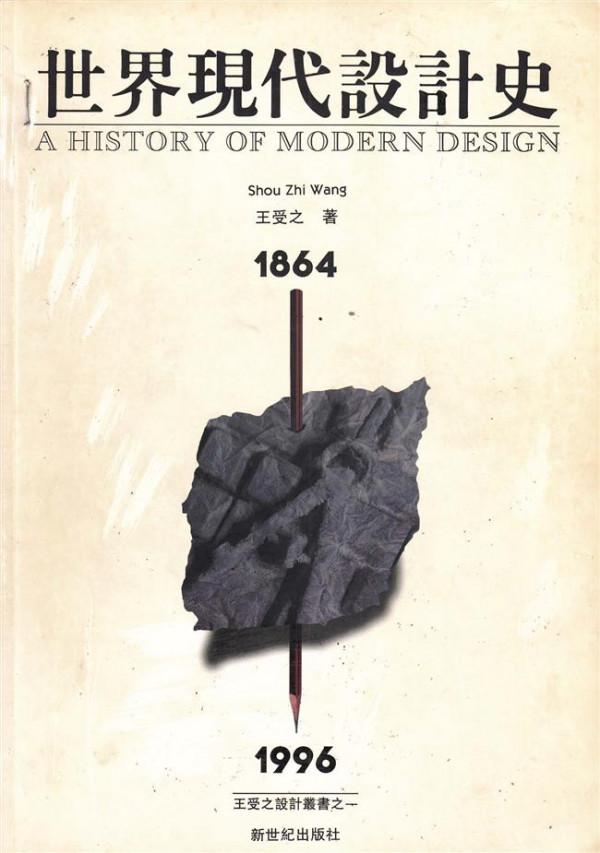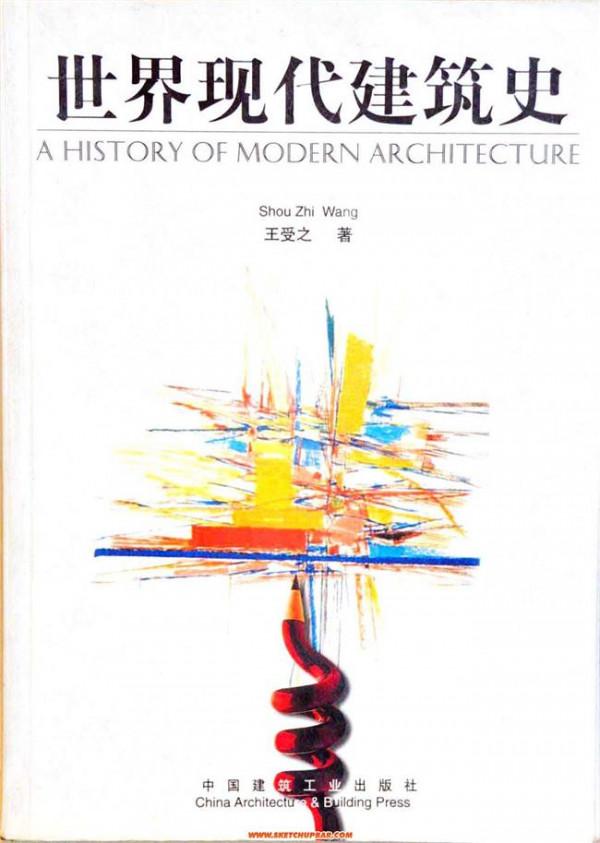阅读|王受之谈设计教育
本文转自《设计通讯》。《设计通讯》是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刊,是汇聚全国工业设计发展信息的平台,其读者为设计业界的高端人群。
在美国,独立的艺术和设计学院,全国大约有60多所,私立为主,其中1到2家是公立的,像马萨诸塞州艺术学院是公立的。我曾经在三四十家大学讲过课。在南加州当老师的是四家,在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是终生全职,另外三家兼课,分别是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奥迪斯艺术与设计学院、南加州建筑学院。
南加州大概有30家独立的艺术学院,有比较出名的,还有一些不是那么出名的。我在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教过书,那个学院是1972年由迪士尼公司在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地方建立的,是个综合艺术学院,最有名的是动画,我在艺术评论系教过几个学期。
还有一家叫奥迪斯艺术与设计学院,我在这里兼过几个学期的课。我在南加州建筑学院教过两个学期的课,主要是教建筑史。
另外有些学校,我去讲过课,但不能算教书。应该说,我对美国的艺术与设计教育体系没有很全面的了解。在美国,有艺术专业的大学,据美国人的统计大约有两三百所,大概综合大学基本上都设有艺术专业,小的就叫系,大的就叫学院。我只能说,美国的艺术与设计教育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没有统一性,差异性很大。而制约差异性的元素很多。
第一个,是市场的需求。比如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需要动画的人才,因为它是迪士尼的学校,所以他的动画很发达。我教书的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适应美国的工业产品设计,所以汽车设计很强。等等。相比之下,中国的1000多个有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大学,他们其实都很相似,这主要是因为所有的学校都受教育部管辖,并且影响这1000多个学校教学体系的是以中央美术学院为标志的所谓学院派体系,这套体系影响很大。
而美国的教育部是不管大学教育的。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差异就是,他的学院当中没有共同的东西,差异性很大,而我们的同一性很大。所以,中国的设计与艺术教育是同质化的教育,教育出来的人才也就比较同质化。
当然,有些学校的资源比较好,比如十大美院,北京的中央美院和清华美院,东北的鲁迅美院,西北的西安美院,西南的四川美院,中南的广州美院,还有中国美院,天津美院,湖北美院,南京艺术学院,其实他们也还是蛮相似的,大同小异。
这个我们解决不了。虽然国内系统下的培养路径有些差异,但实际上还是很接近。再想想我们的高考制度,也是造成这样结果的因素,全国几十万人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素描色彩速写。所以,招收进来的学生,他们接受过的训练也都差不多。在这种体制之下,要想有些特别的设计人才出现,比较困难,因为他是同质的、标准化的。
美国的设计教育中的哪些东西能够为我们所适用呢,那就是,未来我们应该有更多有自己特点的学校出现,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比较困难。同质的情况,特别是受美术教育的影响而形成的同质化,在很多院校还是很严重的,能够把设计作为独特的体系凸显出来的学院,在中国还真是不多。
其中做得有点特点的,我认为清华美院、中央美院做的有点苗头。还有做工业产品设计的,像江南大学、湖南大学,也有些特点。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美国那种百花齐放的状态。
我不认为这是某个人的认识问题,可能这是体制所造成的结果。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未必是一个问题,大概这就是一个现象,并且目前市场对这个同质化还是接受的,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还是能够找到工作,恐怕还没有到必须改革的地步。
如果说美国的设计教育体系中哪些东西对中国有用的话,艺术设计是创意文化,创意文化需要不同的天才,如果用同质化的方式去教育的话,培养出来的人恐怕就是同一种类型的人。这个问题,我其实没有什么答案,也不追求一个结果,只不过是做一些比较。
但是我并不悲观,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改变的。当然,我们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教育能够有一小部分开放给外国比较强的设计学院来竞争,比方说外国的大学在中国有独立的培养设计和艺术人才的可能性,对目前的同质化体系有一定的动摇,但我估计近期还不可能实现。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简称CKAD。我是在2011年接手,2012年正式上任当院长。当时的院长是靳埭强先生。我结束了在美国20年的教学,到这里来当院长。美国的教学方式,我采用的很少,主要原因是,体制的嫁接比较困难。
汕头大学是国内比较特殊的一个大学,有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所以在办学方面有一定的独特性。汕头大学比较早地采取了学分制,这在国内属于比较早的。汕头大学的英语教育,成立了语言中心,由外国人来教英语,有几个学院的英语水准在国内同级大学中属于比较好的,比如文学院、新闻学院、商学院。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建立在2003年,在这之前只是汕头大学的一个艺术系,2003年李嘉诚基金会给予了很大支持,成立了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那个时候,由靳埭强院长引入了许多新概念,进行了改革,设立了很多与设计有关的专业。
如果说我把美国的教学体制引到这里来,没有什么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教育管理方法是遵循教育部所制定的,包括我们的很多学科名称,是按照教育部所列的表来进行的,对于课程的改革也不容易,很多专业的设立需要很长时间的申报。不过,有一个事情,我是受了美国的影响,并且贯穿在我对学校的领导过程中,这就是,比较讲究市场的适应性。
我们学校很小,整个学校4个年级的本科生只有750人,研究生不到100人。专业太多,有七八个专业方向,每个专业方向平均算起来有五六个老师,所以资源很有限,每年国家拨给我们的预算一点点,很有限。在这样有限的资源里,要让学生学到能够找到工作的技巧,我们对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就比较注意。
所以,我们学院里没有传统的一般的美术学院里重点的艺术专业,国油版雕我们都没有。我们的专业方向,都是跟市场走得比较近的,比如交互设计、工业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室内和景观设计等,我们甚至还有一个专业叫文化创意产业策划与管理,完全和市场密切结合的一个专业。我们只有一个公共艺术专业,比较靠近纯艺术。我们的专业主要是盯着市场。
在专业方向的发展上,我是受了美国影响的,专业设立和社会需求、市场需求结合。在课程上面,有一些调整,但不是把美国体系放进来用。我们很幸运的是,汕头大学实行学分制,但是,学分制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学美国。在美国,必修课只占到总学分的1/3,选修课的比例很大,但在我们这里做不到。
我们的公共必修课压力很大,很多课在美国是没有的,比如政治、外语,在美国除非你是学外语学政治专业的,才要学。而这些课,占了很大的比例,本科生一年级的课基本上都被这些公共必修课占领了。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套用美国的学分制。
5年要改变一个学校很困难,教育的事情不容易。我在美国的那个学校,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是1930年成立的,工业产品设计专业是1986年才建立的,在那之前,工业产品设计和汽车设计是一个专业,1986年才分开。
我在这个学校正式教书,是1989年,也经历了20多年,他的工业设计专业才慢慢形成轮廓,汽车设计专业原来就很强,其他专业还在变。我当时建议他们,建立娱乐设计专业,15年前我开了娱乐设计导论,到3年以前,这个学院才设立了娱乐设计专业,从我建议到成立,用了12年的时间。
5年时间要改变一个学院,非常难。我觉得,一个院长如果要让一个教育体制产生变化,大概要两任,也就是10年的时间才够,但是我估计我做不到这么长的时间了,有各方面的原因。
关于教学改革的成果,我们只能说,第一步是按照汕头大学的要求和教育部的要求,把所有的课程修理了一遍,把不正规的、有问题的、零散的东西,比如学分、记录等,修理了一遍,特别是经历了今年的审核评估后,应该说这方面修理的比较整齐了。
汕头大学在审核评估当中是表现挺好的,并且是广东省最早审核评估的大学之一。但是面临的问题是:专业和教学的结构合不合理?对这些问题今年才开始动手,对专业课程和4个年级的分布,进行比较大的改动,这些改动还在研究之中。
在我的主导下,将从2017年开始,本科一年级取消传统的素描、色彩等基础课程,学生一进来就选专业。我在美国的教课的那个学校,学生一入校就选专业。当然有一个是我们做不到的,美国采取的是择优录取,如果第一年你没有通过的话,第二年你就不能再读,这在我们国内做不到,就是不能退学生。
按照我们的新规定,2017年入学的本科生,进校两周,在了解学校情况后就要选专业,这样就减少了一年的原来的基础课耗费的时间,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工作,这样的成果会怎么样,还看不到。
第二个。当初我接手院长的时候,专业方向太多,我们开始收缩和调整。像我们这样只有40多个老师的学院,有5到6个专业方向就足够了,现在我们有七八个。所以我们做了收缩,未来我们还要再收缩一些。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的资源和教员都非常紧张,有些专业只有三四个教员,这不正常。
在课程的设定方面,我们也在进行一些改革探索。有的课是应该有的,比方说,整个学院没有一个共同的针对人文的课程。我最近看了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书《让人成为人》,所谈观点是,因为有了艺术,人才是人。这种思路的课程,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计划在2017年开一门课,就叫“人文基础”,讲诗歌、戏剧、音乐、电影、绘画、雕塑、建筑等,把它作为一个大人文的东西去讲,这门课程不容易,但我们希望在课程上做一些调节。还有一些具体的课,我们认为很多专业都需要,比如怎样提交自己的方案,做方案的方法每个专业都需要,在全国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个学校开设如何做专案方法的课程。
还有一个更大的改革在于,我们要把基础课原来必须修的素描、色彩和速写进行修改,估计在未来很多专业就不上这个课了,因为很多学生在进学校之前已经上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课,到大学后又重复一年。
我们考虑,基础知识应该由几个部分组成,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动手,也就是金工、木工、电工等,还有3d打印、摄影等,我们考虑在2017年基础课要在这些方面有比较大的改革。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源有限。我们在硬件和环境方面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我们的地理位置相对很弱,汕头在粤东地区,远离经济核心发展地方,这里到珠江三角洲还有300多公里,这里的经济是偏落后的,远远比不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
我们要找到好的老师,找到好的项目,找到学生实习的地方,都只能转向珠江三角洲,这也是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聘请国外的老师,但是存在学生的语言水平不高的问题,用英语教学还有一定的困难。聘请台湾、香港的老师,也有一定的具体操作难度,比如香港老师的国语水平平均来说不是太好,台湾和香港的人工费用比较高,按照国内的工资待遇,达不到。
总体来说,我们的教学改革需要两任、10年时间才够做。但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再投入到这个上面,所以我希望把基础做好,以后的老师会继续往前推进。
我们的体制是单一体制,也就是教育部制定的一套体制。又按照重点院校的排列,国家给予投入,投入多的学校可以达到上百亿,像汕头大学一年也就几个亿,分到每个学院,也就仅够运作,发展的硬件和软件,我们都跟不上。这里我特别要讲,软件跟不上。
所谓软件跟不上,就是人才跟不上,我们找人很难。因为潮汕地区没有办法让人找到其他的工作,比如做交互设计的人,在这里只能教书,如果他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外面的活儿多得很。
还有体制问题,是大家都认同的,但是也没有解决的方法,中国的教育也不能开放给市场竞争,也不能开放给外国,与外国合作也只能是合办,大家都必须按照基本要求去做,也不能说他错,就是这么个情况。比如说,新生要军训,学生要上很多的政治课,要上很多的英语课,这些都是硬性的要求,我们也改变不了。
我不认为我们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突然看到教育部能够让外国的比较好的学校来参加竞争。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在能力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小幅度的改革,像基础课、专业布局这方面的改革。不要去奢想我们能够动大的,背不起这个风险。
这主要是针对学生的素质而言。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是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一条龙上来的。我在美国教书的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他要求工业产品设计的学生,基本上要读过其他大学,或者是工作过3到4年,所以一年级学生平均年龄是25岁,这和国内有很大不同。
这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这在国内怎么可能呢,你工作了4年,再来大学读4年,这个大学必须有很强大的力量吸引人。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他不缺学生。也不是每个学校都能这样的。
社会需要工业设计是因为有高端的综合能力。从我们现在的高中生来培养的话,我估计培养不出来,这些学生只能毕业后到社会上获得自己的经验,才能变成这样的人。学校的教育只能给他一个基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学生必须到实践里面去训练。
学校教育能够做的是增加实习。我们已经安排学生在暑假进行3个月的实习,两个暑假加起来就有六七个月时间,学生在设计公司有六七个月的实习,他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就会提高。所以我们把希望放在实践的锻炼上,而不是仅仅通过教育。
教育也很重要,这需要老师给学生提出很多实际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我们的老师现在也是高低不平,有些老师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些老师自己也没有做过设计工作,也就是从学校到学校。现在各个学校都追求高学位,要求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种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一条龙上来的培养方法,出来的老师肯定是没有经验的,这成为中国设计教育将来的一个隐患,大量的教设计的老师本身没有做过设计。
我遇到很多这样的老师,夸夸其谈,不能动手。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比较特别,我们都是先工作再上学。我在设计公司工作了6年才读书,再去做设计教育的时候,已经很有经验了。这样的经历,不可能了,这是特殊情况下产生的。但是要求目前的老师都有这样的经验,比较难办了。
这个现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设计公司比较强大,和高校一起联合办学,他可能提供给高校一些专项的锻炼的机会。有的设计公司和学校搭在一起是为了出名。因此,不能一概而论。严格的来说,国内的对教育有很高期待、有理想主义的企业,我看极少。
有理想的企业,在中国比例很少很少,虽然我们有钱的企业很多。企业文化的成熟,是对社会的使命有一种认同。当然,企业都是追逐利润的,但是同时,对于社会教育,他有一定的责任,有一定的认同,这是比较成熟的企业,这种企业我看不多。
所以也就不能期待,设计公司与高校办学,就能办出很好的学校,不过是大家各自利用对方的长处,互补自己的不足而已。但这种现象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说他错,也不能说他对,要看具体的情况来定。
教育,医疗,一搞产业化,就变质了。教育是育人,如果利润成为一个目标,那就没有办法搞了。我们的设计教育为什么现在搞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是因为学校要搞产业化。大学要搞“大舰队”,学校搞得很大,有一部分是靠国家拨款,有一部分要靠学费收入,而对于招的学生,一般来说都是限制学费的。
在扩招开始的2005年,当时一个学生的学费是5000到6000,只有艺术和设计的学费可以收到1万,有的学校收到1万多,有些省市达到14000或15000。
也就是说,一个学校想把自己的收入提高,设立了设计专业的话,比设立别的专业要赚钱。在这种情况下,就迫使很多学校为了增加收入而搞设计专业,这就是毁于一旦。这么多的设计院校,1000多个大学有设计专业,并且全国有40多万学设计的学生。
哪有这么多的老师?没有办法协调,又没有办法脱颖,明摆着有的学校面临停牌。十大美院占尽头獒,剩下的那些学院就自生自灭。所以有很多的设计专业,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去看过一些学校,那完全就是在混,根本就没有好的师资。而设计又是一个精英的教育,要求培养出有综合解决问题的、高智商的、有情感的、有人文素质的人才。而现在我们是把它泛滥,所有的学校,理工医农,全部都有设计专业,这怎么不是毁于产业化。
这个问题,到了目前这个状况,我们都解决不了,大家扭不过来了。我们能够讲的,如果没有2005年的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扩招做法,可能我们现在还比较容易把设计教育搞得更好,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