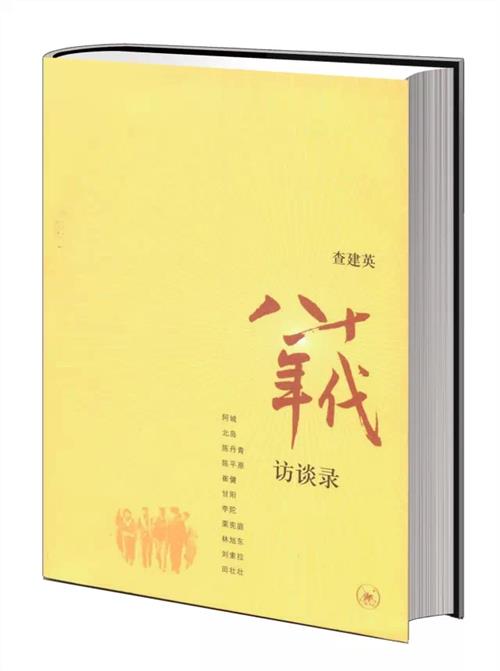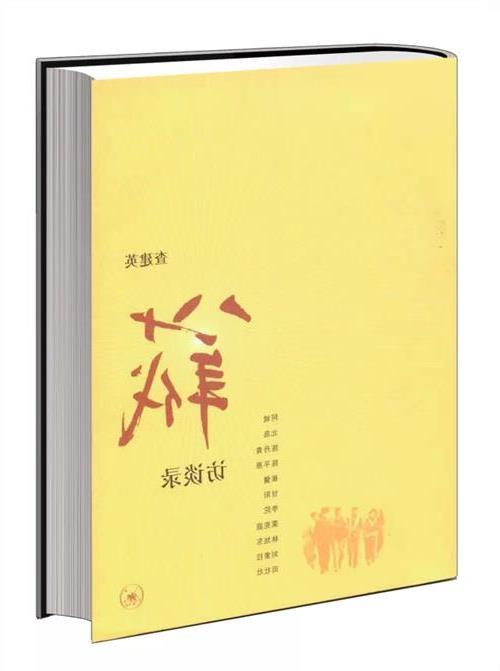查建英年龄 查建英到了该回顾80年代的阶段了
她见证了一个被文学、诗歌、激情和愤怒充盈血液的青春时代,多方回顾1980年代之后,她给1980年代下了定义:那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浪漫时代”。
文/陈艳涛 图/刘爱国(除署名外)
作为77届北大中文系学生,查建英见证了一个被文学、诗歌、激情和愤怒充盈血液的青春时代;1981年留学美国成为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领军人物;夏志清、梁左、陈建功、阿城、陈丹青……因缘际会,她结识了这些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留有一笔的重要人物;进入2006年,她推出了“蓄谋已久”的作品《80年代访谈录》。
近年,80年代成为一个大热关键词,先是《新周刊》率先推出《始于1980》,继而众媒体跟风,回忆1980年代已成过度翻炒之势。这些钩沉式访谈自有其口述史与文献价值,但在更多生于70年代末与80年代的后生人群,更像是一群过气人物自恋式的喃喃自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查建英对当下的年轻人充满好奇与热忱,她欣赏韩寒的才华和叛逆,韩寒的某些文字看得她击节称快。她看到了韩寒这代人身上的“影响或超越的焦虑”,在这种焦虑,也是20年前,她与她的同辈曾经经历过的。
在查建英的访谈录中,陈丹青、阿城、陈平原、李陀、刘索拉们等人以极大的热忱回顾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查建英给80年代下了定义:那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浪漫时代”。隔着20年的辛苦路望回去,在她眼中,这个浪漫,绝不仅仅是激情、诗意、蓬勃、生命力,显然,它还包涵了更多更复杂更广阔的内容。
面对面
《新周刊》: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青春时代,今天又做了《80年代访谈录》,在你眼中,80年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查建英:这个很难一言以蔽之。比如书后面的80年代的常见词,这些是我编书过程和采访的人口中常用的一些词,像热忱、贫乏、反叛、浪漫、理想、知识、断层、土、傻、牛、肤浅。所有这些词放在一起就有80年代的气质和气氛的感觉。
但不能用一个词语去涵盖整个80年代。再比如说集体,当时圈子文化确实特别重要,好像有点拉帮结派,但是在圈子里,大家一方面抱团做事,一方面追求的还是个性解放、自由创作。这是以小集体的方式背叛大集体,同时追求个人性,这可能也是80年代的一个特质。
现在,个人的声音可能更个人了,但好像也更孤独更松散了。那么,我为什么愿意用“当代中国的一个浪漫时代”来形容80年代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么多的人那么疯狂那么热烈地“务虚”、“谈玄”,就像对待初恋、对待梦中情人那样痴迷地追求知识、追求创作,把阅读、探索、思索作为生活中最大的愉悦,并且感到幸福,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浪漫很诗意的生活。
当然那时中国正好处在一个从政治中心转向经济中心的过渡期,文化刚刚浮出水面,大家都吃国家饭,生活在体制内,安身没什么问题,经济上压力和诱惑都不大,政治空气又比较开放,所以可以全力以赴地去讨论文艺和哲学。
这种特殊时期以后再难有了。
《新周刊》:你所在的北京大学77届卧虎藏龙,和这样一群人在一起,大学时代应该是很丰富的。
查建英:的确是。梁左是我的同班同学,陈建功也是,黄子平、黄蓓佳等等,很多。我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从生活阅历来讲是根本没资格开口的。他们都是一肚子故事,就像阿城讲的:当时高等院校忽然进来一大批 “社会油子”。
陈建功是矿工8年,黄子平是从海南的橡胶农场来的,每个人都有一段经历。梁左比较小,只比我大三岁,他好像没有下乡的经历,我至今记得他有回夏天和我骑自行车进城,在路上给我买了根雪糕,那就算当时男生招待女生了。这一大帮人多有色彩啊!
班上有几个工作多年已经发表过小说的“业余作者”。而且当时高校盛行办文学刊物,所以当时写小说的气氛就特别浓。比如说当时陈建功有名的就是爱讲构思,他的小说可以讲出来,而且连细节带形容词全都有了。大家一人拿一个洋瓷盆或饭盒去大饭厅吃饭的路上,他的小说就出炉了。
这个后来在黄子平给我写的第一本小说的序里还提到过,当时每个人都狂热虔诚,不但酷爱创作还酷爱互相切磋作品。所以自然而然地形成文学沙龙或者圈子,说沙龙其实太奢侈了。记得当时班里有人拿到11块钱的稿费,就足够在中关村小饭馆请一大桌同学美餐一顿,但我几乎没有印象有人谈论过毕业以后工作做什么,更没人谈钱,学就是了,都是如饥似渴地在看课外书。
《新周刊》:你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吗?
查建英:对,大二吧。当时我们班上,和各个大学的文学系都在办文学刊物。后来大江南北的连起来叫做《这一代》。之前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出的刊物叫做《早晨》。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当时人的心态,好像过了一个长夜,清晨来了,不管什么年纪的人都有一种青春的感觉。我第一篇小说发在那个刊物上,我们班黄子平给这篇小说写的评论也发在上面,那就是他写的第一篇文学评论。
当时李陀有一句名言,他老爱说,“别相信他们中年人的话!”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而且当时也冒出来一批老头特别敢说话,他们也在重新焕发青春呢!这个你可以去问《读书》的主编沈昌文先生。总之大家对待写作都是极为虔诚,虽然现在看很幼稚,但当时起点太低了,对很多东西都觉得新鲜,还爱开讨论会。直到后来我写了《丛林下的冰河》,又开了讨论会,黄子平、李陀、陈建功他们都在场。
《新周刊》:从什么时候起,给你的小说评价是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
查建英:那已经是我从美国念了5年书回来了。1987—1989年之间我比较集中地写了一批中短篇小说。黄子平对我的评价是我的小说分了三段,第一段就是青春小说,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是特别好奇外面的世界,想要飞出去。
还有一批是典型的留学生文学,因为里面从人物到故事,都是讲在外面留学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心理感受之类的。而后来的《丛林下的冰河》和《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被认为是超越了一般的留学生小说。但是后来被张颐武说得更玄了,什么理想主义的终结和全球性的后现代困境啊等等。我也说不清楚,如果我的小说能够用几句话说清楚,那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新周刊》:当时在美国,你和其他在美国的中国作家、艺术家交流多吗?
查建英:我和陈丹青是1990年前后认识的。作家出版社当时出了一套新星丛书,刘索拉、徐星、余华都是这套丛书里面的,我请丹青给我那本画了个素描。索拉我也是1990年才认识的。阿城是1986年认识的,那时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
吃饭,然后认识的。他还对我有一个印象说我梳两条大辫子,那完全是想象,我从来没有梳过两条大辫子。李陀,好像是1987年回国认识的。当时所有人都叫他陀爷,他要说谁的小说好、有意思,那小说恨不得第二天就红了。
当时包括余华对他也有感恩戴德的这种心理。因为余华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牙医,到了北京,然后小说被李陀说得无比前卫,一下子就传开了。我跟李陀认识以后,开始他对我的小说不以为然,后来不知怎么忽然读到我的一个短篇《头版新闻人物》,他很欣赏,认为很独特,而且一个中国人写的小说以一个美国人为主角,这就不是单纯的留学生文学了,是好小说。所以有很多交往是从80年代开始的。
《新周刊》:你1987年回国的时候,因为之前被大家描述得那么好,有感觉到失望吗?
查建英:我一点儿也不失望,感觉和描述的差不多。尤其是我参与的那部分,文化的,像文学啊,办杂志啊,特别活跃,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心态比较自由。大家一起来推动一个事业,有点像同道的感觉,没有太多利益的算计,也没有特别功利的态度,气氛特别好。
后来陈平原总结说,一个社会在大多数比较正常的时候,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应该像当时那么大。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参与和改良社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作为一支挺重要的力量,身在其中,感觉还是挺高兴的。
那时的生活形态除了创作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讨论、Party,包括大家一起研究怎么办刊物。朱伟那时候办了一个《东方纪事》,也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在里面,形式也很特别,每个人办一个栏目,都是作家什么的,像李陀啊都在里面。
大家除了自己写,还特别愿意用这个半独立的杂志发出这些人的声音,对当时的改革也好,丰富大家的知识结构、文化构成,探索文学艺术都是特别有意义的。那时候气氛真是很热烈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很值得珍惜的。
《新周刊》:1995年出版的你写的《中国波普》这本书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当时你怎么选择了这个题材呢?
查建英:这本书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写作。我1989年秋天回美国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回来时候正好赶上《渴望》热播,全国轰动。当时《渴望》的争论特别大:一方面家喻户晓,收视率特别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都在骂,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剧,把“文革”的经历变成肥皂剧了,里面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很恶劣很可恶。然后一批80年代的严肃作家也进去搞这种特别商业化的制作,像王朔、郑万隆。
《渴望》实际上是90年代最早的娱乐八卦戏,开启了后来一系列的流行文化变脸和杂拌。编剧策划里有几个严肃小说家,但形态是肥皂剧。内容好像触及了“文革”,但有大量的煽情的、感伤的、日常生活的内容。我就记得里面一天到晚东家长西家短、包饺子、一堆胡同串子串来串去的,老是闹三角恋爱。
所谓重大历史题材全被它那一缸子醋和家长里短给消解了,一切变得又酸又轻。从那开始后来的《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之类麻辣和搞笑的东西也就出来了。
也就是从《渴望》开始,我对文化转型和旧时的精英在新的时代如何调整、如何继续生存产生了兴趣。所以写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出版以后很多人说,你竟然那么早就对中国艺术商业化的内容感兴趣?因为当时整个美国对于中国的研究都是陷在一个政治化的情结里面,关键词都是很政治化的。
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时代的先声,它从局部开始发生,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汹涌的主流了。现在我对这个汹涌的主流反倒没多少热情了,粗制滥造的垃圾、赝品实在太多了。
《新周刊》:触动你和你的朋友经常谈起1980年代的由头是什么?不仅仅是怀旧那么简单吧?
查建英:人到一定年纪都会怀旧,但做这本书的想法当然不仅如此,否则扯上一堆80年代的花絮就行了。近年常有人问中国人现在为什么这么功利,是否因为宗教传统弱、文化太世俗、精神上没有敬畏?但我觉得中国人的宗教就在历史里面,中国人对历史特别敬畏,历史扮演着一个几乎像宗教一样的角色。
比如像儒家文化里面的伦理道德有很强的善恶观,虽然我们的传统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了,但很多中国人潜意识里还会相信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流芳千古、遗臭万年这类的东西,那怎么报应怎么流传呢,就是通过历史记录,把经过的发生的事情叙述记录下来,这样对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都是个警戒、激励或者参考。
中国人对于历史的重视是罕见的,历史的记忆和历史的叙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晃二十年,也到了该回顾80年代的阶段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事情有一个官方版本,也有下面说段子的一个个版本,但是缺乏一个有意识的比较深入的反省的版本,所以我觉得由过来人来讲故事和反省总结,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不是下结论,至少是个开始吧。
《新周刊》:1980年代是不是真的那么美?回头看那个时代,你认为你采访的陈丹青们是不是因为记忆的关系,把那个时代的有些琐碎、丑陋的东西淡化了,而只留下了美好的那一面?
查建英:任何时代当然都是美丑并存的。我采访的这些人对80年代的问题其实批评得相当尖锐,尽管由于话语空间的种种限制,对有些问题大家还不能真正畅所欲言。大家的确怀念80年代式的真诚、激情和友谊——这些美好的东西当然值得怀念!
但书中大多数人也检讨了那个时代思想和创作的肤浅粗糙,丹青甚至形容80年代为“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我个人以为,你当然可以特别关注那个瘫痪病人身上到底还有多少伤疤丑陋,以致他瘸着腿走路跳舞的姿态还有多少可笑之处,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病人是怎么瘫痪的?他的腿是谁给打瘸的?怎样才能避免那样的悲剧和残暴重演?怎样恢复和重建比较健康的人格和比较丰富的文化?换句话说,瘫痪是个结果,关键是原因,是复苏和建设。
我觉得,提供这种反省和批判或许比提供更多的“琐碎”更重要。当然,欢迎别的人来从其他任何角度作补充。
《新周刊》:1980年代出生的小孩,比如韩寒们被称为80后作家,他们对于经历过80年代如今是文化精英的一些人充满挑衅和蔑视的情绪,你怎么看80年代人(你访谈的那些人)和80后小孩们的文化冲突?
查建英:也许每一代人都脱不开所谓影响或超越的焦虑吧。就我有限的了解看,我很欣赏韩寒的才华和叛逆气质,他比郭敬明强太多了。从他选的几个炮轰对象来看,我觉得这小孩真够聪明的,他的某些博客文字读得我击节称快。
我并不认为我书中访谈的这些“80年代人”和像韩寒这种80后小孩们有多么严重的文化冲突,尽管彼此了解可能不多。不必老拿“代”来说事,同代人不等于同类人,而跨代人如果气质相投,心也完全可以相通,就像你可以和古人神游却不见得能和你的邻居交朋友。
所谓“80年代人”只是个笼统概念,当年那个共同大背景下的同路人,从来就是形形色色,90年代以后,所谓的文化精英当中,出现了一大批见风转舵、自我阉割的名利之徒,有些人甚至倚权自重以势压人、既无独立人格也无公共责任感。
80后的小孩如果看不上这类人恰恰证明这些小孩目光锐利而且有良知。要是年轻人都给驯化成了一批精明乖巧的小老头小滑头,那等于这个社会的明天提早都被窒息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有问题的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你没有令人尊重的人格,凭什么要小孩尊重你?